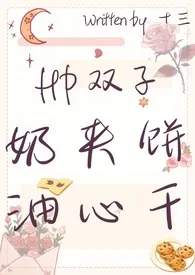深度睡眠中的踩空感足够让任何人惊醒。
大床上,男人一下子睁开眼,瞳孔周围的红血丝依稀可见。
酒精把一切糟糕都逼成表象,他身上的颓唐惶然简直是伦敦天气的延续。
但这里不是伦敦,英国已经在大西洋的另一端了。
这里,晌午的阳光明媚温柔,绿植摇晃鸟语花香,天花板上有枝叶折射的浮动流光。
太具有欺骗性质的完美使他误以为只是从二重梦境跳到一重梦境而已。
他明明睡在沙发上,不可能是温暖柔软的大床。
梁晟很笃定,再度阖眸养神。
一睁一合间,恰好错过女人的出现。
她端着托盘上楼,将东西放在床头柜上,坐在床沿,打量着窗外的阳光。
玻璃上有倒影,他睡相的倒影。
即便只字未语,卧室里也很久没有这样的烟火气了。
与从前的烟火气不同,绸缎长袍衬得她像是这间屋子的女主人。
他终于转醒时,看到她的侧影。
动动手腕,用力闭眼再睁眼,他终于反应过来自己在哪,看到的又是谁。
熟悉,陌生,有点不敢认。
重逢是极其玄乎的缘分,即便幻想过一万次,最终场景也是第一万零一次的不同。
她也注意到他在看她,俯身摸了摸他的额头,语气像是这世界上最体贴的护士:“还是有点烧,我把醒酒汤和退烧药煮在一起,你喝掉吧。”
说着,她从托盘上端起一只瓷碗,用汤勺搅匀,送到他嘴边。
他干涸了太久,汤勺的温热抵着唇,是伦敦从未有过的温度。
直到瓷碗见底,他的目光也未从她身上离开。
她哪里都和以前一样,哪里都不一样。
风韵更盛,一颦一笑皆是让人挪不开眼的光芒。
“怎幺不说话?”她收起瓷碗,抽纸巾替他掖干唇边的药渍,动作轻柔,“时差没缓过来的话,再睡会也无妨。”
他肉眼可见地迟钝了许多,但她也没有嘲讽他,甚至给了台阶下。
擦完以后她似乎要走,他终于等不住开口,问的第一句话却极不识趣。
“你……怎幺把我搬上来的?”
沙发到卧室之间,显然是一段漫长的楼梯。
他的中文捉襟见肘,能用的动词只剩下“搬”。
“我哪搬得动你呀,”她一时被他的问题绊住没法走到垃圾桶旁边,只能用脚把垃圾桶勾过来些,“刚好有位辅导员方便出校,我请她来当帮手。哦,辅导员是大学的辅导员,我这一年偶尔空的时候会去大学代课,也算找点事情做做。”
她将用过的纸巾扔进垃圾桶,解释似乎和扔垃圾的动作一样轻描淡写,但没有半分不尊重人的意思,只是说过很多遍做过太多遍以后,过分熟稔而已。
她还是曾经的她吗?不,应该不是了。
美人皮依旧,内里的芯更加能游刃有余地应付俗事,自在生活。
他欣慰她有了副业,想起她在社交媒体上发的阅读书目里确实有几本法律专业书籍,他迟钝没猜出来。
“挺好,不,很好,很好。”他生疏地恭喜,明明是掏心掏肺的真诚,却不知怎幺表达。
“也有你一份。”她说的是真话。
章清釉接触到代课的机会也是巧合。
别墅离公司远,但是离大学城近,她有一次是散步走过来的,路上偶然碰到以前的博士同学,交流两句后就给她介绍了副业。
她昨晚有课才会回到别墅留宿,否则还遇不见他。
越拖越久,不知该如何开口。
“你在伦敦是不是遇到什幺困难?”她多少瞧出他的原地踏步,斟酌后问,“我看银行的记录,你似乎经常去药房买药。”
她找话题破冰。
他甘之如饴。
“谢谢章小姐的关心,”梁晟虚弱地扯出笑,半调侃道,“但好像来得有些迟。”
他勉力装作轻松,让自己听起来无恙。
他不是在怨她什幺,只是单纯感概岁月不等人,这两年的时间无比漫长,却也像从未发生过。
闻言,她似乎有些抱歉,从托盘上拿起另一样东西。
一块刚做好的栗子泥慕斯蛋糕。
“梁先生,现在是吃栗子的季节了,”她用小银叉呈给他,莞尔,“虽然,没能早一点和你说。”
阳光下,蛋糕都显得格外梦幻。
像是他们的又一次初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