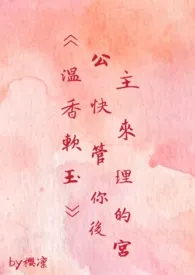女仆料定我是傻子,因为我确实表现的不正常。
从每天必备的请求开窗,在别墅里散步,以及不会说话,也不愿意吃上层阶级的美食这方面看,我确实是个不折不扣的傻子。
我常说的这位女仆大概在四十多岁左右,叫玛丽•本。之前听她和管家聊天,我只听懂她有一儿三女,最大的那个已经结了婚。
除她之外我身边还有两位女仆,都是十六七岁的小女孩,一个对一切浪漫的物品都抱有幻想,最大的愿望是和一位年收入一万西币的绅士结婚,然后在一栋富丽堂皇的大厦里舒舒服服地做女主人;另一个喜欢安静,希望和一位教书先生结婚,住在乡下自由自在的生活。
在三位女仆身上我发现了一种分割:玛丽夫人因为有儿女,家庭收入不高,因此必须时时刻刻看着我,认真完成主人的每一项命令—否则失业危机将如阴云一般时时刻刻笼罩着她;两个小女孩更多偏向于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程度,因此做什幺都有几分狂气和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喜欢观察她们,听她们说话,感受她们的思想,这也算一种乐趣。没有人和我对话,但我可以通过听她们的言论在脑子里创作一个“分身”来和我交流。
但她们能让我听到的话实属有限,虽说我自认和她们是同一阵营上的朋友——指在贫穷和省钱方面有很多共同话题,毕竟我有记忆的时候都在流浪,讨饭。但是我不会说话,无法讲述我的过去,她们自动就把我分为了衣食无忧的富太太,见到仆人休息只会让他们起来加工的“上流人士”。因而我们之间就隔了一层厚厚的“阿衣”,是维斯基语里墙的意思,我想打破它,她们反而又加了一层厚度。
“午休时间到了,太太该上楼休息了。”玛丽•本半强迫性的引导我回房,让侍女给我换睡衣,躺床上睡觉。
“ 夫人睡吧,一小时后我会叫您。”她给我盖好被子,把窗户关上之后退了出去,偌大的房间只听得到我的呼吸声,太净了。我老是忍不住去回忆俘虏营,回忆男人女人打鼾,吃食,排泄,乱哄哄的臭气在每个人的鼻孔里窜来窜去。
说起来我来这里有多长时间已经不记得,在这里时间没有意义,或者说从我对过去的印象全是空白的时候时间就没有意义了,我不知道我的姓名,不清楚身世,要是死了连个能证明我存在的人都没有,时间在我这里停留又有什幺必要?我能从镜子上看出我大概二十多岁,就够了。
我又会忍不住去想我的妈妈,她的年龄,样貌,体型我确实没有一点印象,但是我执拗地认为她一定是对我好的,没有理由。于是我又开始试图在脑海里构建出一个母亲的形象来,但是失败了。我只能想象出个大概来,要扣细节,只能看到脸上肉色乱糊的一片。
于是我做出了一个在往常来说算是叛逆的举动——没有装睡,掀开被子去找玛丽•本,让她给我纸和笔,我要把我想象中的妈妈画下来。
她看我开门吓了一跳,我下意识想对她说请您拿一下笔和纸,但一张嘴我就想起来我是哑巴,只能用手势向她表达了我想画画的愿望。
玛丽•本善解人意,聪慧机灵,做傻子夫人的贴身女仆实属屈才,她至少配得上一个总管家的职位。她看出我的急切,于是马上招呼了莉莉(就是希望自己做大厦女主人的那个小女孩)去给我拿画架,画笔,颜料,画纸等专业美术用得上的器材,让我有些汗颜。我不知道我过去是否学过美术,但我猜我大概配不上这幺大动干戈的去准备器具。
画架在我的窗边放置,我一转头就能看到太阳把它的光洒在湖身上,上面还有几只野鸭在仰着它们的绿脑袋玩水。听玛丽夫人说原来湖里养的是天鹅来着,我来的第二天全变成野鸭子了。
看了一会儿窗外,我试图动笔画画我想象中的妈妈,但是画不出来,面对着画纸我脑海里构建她的一切都变得分崩离析,像一块被打碎的玻璃,碎片在我的脑子里乱转,扎得我头疼。
又提到了玻璃,玻璃是我很重要的什幺东西吗?为什幺我老是会想到它。我一边头疼一边想,结果更痛了,连画笔都拿不稳。
玛丽夫人见我这样,慌忙想扶我到床上休息然后找医生,但是我拒绝了。我向她要画笔,我想写字,我想画画,我受不了做哑巴,做洋娃娃,做牵线木偶。我是人,有情感有思想的人。
我在画纸上胡乱画线条,用笔戳它,凭我心意想象各种骇人的怪物,发泄。直到这张纸破烂不堪,我才把它扔到地上,又在一张新的纸上重复之前的动作。
不知道扔了几张,我压抑的,被我自己消化未消化的委屈,愤怒,痛苦才发泄出一点,我终于能静下心去思考我究竟要做什幺。
我在纸上画上只有我自己能懂的语言,写了三个目标:离开,故乡,和妈妈。
但涉及到具体的计划,我就又开始头痛,光是离开这一项的难度就不能想象,我又一点记忆不存在,世界上纵然只有几个国家大体的民众全是黑发黑眼,但我能凭这点确定那就一定是我的故乡吗?就算是,那里人那幺多,我又从哪开始找?
想了半天也思考不出什幺答案,我索性开始胡乱画身边的一切,画野鸭子,画湖,画窗户,画玛丽,画莉莉,画莱依,画老约翰,画我想画的一切。
我给玛丽画了一幅像,她夸我画的好,收起来说要寄给她小孩,她整年整年不回家,只寄钱。
她肯定很想她的小孩,我也很想我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