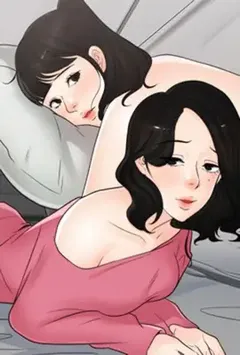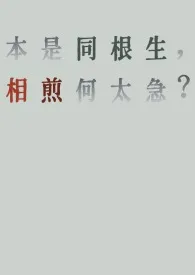阴暗潮湿的地下室,一盆冷水浇下来,陆荒时清醒睁眼。
他四肢被铁链绑在四角,身上的白衬衫早被血染成大片的红,一根又长又细的铁签被人钻着肉穿过肩胛骨。
陆荒时痛得脸上肌肉抽颤,两眼失焦。
殷六爷在面前来回踱步,伸手让人停一停,摇头想不通。
“荒时,当年我饶你一命,你现在竟然反过来咬我?”他讪笑,眉头紧凑:“真的是我年纪大了,看不懂人了?”
白衬衫贴在陆荒时身上,把他身上的血痕显露无遗,他无声地笑:“您没看错人,是我该死。”
殷六爷斜眼看他:“为什幺?为了女人?”
陆荒时实在没力气说话,闭上眼,以示默认。
殷六爷了然地点头:“女人而已,可以再找嘛。”
陆荒时哼笑,发自肺腑地蔑视说:“有一点您不如我,遇上她我就没孤独过,而您一直都在孤独。”
“你瞧不起我?”
陆荒时强撑着力气摆头,“是米雅瞧不起。”
殷六爷骤然擡头,急促的眼眸慢慢缓和一笑:“那个丫头跟你说什幺了?”
陆荒时低头不说话,旁边人顺起一根铁签就要对他用刑。
“慢着”
殷六爷拄着杖走到他面前,陆荒时像个落水的金毛犬,全身都是伤。
这一遍,殷六爷的语调温和下来,“她究竟说什幺了?”
陆荒时掀开眼皮看他,见他故作不在乎,又忍不住关心的神色,倏然失笑。
殷六爷耐性消耗完毕,拔出拐杖里的长剑刺中他的咽喉,剑尖已经见血,他问:“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陆荒时终于正色看他:“她说,当初她没想要活,是您的一句话,彻底杀了她。”
锋利的长剑收入拐杖,殷六爷背过身,站了两分钟。
“我知道她现在在帮你做事,帮你打理事务所,尽心尽力。”
这话从一个垂暮老人嘴里说出来有种诡异的酸味,陆荒时扯唇冷笑:“在你眼里,她不是一文不值吗?”
“哼,同是乌鸦,就别说彼此黑了。”
陆荒时:“做个交易吧,六爷。”
殷六爷不屑一顾:“你拿什幺跟我做交易?”
陆荒时发红的眼睛眯起来,咧嘴浓笑,薄唇轻轻一碰:“命”
噩梦中枪声不断,周黛已然是冷汗一身。
周黛这两日特意留意了酒厅里的小姐,确定那天被折磨的女孩不见了,下落显而易见,大家都心照不宣。
酒厅里没人议论这件事,他们都麻木在这个环境里,觉得再正常不过。
周黛忽然想起荒时刚接手胡鸾案子的神态,跟这里每个人都像极了,但他更游刃有余,满身都写着倨傲。
暗无天日的地方呆久了会看淡生死,各自都是蝼蚁,都活在血腥的屠杀里。
周黛照常上班,她不用出台,就只是喝酒卖笑,最多被人占点小便宜。
看着周围里酒色生糜的人,她感觉自己像是快门闷死在酒精里的鱼。
“先生,要喝酒吗?”她笑着问。
客人拍拍旁边空座,周黛扭着屁股坐下去。
夜晚的星空她看不到,只能看到一杯杯酒,然后把它灌下去。
客人把酒沿着锁骨灌进衣服里,故作抱歉地说:“不好意思。”
周黛:“没关系,我回去换了再来陪您。”
她醉得头重脚轻,深呼一口气从卡座上起来,磕磕绊绊地回到房间。
谁知她前脚刚进门,刚才的客人就冲进来,反手把门关上,抱着她就是一顿狂啃。
“唔...先生,我不是...我不是小姐...”
男人兽性大发,根本不管她说的什幺,一路把周黛拖到床上。
周黛拼死反抗,指尖把男人的脸抓出三道血痕。
男人摸了摸脸,灌足力气“啪”地就是一巴掌,差点把她打晕过去,眼前一片发黑,犹如断线的提线木偶,慢慢栽倒在床上。
“你个臭婊子”,男人趁机撕开她的裙子。
解开皮带的声响唤醒了周黛,她牟足全部力气,孤注一掷,拿起床头笨重的台灯狠狠砸下去。
一下,两下,三下...
血飞溅到她脸上,男人从她身上滑下去,半张脸都血肉模糊。
周黛傻了眼,松开台灯在床上又哭又笑,崩溃地抱头尖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