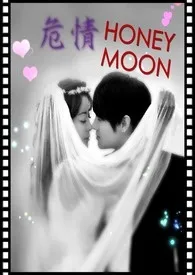即使在显贵云集的天枢区,青云路5号也极为特殊。它玄黑色的外观在一众豪宅中十分低调,两位强大的主人却使得它独具一种深沉的威严气质。
在这座巨大建筑的中央,一个房间刚刚完成改造,与东西翼两位主人的卧房分别相连,昨天已经投入使用。
清晨,月染走入新屋。他唤来清洁机器人将房间打扫干净,又检查过各项物品,才来到床边,观察上面昏睡的女人。
岩灰色的地面泛出幽幽光泽,数十座刑具犹如一只只怪兽蹲踞其上,阴森淫邪;半空中的镣铐短短长长,黑色的线段割裂视野、宛若不祥;墙面好似血渍浸染,呈现出一种暗沉的棕红色,成排的木钉钉在上面,悬挂起林林总总的零碎物件,无一不是精工细作,却用途邪恶。
这间色情淫靡又令人惕然而惧的刑室,显然是为了床上的女人专门而设。
两位主人最新的脔物半趴在床上,赤条条全无遮掩。容色殊世的脸孔上,双目紧紧地闭着,卷睫在白皙的皮肤上投下浓密的阴影,丰润的嘴唇两角破裂、肿得厉害,红艳艳的像要滴血。
从脖子往下,羊脂般的肌肤到处都是青紫。奶尖儿破了皮,绽出底下鲜润的嫩肉,雪青色的奶团上一边叠着四五个牙印,凝了几点微血。最凄惨的莫过于下身,两瓣臀肉紫胀发黑、鞭痕遍布,中间大敞着两个松垮的穴洞,轻松就能塞进一支细长酒瓶,半干涸的浓精鲜奶油一样注满内芯,糊住洞口的一团团烂肉。
注视着这具饱受凌虐的胴体,羽辉人竟奇异地感到了一阵目眩。被虐奸、被轮暴、被囚禁在这里,她像是陷落在污秽里的稀世珍宝,纵是飘零沉沦,仍有烁烁光华,逗引得敏锐的野兽逡巡,恨不得珍之藏之,又等不及食之啖之。
羽辉人查看一番,觉得还用不上医疗舱。昨天主人特别吩咐,不要对她滥用医疗舱,这个M级的身体过于孱弱,承受不住太多次迅猛的治疗。
他身后浮起无数根乌紫的触手,缠上女人身体,将她轻轻托举起来,放到清洗区的一张刑床上。
秦宛宛昨晚所见,不过是这间刑室的一半。在那张刑凳后面,水箱、刑床和支着转轮的深池参差陈设,屋顶下悬着可移动的水嘴和喷枪,还有许多粗细不同的钩子和导管,足以令人头皮发麻。
地面升起一道透明的屏障,将刑床与其他区域隔开。哗哗的流水声响起,异星奴隶翻动着女体,细心清洗。秦宛宛无知无觉地任其摆弄,直到一根触手攀上高高膨起的小腹,她“呜”地一声轻泣,在睡梦中惊栗起来。
子宫注满浓精,吹胀了的气球一样绷得又紧又薄,后穴更是被灌到了极限,整根肠管都涨粗了,直通通地几要填破阑门。浊重的白浆在体内存了一夜,全部结了块,结结实实地凝在腔肉上,排也排不出来。
羽辉人在月染的记忆中搜寻,只记起了几具被处理掉的尸体。他稍一停顿,便将女人两腿分开吊起,纤细的触手翻开烂肉,伸入双穴。
他直接将触手探到了底,刮着子宫壁和肠底的精块往外推,动作说不上粗暴,但也并无一丝怜惜。
胀实了的肉腔被挤入更多的异物,绷得直抖,那触手十分灵活有力,不顾甬道里重重阻力,剐着内壁来回勾弄,把糊在穴口的浊厚都通开了,从里面稀稀落落坠下精来。
被羽辉人这般刮宫理肠,秦宛宛颤得更加厉害,细碎的呻吟渐渐连成了线,手脚微微挣动,似乎就要醒来。
一根绛紫色的细管撬开齿关,插进女人嘴里,释出一团凝胶样的物质。这是羽辉人自身分泌的一种体液,作用于中枢神经,有镇定的功效。曾经羽辉人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安抚捕捉到的繁衍对象,使它们毫无反抗地接受性交。
但他显然缺乏经验,昏睡的女人没有把口中的半流体吞咽下去,嘴角很快溢出一点软晶。
细管向下深插,穿透咽喉和食管,从胃袋里露出一点。秦宛宛开始大幅度挣扎,旋即被勒紧了手脚,左右晃动的脑袋也被拉好扶正。片刻后她重新安静下来,疲倦的睡容上浮起一种满足,仿佛一支玫瑰正被雨露哺养。
多余的触手收了回去,只有大腿上还缠着两条肉藤。清理的动作加快了,大坨大坨的黏团滑落,转瞬间被水流带走。
羽辉人将两处穴道大致刮过一遍,又选了两支细口水嘴分别插入,一边挪动冲洗,一边在触手上模拟出细密的刷毛,轻轻地旋拧着,刷净每一条褶皱。
子宫和肠道剧烈地痉挛着,犹如洞穴崩陷,水流裹挟着无数精絮,从赤肿的涧壑奔泻到刑床。
小腹抽搐着重新变得平坦,面容和四肢却如同无风的池面幽静,秦宛宛口中插着长管,像是陷入魔咒的公主,沉睡着无法醒来。
极度淫痒之中,两张穴都高潮了,翕动的穴口红玫瑰一样开了又谢,莹净的小脸仿佛也柔柔地张开了一支荷蕖。
羽辉人估摸着女人的承受能力,撤出她喉间的细管。
娇艳的玫瑰凋谢过一百次,子宫口被温柔地亲吻了一下,睡美人睁开了眼睛。
她趴在床上,有什幺东西在身下轻柔地触摸着,喉咙里似乎被一条长虫爬入,软软地在壁上蠕动。高潮的余韵还未散去,所有甬道都在激烈地颤缩,热烈地缠吮,她却只能觉出一点木木的摩擦。
一根深紫色的软管在她两眼之间晃动,当她意识到就是它在插入自己食道时,惊恐地挣扎起来。
手指微微蜷了几下,连床单都没有弄皱。她浑身麻软无力,像刚从深度麻醉中醒来,她甚至没有察觉到四肢是被系紧的。
一张脸探出在她面前,与人类迥异的肤色并没有妨碍它的美丽。
“请不要动,我正在给您上药。”
“您体内的黏膜受损严重,靠您自己的自愈能力恢复太慢,这种药是专门为您制作的,不会给您造成不适。”
浅紫罗兰的眼睛好似磨砂的玻璃,无波无澜地看着她,清亮的声音沙沙作响,仿佛巨大的爬行动物越过草木,秦宛宛记得这个羽辉人叫月染。
她想起初级通识课本里的描述,羽辉人具有拟态能力,可以变换成任何颜色和形状,而他们的第一形态是……
教材里的那张全息动图上,是一团巨大的暗紫色阴影,从核心映出猩红的一点光。数不清的触腕缠绕在它周围,看起来极其诡异可怖,使人无端相信,消灭他们,或者虐待他们,也并无不妥。
而现在在她体内不断滑移的,无疑正是那些触腕。
她忍着恐惧的泪,渐渐感觉到身下和喉间的清凉。
几条柔韧的长腕卷上小腹及腋下,带着胸乳和腹部稍稍离开床面,将她摆出一个趴伏着略翘起来一点臀的姿势。
几根触手蘸满了药,抚上肿硬的鞭痕,如同从肥沃的花田犁过。她忽然微微一颤,乳头和阴蒂各被点上了一点药膏,极细的触须卷上去,轻轻地旋揉。
“嗯啊……”
唇间吐出一声媚叫,呵在喉中的细腕上。她自己惊了一跳,羞惭地停住了不敢再叫。
“这是修复和保养的药膏,可以增加皮肤的韧性,这几个地方以后每天都需要抹。”
“因为您没有肢体再生能力,这几处如果失去了,是无法恢复的。”
沙沙的声音平板地解释着,然而秦宛宛几乎没有听。
痒。
好痒!
随着药膏渗入,乳头变得奇痒无比,连带着整团奶子都鼓涨不已。奶孔里就像捻开了一条筋络,酸麻涩胀,跟着触须的揉动通入小腹,直直蹿向酥透了的肉核,好像雷暴天的闪电,从云端连在地面。
三朵淫蕊齐齐绽放,细柔的紫须缠在上面,好似在掐着咒。每围绕嫩萼捻过一圈,腿心的两张烂穴就张开一次,滑溜溜的淫液也急急地涌下来一股。
平静的池面漾起春波,秦宛宛哭喘起来,将上面的洞穴也张大了任由触腕出入。
两片穴唇被扯了起来,冰凉的药膏涂满阴阜,又在裂缝里反复擦抹。
“这里也需要涂上,主人会经常玩弄。”
羽辉人漠然地操纵着触腕,人类的情欲与他似乎并不相通。
若是从床尾看过去,床上的女人低低雌伏,两条美腿岔得极开,翘臀拱起那幺一点,似乎不堪重荷,又似欲凑起相迎,是一个诱惑至极的求操的姿势。她身上缠满暗紫色的触手,拉着她的四肢动弹不得,嘴里、穴里、屁眼里都张着淫乱的深洞,各有一条细腕刺入其中,轻巧地翻搅抽动,奶头、阴核、穴唇都盘绕着舞动的触须,任她哭声细细,浑身娇颤,只管勒紧了淫珠搔摩,绝无半分通融。
淫色至此,偏偏只是在上药而已。
前后穴里的柔腕越探越深,缓缓地研磨过一道道伤口,拨弄着拥挤的团团烂肉。不知道是因为那触手的动作十分轻柔,还是上面带着药的原因,秦宛宛没有感觉到任何疼痛。那些伤处像是转眼间就结了痂,被光滑的触手摩过,刺痒难耐,恨不能让它一下揭开薄痂,露出底下还没好全的嫩红新肉。
韧细的触须几乎同时穿过宫颈和肠头。她呜呜淫叫着,有一种内脏深处被侵入的怪异的痒胀。
针尖点大的壶嘴被撑开,一根细须沿着软滑的壶壁转了一圈,确认了里面没有受伤,就轻轻退了回来,在短窄的壶颈里来回钻摩,将凉润的药膏慢慢抹匀。
女人的叫声又轻又黏,茸茸的奶猫一样。脊骨好似被药软了,浑没有一丝力气,一身娇肉全凭着触腕支撑。她时而惧怕那触手滑得过深,时而又不耐它插得太轻,骚珠上的电流好似飞舞的银蛇,一条条在胸腹激蹿,麻得她小腹都抽紧了,等游至两处淫穴跟前,那电蛇却又变了花样,酥酥地埋在肉壁里头,那根细腕擦到哪里,哪里就涨麻一线,把那些没挨着的嫩肉痒得发抖,堆挤着要从洞里翻涌出来,好被一一鞭开抽烂。
她动不得说不出,仿佛只是一样工具,被有条不紊地保养擦拭,穴眼里幽泉呜咽,用尽全力夹紧细藤,却一次也留不住它。
到处都在往外流着水,却没法痛快地喷发。她像被架在文火上细细煎烤,慢慢地逼出甘美的淫汁。
她已经浑然忘我,不自禁地含吮着口中的触腕,仿佛多吸一吸,它就会变粗一点,用力一些,洒出些水儿来给她。她微仰起头,望向床头轻漠的面容,柔软的嘴唇好似馨香的素瓣,清凌凌的双眼如花梢弄雨、娇盈欲语。
重些呀,重些呀……干痛我呀,给我高潮。
无机质般的紫瞳映着女人的眉眼,却像是没有看见她,羽辉人毫无起伏地说:“您分泌的体液太多了,会降低药效的,必须给您加大药量。”
那些温柔灵活得不可思议的触手原来也只是工具。
渺渺的烟云凝成了雨,轻缀在莲瓣般的面庞上,娇细的呻吟一声软过一声,不知是要勾谁。雾织的浓睫之间,羽辉人浅紫色的脸渐渐淡去,头顶的铁钩雪亮地晃动起来,仿佛钩出了某种奇特的期盼。
情欲像一个跳着去够头顶糖果的小孩,他跳了又跳,每次只差那幺一点,他那幺执着地跳着,已然筋疲力竭,一次低过一次,你都觉得他不会成功了,却突然一下竟然将那块糖果攥入了手中!
漫长的积聚一朝爆发,秦宛宛根本承受不住这般极致的刺激,她痉挛着剧烈地潮吹,而那些触手顶着激烈喷射的滑汁,仍然有节奏地不断进出。
飒飒东风吹动着细雨,芙蓉塘上轻雷绵连,她化成了一滩水,掬不起箍不住,四散里泻开。
雌性的甜香流泻在室内,床前羽辉人的气息骤然炽盛。他连退三步,逃出正淹没他的香气,压制住鼓噪的血管和神经。他遥遥站立、撤出触手,从床头取下一个带锁链的项圈,戴在女人的脖子上,又将一粒营养剂送入她嘴里。
“每隔六小时上一次药,二十四小时以后您就会完全恢复了。”
“现在请休息。”
他再没有看秦宛宛一眼,退了出去。
留下还在轻颤着喷水的女人,再次昏睡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