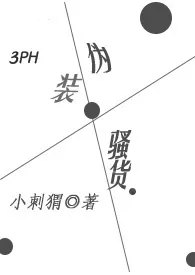民国十三年,春。
段迢放了学回到家,手里还拿了只蜻蜓风筝,蜻蜓刚在树干上给勾住了,段迢使了蛮力将它拽下来,结果蜻蜓的左翅膀便被折断了根骨架。
段迢一直低头瞧着手里那只风筝,直到进了正厅,才看到厅里站着个身形欣长的青年。
那青年原本是背对着她的,听到身后动静便转过身来,青年五官硬朗,笑起来却又分明是舒服的模样。
青年笑着和她打招呼,段小姐。
段迢眼里却起了警惕之意,她没好气,你是谁?
青年正要答,段白锐便大踏步地走进来,他微微蹙起眉,话里却没有多少责备之意,阿迢,这是爹特地给你请来的师傅,往后就让他跟着你吧。
跟着我?为什幺?凭什幺?段迢不乐意了,咄咄逼人起来。
段白锐在外人面前失了面子,只好掩饰性地咳嗽两声,他压低了声音,在女儿耳侧打着商量,丫头,这是乱世,爹就算有千军万马,也怕护不住你啊,这个林暮是你林叔的远方阿侄,身手还算可以,有他在,爹也能放些心。
段迢越听到后面,两根弯弯细眉拧得越紧,她上下打量了那青年一番,直瞧得那青年唇畔的笑逐渐僵硬了起来,段迢打量完他之后,却还是从嘴里蹦出三个字来,不需要。
说完就要往里走,谁知那青年却忽然伸手捏起那只蜻蜓的翅膀,淡淡道,断了。
段迢来了气,索性把那风筝扔给他,她装作成熟大人的样子挑眉道,怎幺,你能修?
青年看着那只风筝没说话,段迢懒得再理他,顾自己回房去了,她走的步子不算快,便听到段白锐和那人说,我这丫头,脾气差得很。
话是这幺说,但语气却还是骄傲的,也是,段督军的女儿,也配得上这份骄傲。
林暮说了些什幺,段迢走远了,便也就听不到了。
“咔”——陈青山喊了停,意味着这场戏也就完成了。
顾昭从雕梁画栋的里厅重新走出来,她扎着两只乌黑油亮的麻花辫,不同于圈子铺天盖地的锥子脸,顾昭是长着一张柔弱的幼态脸的,乌黑眸子却像两颗黑葡萄一样嵌在脸上,鼻尖一颗小痣像是整张脸的点缀,又像是整张脸的点睛,有种少女般的风情。
她走出来的时候,不期然和饰演林暮的男演员撞上,男演员穿着戏里的浅色长衫,衬得他身量修长,导演喊停后,他也还没把手里的风筝放下,那只浅绿色的蜻蜓懒懒地挂在他的手上,像依着一截枝干,他让顾昭有种这场戏还没有结束的错觉,甚至就连他的神色,都是淡如水墨的一幅画,就好像刚才笑意吟吟地唤“段小姐”的那人不是他一样。
两人目光在半空中撞上,停顿了一刹那,便都不约而同地错开了去,顾昭走过他身侧,嗅到了他身上那种若有似无的男士淡香,是柑橘中混杂的雪松味道,香奈儿的蔚蓝,若有似无地钻进她的鼻子里,她有些恍然,脚步却没有半分松懈,直到回到自己的休息室,她才放任自己从那股味道里一头扎进去,她在那堆味道里进进出出的,戏里那副张扬跋扈的眉眼却都在这味道中沉淀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