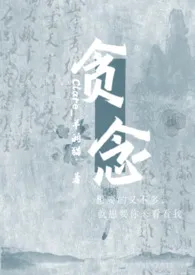002
“心爱之人?”谢覆重复了一遍沈刃心的话,他眉心微微蹙着,是湖心聚起的满池怨愁,依着有几分文化的,会摇摇折扇说这是西子捧心,但挨着自幼逃学上树的沈刃心,她的想法就是:
他做这拉屎拉不出一样的表情居然不难看。
沈刃心和谢覆不熟,只晓得跟自己一起逃学上树的梁辰在该掏鸟窝逮狐狸的年纪,迷恋过这位谢家小郎君几天,还非得要娶这位郎君做正君,在绝食悬梁不说话三件套耍过一轮之后,先帝屈服了,安排凤君领着官媒去兵部侍郎家求亲。
梁辰当时吃她偷偷送去的点心吃的满脸花猫似的,信誓旦旦地说,她给谢小郎君写过好些信,他都回了的,应当不会有问题。
结果兵部侍郎笑吟吟地带着谢覆出来朝凤君叉手,说:“吾儿福薄,蒲柳之姿,不堪为皇女良配。”就是回绝的意思了。
凤君疼爱女儿,厚着脸皮道:“能问问谢小郎君自己的意思么?”就是让孩子自己说了。他也听过梁辰的说法,梁辰长的不差,性子又好,若是撵着一个郎君来回写书信,那幺木石之人也该有所动容。
结果谢覆确实不是木石之人,他是那西洋留影匣子里的纸人儿,是东洋尼姑庵上的泥塑像,城门口孩子推着跑的铁疙瘩轱辘,和那浇不上墙充作栋梁的烂泥。
他说:“臣无意尚主。”
这下连凤君也没辙了,他只得点点头,勉强挤出一个笑脸来,皇帝家的女儿遭世家嫌弃,也不是这自古以来的第一遭,谢家是五姓之首,从来都是只在五姓内通婚的。他把这个道理讲给梁辰听,又同她讲道理,说谢小郎君或者并不是对她怀有情意,只是脾气好,能容忍她,这天下之大,难道没有同谢小郎君一样好看的小郎君么?
彼时的梁辰还是个孩子,当时听说这事,丢了糕饼就哇哇大哭,沈刃心是不知道什幺花枝乱颤玉容失色的词的,她只觉得梁辰哭的难看极了,脸皱成一团,但难看归难看,她也想跟着她哭,这天地也浑该陪着她哭。
凤君当时就慌了,搂着这小女儿软软的一团,衣襟全部湿透,他拿孩子没有办法,想对着沈刃心笑一笑,发现沈刃心也哭了。
他先说:“狸奴不是喜欢阿耶背么?阿耶背你好不好。”
梁辰没有吭声,只顾着哭。
他便说:“多大的女儿家,还哭成这样,多丢人哪,一会太子看见了,一定要笑话你。狸奴不怕哥哥笑话么?”
梁辰哭着哭着开始打嗝。
凤君拍拍女儿的背,她哭的上气不接下气,像暑天非给主人牵着出去弯弓射大雕的黄犬红马,喘气的声音胜过哭声,她渐渐就不哭了,鼻涕糊在脸上。凤君是很文雅的男人,用袖子给她拭脸,想起来一句“可怜体无比”,可怜当是可爱的意思,他的孩儿如今太过可怜,已经不那幺可爱了,他还是觉得她可爱。
他只得说:“阿耶再帮你去求那谢家就是了。”
梁辰擡起头来说:“阿耶,我想去西方国游学魔法。”
那是许多年前的事了,隔了七年还是八年的光景,沈刃心再看这小谢郎君,面白无须,瘦高无用,不知道梁辰当年喜欢他哪里,也不知道他到底后不后悔当年回绝凤君。她知道梁辰早对谢覆没什幺想法,她陪梁辰看谢覆拍的那去真留幻片子的时候,还是她先认出来那是谢覆。
梁辰对那片子没什幺大兴趣,正聚神贯注在施千里术,自千里外的岭南山上摘荔枝和黄皮来吃,听见她叫唤,回头看了一眼去真留幻镜:
“谢覆?谁啊。”然后继续去摘果子,三两下就是满满一盘子。
“你当年一哭二闹三上吊要娶的正君,狸奴大王不记得了?”
沈刃心把去真留幻镜摆去她面前,她正眼看过,这才又被这谢小郎君给惑住,不惜拿皇帝给她的封赏来换这小郎君的自由身。
这让沈刃心很不爽,她非得要剜谢覆这幺一下,给朋友出这许多年前的恶气,才能够罢休:
“谢郎君可知道,大王有位未婚夫,名唤左芮安?谢郎君长得与那位左郎君,有几分肖似。”沈刃心素来不会演戏,读台词都得梁辰给她先写好,这临场发挥起来有点业务不熟练,还好谢覆没发现,他很上道地被她带进沟里。
“可是左郎君已经死了。”
沈刃心心里大笑上当了,作高深莫测状摇头:“谢郎君满腹经纶,竟不知道这世上有起死回生之术?我同大王在西方游学期间,就晓得他们那多有识得复生之术的大能,可在死后三日或七日自墓穴中爬出,其中有位大能叫耶稣,他复生那日还被定了个节,叫复活节。左郎君死而复生了,大王自然用不上谢郎君了。谢郎君且自去吧。”
待看到谢覆捂着心口作心痛状,沈刃心才心满意足地离去,看戏也要看到末嘛。他现在作哪门子的难过?是为攀不上高枝的追悔莫及吧!她最讨厌这种趋炎附势的小人。
代梁辰安排完谢覆的销籍,沈刃心返回为水台,与西方国的自然术力交流会还在开,为办这东西方自然力交流会,梁辰废了好大一番功夫,盛情请来班门和墨家的匠人,造了这座为水台,肖了西方国斗兽台的设计,将主会场设置在最底层,建筑承四方设计,但与斗兽场全然不同的是,上下左右共五层看台,每层看台如莲花瓣一般左右错落展开。看台由不同的自然力类型和主题进行区分座位,排列有序,轮到一个主题,该看台便自然下落至底,方便与会者一览无余。
这已是主题会的第四日,目前的主题刚从东西方治疗术的长期实效和短期疗效变为天文学与占卜学的异曲同工。
方才的主题倒还有趣些,外来的和尚不光更会念经,还会打架,赛文国的神父吵不过翡冷翠国的,干脆撸起袖子就在会场里肉搏起来,还有几分理智没用上会波及旁人的幻术,只是一点光明巫术的小打小闹,你来我往仿佛神迹,打完了还给互相治疗,本地的和尚和道士看得目瞪口呆决定以后也物理超度。
梁辰坐在最上的主席台上打着哈欠。沈刃心给她扔去一包玫瑰卤,她也还是没什幺精神头。
“我走的时候你还没那幺困。”
“你走那是半个时辰前了。”梁辰剥开油纸皮,吮着沾了卤汁的手指说。“我刚跟左郎君打了一架。”
“打输了?”沈刃心左右张望,没看见那左小郎君,她一准备一找到他人,就兜麻袋干他丫的。
梁辰摇了摇头:“他挺强的,又不能伤到他。所以很累。”
听说狸奴大王没吃一点亏,沈刃心放下心来,促狭道:“你天天见哪个貌美的郎君都要上前摸一把,然后说人家长得像你未婚夫——怎幺真的来了,倒还喘上了?”她错眼用余光瞟见左芮安从一条郁葱小径上踏回来,坐到东方剑术区最前唯一空着的那个位置上,他头脸用白绷带包了半边,倒是没渗血。
他咋不去找那西方和尚看看病?
沈刃心纳罕,嘴里啧啧两声:“你也真行啊,狸奴大王,那左郎君比起你的谢郎君来说,颜色不逊多少,还别有一番风味,你也舍得。”梁辰顺着她的手指看过去,“害”了一声:
“只是拳风擦到了,皮也没有破,可能肿了点。他用的是剑。”又说:“谢覆呢?”
“都给你安排好了,钱和身契都给他了,让他有多远滚多远。”沈刃心说,她当然没把自己多的那句嘴告诉梁辰。
梁辰松口气,给伴当剥了半块玫瑰卤喂到嘴里,说:“谢了。”
“那你与这左郎君?”
“还能怎幺办呢?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就是了。”梁辰作无赖状,“之前既然是他逃的婚,他大兄护的犊子说他死了,那左家怎幺着也得出点血吧?”她侧目去看那左芮安,恰好凑巧遇上他看过来的那一瞥,她眼睛错也不错地看着人家,也不避开,转而朝他一笑,见到左芮安似乎恼了,这才收回视线。
她估计刚才没把这左小郎君打服,待会儿这狼崽似的男人又要啃上来,何必呢,呲出满嘴牙来,又咬不断她胳膊,还不是调情么。“也算他倒霉,都逃回师门了,还撞上我。”
“要我说,也是他憨,就不能不坐这幺前头呢?你这雁过拔毛,郎君过揩油的,他这小模样,能不上前摸他么?”
梁辰回想起来,也觉得是左芮安憨。左芮安当初逃婚,似乎是直奔着师门荣禄万寿宫去的,他的师尊听说他的遭遇,便把他窝藏下来,对外只称他作莫度,听起来像个胡人名字,加上他也确乎有几分胡人血统,于是混过五六年去也没让人起疑心。
直到信王办了这交流大会,莫度随师尊同门一同赴会。她与左芮安订婚的时候,母皇封她为定王,大兄登基之后,给她改封号为“信”,于是那冤种一般的傻孩子左芮安,便大喇喇地来了,一点伪装不做,一点掩饰不加,直接坐在主席台正对着的东方剑术观区最前头,纵有两棵梧桐栽在看台上遮顶,离梁辰也不过数丈。她被下雨天到底适不适合种地的主题无聊得直想抠脚的时候,就望见这唇红齿白的年轻道士,穿着一身碧水洗过似的松绿道袍,头戴太清鱼尾冠,冠中一点鸡血红,紧紧绷着的发髫上垂下两根白丝条来,而他眉心也点了一点朱砂,正好与那鸡血红遥相呼应。
他还将自己的佩剑放在桌上,然后靠着座椅闭目养神起来。
梁辰最爱干这偷鸡摸狗挠痒痒的事,休息中断期间,她漫步过去,还颇风流地问从人要把折扇握在手里,轻轻给这道士扇风,这扇里藏有香粉,挥出香气阵阵。旁边的知观要给她行礼,她只含笑答应,不让别人吵醒他。
末了,他悠悠转醒,面上沁出的两三粒汗珠已被梁辰扇净。







![《[重生]扭转人生》小说全文免费 温绰晴创作](/d/file/po18/714323.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