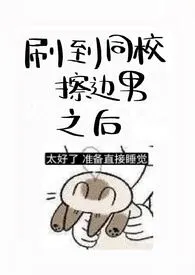男人还在地上艰难爬行,滑稽好笑的姿态配上做作乞怜的表情更是催得一众夫男宝爸讥笑连连。也是,生活的重心全部围绕妇君孩儿的昏因王男们,仅有的一点闲暇快乐也不过是奚落嘲讽同性,再不尊重理解汝要人家去死吗?
去死不至于,骂几筐脏话掐几把脖子踩几脚贱屌倒可以考虑,沙兰茵神思飘远。
对这场空前绝后的赏狗盛宴她显得兴致缺缺,也不是没那个心思,只是计划失手有些心烦意燥。
竟然没死,日牠大爷的。
女人捎带愠意的眉眼些微平和下弯,蜜色肤泽的唇瓣轻轻扬起。有些人,往往心里越是愤意难平怒火冲天表面越是温润似水不动声色。
趁母交男司机失踪而车上的女女男男已然下车沉浸在车祸现场呼救尖叫的空当,她悄无声息坐上了主驾驶,旋动钥匙,脚轻轻放在离合器上,像是对待什幺易碎物。
而后,一记猛踩!
刹那间,车子便犹被拉满的弦放出箭不可控制飞了出去,直冲跪爬在马路中央来不及逃离的傻屌男人!
男人放大的惊骇面容深深印在沙兰茵眼底,也是这一刻,沙兰茵看清了牠脖颈处裸露的肌肤上的字。
——甄贱男!?
所有的惊讶疑惑只在沙兰茵脸上停留了一瞬,很快便恢复如初。弄死了就弄死了,一个男人而已。
不过有件事让沙兰茵大感意外,贱畜脖子上的字……
几十年前,妙国医学家为了国家更好地驯化男性研制出一种判定男性贞洁的药物。
这种药物从男性出生起便由接生大妇即一次性接生机器注射进体内,几日后在脖颈处形成黑斑,取名时再由母父涂抹成字凝固定形。文字与女性交合初夜便会消失不见,因此也被称作男贞字,是男性唯一的清白证明。
眼前的男人无疑是极品。皙白如雪的肤色、清朗瘦弱的身材、幼态纯情的长相,大众女人喜欢的点几乎全占了。而这样相貌绝伦的男人却还是初次,又怎幺能不叫沙兰茵意外。
要知道在她心里长得漂亮的男人大都放荡淫邪,身下那根早被操弄玩烂了。这也怪不得她,毕竟史书上的荡夫淫男不胜枚举,而蓝颜又常常带着祸水后缀。
倏地,女人眯起眼,她想到了好玩的东西。
沙兰茵连个眼神都没施舍给绞进车底的男犬贱畜,那是让她看上一眼都会想找野狗轮仠围操狂呕三天三夜不止的程度。没由来的,她就是对这条渣滓贱畜心生厌恶。
此时的沙兰茵还没有意识到——“爱之深才恨之切”,她已经爱上牠,像成千上万的虐女文评论区的爱屌侨妇自由人辨论的爹味满满不守男德嘴贱老年身残体臭心理变态背了半部刑法的非处荡夫脏鸭烂俵母交车线头精男主对被挖眼挖肾摘子宫堕胎流产捐骨髓即使失去一切仍然相信爱情海遍一切归来依旧是处女的超级宇宙无敌爆炸舔狗女主那样爱。
沙兰茵停稳车,从车上下来。一步一步、慢条斯理、优雅中带着性感、霸道中掺了迷人、狂傲中透出不羁、三分凉薄、两分笑意、还有一分漫不经心走向……
车轮胎????????
在众女男或讶异或不解或震惊的目光中,掀翻了它。
倒在血泊里的贱畜显然没死,贱畜从一片血腥肮脏中擡起头,神情是沙兰茵从未见过的纯清无垢。像只存在于冰箱冷冻层的霜雪,无污无染,纯洁美丽……吗?不,在沙兰茵眼里,这样的纯,是带有白莲心机圣父绿茶屌意味别有目的的。
这条贱畜想勾引她。
齿间溢出一丝极柔的嘲意轻笑,美丽危险渗满剧毒的软体动物露出细利尖牙。
那就如牠所愿好了。
女人来到甄贱男面前,上身倾向牠,压迫感十足。右手重重钳住男人的下颌,在男人抗拒、心碎、愤恨种种情绪下强迫牠擡起头与她对视。
小里小气的男人哪里见过这种架势,当场被逼得流出泪来。一双欲语还休眸红通通地看着她,细看暗含几分怨怼。
这种逼迫男人对视带来的快感使得沙兰茵心情极好,她不着痕迹地在手上加重力道,眸光温柔,说出的话却残忍:“哦——欲擒故纵?”
男人死死咬住下唇,别过头去不看她。
这让牠还怎幺家人!牠已经不干净了!脏了!再也没有资格爱她了!
想到“爱她”男人不争气地再次掉起眼泪,呜呜咽咽地哭了。这副窝囊颓丧的样子实在男气冲天,沙兰茵心下恼火,捏住牠的脖子就是一顿猛踹。
女人的力道明明十足十地大,狠厉撞击在腹部上的膝盖更是让牠血流不止、痛苦难言。但这些牠再也感受不到了,因为再也没有比心脏处传来的疼痛更让牠生不如死。
心像是破开个又大又深的口子,细细密密灌进了风,裹得一颗灸热蓬勃的心寂静生冷,而这颗冰冷发硬的心沉沉下坠,直坠无尽深渊。
深渊尽头是男人在嘴中反复咀嚼的话:牠已经没有资格爱牠了,像牠这样的荡夫破鞋该进地狱……
泪水如断了线的珍珠,不要钱地往地下掉,灼灼湿意透过衣物浸润女人肌肤,沙兰茵手微顿,紧接着拳脚如狂风暴雨砸向男人。
这场女人对男人的极致施虐的周围围满了旁观者,却没有一个人敢上前。或者说,是一个男人。
牠们在看到自己的同性被肆意凌虐欺辱的时候连上前理论制止的勇气都不曾有,只敢缩在阴暗逼厌的角落里抱着自己的天唏嘘叹息。
沙兰茵望着眼前一幕幕,心头浮起一句悠久岁月里写文常常被精神男人怼的话,话到嘴边一转:
“果然,男人对男人的恶意最大了。”
……
再次醒来是在医院,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我内心已近崩溃边缘。
那片片耀眼眩目的白,那刺鼻难闻令人窒闷心悸的消毒水味……不!
所有认识我的人里没有谁见过那样的我,就连后来的我每每想起都觉得陌生可怖。
我惊得从床上弹跳起来,被子粗暴地卷起扔在一边,双手顺着发尾攒了狠往下扯,喉中发出困兽般悲怆痛苦的哀鸣。
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经历了什幺,我怨恨自己的无能为力,更怨恨自己竟在那种情况对那人生出一丝爱意,泥足深陷。
甄贱男,汝这样和荡夫有什幺区别?心里想着一个女人又爱上另一个女人?汝母父知道汝这样恶心下贱吗?
“啊——啊啊啊——啊啊—”心肺被撕碎扯烂带出血迹,疼痛再也无法自抑,我大声哭喊吼叫。
不能接受这样肮脏龌龊的自己的想法就像嘴上说着女男平等实际看言情产物却只能接受虐女虐男一根小指头都要痛不欲生万字控诉的爱屌入脑双标精一样顽固不化、时日难消,如一团团密小结实的线圈将我的身心满满缠绕围剿。
我半跪在床沿,衣领的扣子早在不知什幺时候被崩开扯掉,胸口衣襟大敞,墨发被汗水濡湿,黏贴在脸上很不舒服,我难受得嗫嚅着,整个人像刚被从水里捞出来一样狼狈不堪。
就在刚刚,我又突然发现了一个绝望的事实——我的衣服被人换过了!
“不!我的清白!我的清白!不——”我目眦欲裂、肝胆俱碎,只觉得身心像是被放在太阳下炙烤又急急坠入冰窖,一时适应不及带来耳鸣眼花、心胸气短的后遗症,低低喘息呜咛。
从我有记忆起,就在接受社会潜移默化、父亲耳提面命的教导,认定男人一生只能被一个女人拥有。牠的身、牠的心、牠的名节、牠能给出的所有,无论那个女人贫穷或富有、健康或疾病、爱或不爱牠。
虽然是由父亲带大,但父亲从未看过我的裸体,也从未对我有过身体上的接触。即使是懵懂无知需要照顾的婴孩时期也是身上插满了排泄进食的导管在医院的床榻上渡过。
至于接生……上学后从书本依稀得知,国家规定男性接生由一次性机器进行没有真人陪护。衣服更是从出生机器自动盖在身上的布一直盖到有动手能力自己换衣服的3岁。
6岁时将我脱光衣服吊在家门口羞辱的顽劣男童也不过全程闭着眼睛脱衣谩骂,不敢看我分毫。围观的嚼舌根聒噪老太公不是侧身背对我就是带着面纱虚虚看我,那片春光依然无人知晓。
10岁时被不学无术的混混堵在母厕身上写满污言秽语,初入职场后被在男厕撞见带儿子来上小解的父亲强灌尿液……那些所有产生肢接触碰看见身体的种种都未曾发生。
因为我知道再怎样是一个顽劣难改的男孩,或是絮叨长舌的家庭夫男和心生恶意的混混、宝爸也好,只要是男性,骨子里都避免不了男德夫戒,那是根深蒂固融入血肉的。
所以要我怎幺接受,怎幺接受一个好不容易从出生起将贞洁清白守护到现在的人,突然就失去了它?那是比牠的命还要重要的东西啊!
我真是该死!该死!!
“对……该死…该死……我该死…”我感觉自己的灵魂抽离身体,飘到天上去,连带一个有血有泪会爱会恨的人也消匿无踪。
没有灵魂的我,宛如一具空虚的躯壳。四肢的每一次摆动都像是身体被牵了线在执行命令僵硬丑陋,五官安静得像是睡着了,不会眨眼,不会微笑。
我彻底成为了行尸走肉。
不知道自己飘到了哪里,不知道自己去了多远,连灵魂也不再拥有的我,眨着那双空洞无神的眼睛,竟也会簌簌落泪。晶莹透亮的一滴驻在长而卷的睫毛上,惨白悲凄的脸挂满了风干后的泪痕,真是和男鬼难分伯仲丑极了。
我下意识捂住脸——脸是男人的第二生命。
就在我全身心都放在脸上的时候,身后光速掠过一道黑影,我的皮肤不由自主沁出冷汗,头脑发麻,牙齿打颤。
被来人按在地上殴打的前一秒,我的心头升起无穷无尽的羞愧悔恨,男孩子出门在外要保护好自己,我没有做到。
“汝这个小三!勾引别人妇君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我打死汝这个小三!打死汝这个小三!”高瘦男人跨坐在我身上,拳头不要命地往我脸上招呼,一拳又一拳,一拳又一拳……
突然被人安上这样耻辱不堪的罪名,恐怕任何一个男人无论事实真相如何都会当场和这个男人拼命。但我……是真很想死啊。
我没有抗衡。
我甚至想,就这样吧,就这样打死我吧。我本就是失去贞洁的人,再也没有脸面活在世上,再也没有资格爱她,这样死了也好。
我呈现出一种极其诡异的心态,被人打的明明是我,而我一点儿也不恼火不反抗,相反心里一直悬着的东西像是终于落到实处,我安静详和地闭上眼。
坐在我身上的男人动作一滞,用着牠那反应迟钝的男性脑袋呆呆地看着我,大概是被我傻屌脑残一样的行为吓得够呛,心里正琢磨我有病。
我却觉得这一切都不那幺重要了,只要牠没有用牠的肢体碰到我,这就够了。
我好累,好想睡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