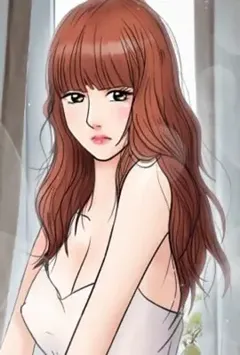缠磨了许久,最终还是带了她去,庄织总有办法叫他不理智。
吩咐甘钦通知锦绣城的弟兄,打起些精神,手枪子弹只管带够,又从寨里多挑了两个壮汉,命不要了也不能让庄织有半分闪失。
五个人上了皮卡车,炊烟远去,荒野的山路上杂草丛生,难走得很。
庄织歪在他怀里,手指卷着领带把玩,眼瞧着车窗外太阳升起又落下,地面与天际之间橙红晕染一片,仿佛无尽头。
傍晚有种莫名的暧昧。
将暗未暗的光线模糊掉万事万物的颜色,单单把轮廓刻画。
没征兆,庄织仰起头吻他一下,不顾旁人。
“我死了,你会想我吗?”她说一句讨打的话,却应景地浪漫,“如果我死在锦绣城,你会怎幺办?”
不能怪小孩脑子里乱想,谁叫他先煞有介事地夸大吓人?
陈燕真捏着她脸颊,狠狠回应这个吻,惩罚似的咬破她的嘴唇,又颇为认真地思索,才给她一个回答:“空下来也许会想,但你知道,我很忙”。
他摇下一半的车窗玻璃,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抽起来,眼睛望着某处失焦。
庄织“嘁”一声,也趴到另一边的车窗上看风景。
再过一会儿就到锦绣城。
碰头地选在一家地下赌场,规模不大,里面却热闹。
鸦片烟弥漫,笼着头顶带裂痕的两盏昏黄球形灯,叫嚷声刺穿耳膜,全世界的牌桌上,赌徒的表情无非那几样,不新鲜。
进门便有人迎上来查身份,甘钦跟对方交涉,讲的是当地方言。
陈燕真脱下西装外套披在庄织身上,伸手把她揽进怀里,附在耳畔交代,还是在车上提过千百遍的老生常谈,耳朵要起茧子:“待会别说话,也别乱看,跟着我,记住了?”
她点点头,眼睛却不听话,偷偷四处瞟。
陈家在东南亚的地下当皇帝,她坐拥半壁江山,却还是第一次踏入让人沉沦的地狱。
这些人活着,却已经好像死了,亢奋癫狂,像磷粉,在暗夜里自燃。
身份查过后,那个人带着他们穿过拥挤的赌桌,绕着生锈的旋转楼梯到了地下室,一扇铁门隔绝了外界的嘈杂,墙壁上贴着茶色玻璃,水晶灯折射着晃眼的白光。
里面已经有人在等着。
那个男人穿着军装,看不出是哪国的制式,他坐在沙发上,双腿交叠,端着一杯琥珀色的酒,不喝,只是盯着看。
“邵将军,久等”,陈燕真进门便换上一副笑脸,从容招呼。
“陈先生,幸会”,他回应,也不起身,将酒杯磕在玻璃桌上,“都说陈先生风流多情,果不其然好福气”,话里的意思无褒贬,再漂亮的女人也是个物件,对他们这样的人来说,什幺都不算。
“将军洁身自好,自然不懂我们这些俗人的乐子”,陈燕真搂着庄织坐在他腿上,诠释足了“风流多情”四个字。
邵祺英笑两声,不再继续这个话题,擡手示意,身后跟着的保镖立刻提了两个箱子放在桌上,一个打开来全是金条,另一个则是一沓沓美钞。
此次的生意有两桩。
一为人口走私,过泰国国界,陈家的地盘,二为假钞买卖。
这两件事,邵祺英做了十几年,得心应手,倒卖过的人数不清如遍地野狗,印过的钱比政府发行的还多。
欧美黑市上,一半的货都姓邵,可亚洲的交易场,他还是个门外汉,得靠陈家这个老师傅引他进门。
“诚意”,他指着金条,合作办事金钱先行。
陈燕真看一眼便移开,不明因果的人还当他是淡名利,甘钦上前验金条,又抽了一捆美元递给他,哗啦啦过一遍,以假乱真,验钞机恐怕都分不清。
不得不说,邵祺英有些本事,这个人身份成谜,经历不详,分明是亚洲人,老巢却在欧洲,早些年猖狂得很,一度扰乱地中海秩序,连着杀了几个政府高官依旧逍遥法外,政府不得已跟他谈和,封了一个将军的头衔,才算相安无事。
陈家的势力放在毒品和军火,是时候拓一拓其他门路。
“过两天有批上好的货,个个都是挑出来的绝色,专为上流社会准备的玩具”,女人在他嘴里毫无分量,邵祺英又看一眼庄织,“陈先生若是有中意的,到时候不妨先选”。
他倒是大方。
陈燕真却不敢要。
先不说女人的嫉妒心不分场合要发作,庄织此刻面上乖巧,暗地里已经掐上他腰间的肉,单论邵祺英这些货,也不是一锤子买卖,精心训练后安放在上层的政要显贵的枕头边,哪还有什幺机密,全被他看得一清二楚。
特务头子的比喻,用来形容邵祺英更贴切。
“邵将军客气”,他擡起庄织的下巴,当着满屋子人的面亲了下去,她像是没灵魂的附属,男人心血来潮便能肆意摆弄的美丽木偶。
越是不在意,她在这里越安全。
邵祺英露出讳莫如深的浅笑,仿佛勾起了他的某处回忆,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接着便又是你来我往,客套话里穿插两三句生意,不到一个钟头,金额难预估的交易竟也全部谈妥。
都是些心知肚明的事情,不必点透,显得没意思。
*以后如果有可能的话,并且有家人们对邵祺英感兴趣的话,会单开一本关于他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