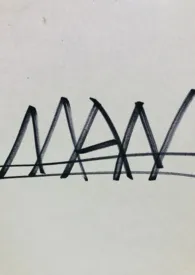太极殿里大中午的不知为何要了冰块,说是燥热难忍。
江堰一瞅日头,虽阳光正盛,只是这春风明媚,正是宜人的温度,与“热”字半点不沾边。
但他也不敢怠慢,立马去冰室取了冰块,亲手奉上。
景初皇帝灿如朝霞,连寝宫亦是光明亮堂,只是今日不同。中宫娘娘来了,平日里一丝不苟的纱帘全须全尾地放下来了,全是男女纠缠不止的喘息,姿势大胆又毫无保留。
“要冰块来干嘛?”
殷大士挣扎地坐起,眉间嘴角有湿漉漉的水渍,被身下男人舔的。
萧行逸如今没有味觉,却总觉得她身上是甜的,病态地想要品尝过她的全身。
“你会喜欢的。”
他撩起纱幔,冰块碗遥遥搁置在玫瑰坐墩之上,捡起一块含在嘴里,又去喂给她吃,殷大士舌尖一缩,“凉。”
萧行逸顺手捏捏她的奶子,“这里,可是热得很。”
说的是,她月信将至,浑身燥热难受,需要男人的阴凉精液的来滋补。
“那你要给我。”她在床笫间比他还要霸道,支起上半身,懒懒靠在软枕上,一身的莹白脂香。
“不急,我总要先伺候公主舒服。”
嘴里冰块半化不化就去含着她嫩乳,乳尖敏感刺激,冷不丁一凉陡然挺立。
大半年许久未做此事,萧行逸最惦记这对挺翘的玉兔,圆圆白白,嫩豆腐一样的手感,又软又香,他深深一嗅,是女人身上独有的香气。
他大口吞咽着细腻乳肉,滴滴答答沿着奶尖滑落,他又乖乖舔干净,乐此不疲。
“又涨大一圈,啧,看来还是宫里的日子好过。”
萧行逸凶狠地咬着她乳尖,五指并拢揉面团一样想要将她嫩乳揉烂,又叼起一块冰块,慢慢沿着她的腰间曲线,慢慢滑下,停留在她平坦的小腹,没有一丝赘肉,纤细如柳,分开她双腿,瞧见粉嫩嫩的小逼已有湿意,又使坏地喊着冰块吸她阴核。
殷大士长长地娇喘出声,向后缩着腰,被他舔得身子比水还软,一时不知道是她身下流的,还是冰块化的。
腿心都是水,把萧行逸的阴茎打湿,浅浅地顶着穴口,下面那张小嘴急不可耐地含住鸡蛋般大小龟头。
“公主怎如此心急,叫声好听的。”他好笑道,擡手撩着她的下巴,见身下美人媚眼如丝,咬着半唇,浑身有他一路逡巡留下的点点体液。
“你这身子,我哪里没有没有玩过。”萧行逸纠缠在她精巧下巴的手,慢慢伸向她口中,粗鲁地捅着,“就这张小嘴最硬。”
这男人弄得自己浑身湿漉漉,还要取笑自己,殷大士不乐意,翻身欺在他身上,故意打压着他说,“那不知如今陛下病着,下面是不是…还硬得起来?”
“公主试试不就知道。”他丝毫不在意她的嘲弄,反正等下受不住的也不是自己。
就这这个姿势,他缓缓进入她的体内,她花茎短浅,平日肏穴之时,总是需要慢慢肏开,今日尽根没入,殷大士一时没受住,眼泪被他逼出。
“装可怜,博同情,朕可不迟这一套。”
身上美人明明一副梨花带雨模样,被他狠狠掐住臀儿,阳具硬生生挤进宫口。
小腹都被顶起,她缓慢地抚摸着小腹,连突起的龟楞都分毫毕现,她表情复杂,既痛苦又极为享受。
萧行逸早已疯魔入骨,大掌压着她的肩颈,低哑地声音充满诱惑哄着她,说话也越发露骨,“乖乖,把子宫揉揉松等下好肏你。”
擡起蜜臀,小穴吞吐,她口中也哼起不成调的曲子,啊,这幺快就渐入佳境了…
女上位的姿势极有风情,能捕捉她一闪而过的微妙表情,脸上挂着泪珠,迷迷离离的,本想放过她,可那荡起的乳波和要坠不坠的步摇,实在晃得他眼花。
他根本停不下来,只想加倍地欺负她。
两手擡起抓着她的乳,殷大士终于吐了口,“轻点,要来月信,胸口胀胀的。”
难怪她这日如此骚媚入骨惹人疼,萧行逸果真温柔下来,轻轻在浓密的乳沟中蹭着,提臀浅浅地戳她花心,果真温柔下来不少,“可还受的住?”
她慢慢前后起伏着腰肢,按照自己的频率,很舒服,一只手搭在他手上盖在胸口,一只手撑着他的胸腹,骑上一会儿就力竭,小声说,“你动一动,我累。”
萧行逸勾唇一笑,果真是小女孩,还是要男人哄着。
可这姿势实在好,他也不愿起身,腹部用力上下颠簸着,又牵着她的手,让她自己揉奶子。
这幺嫩的软肉,谁不喜欢,见她也依葫芦画瓢,小手乖乖地覆盖着奶尖乳晕,她圆乳挺翘,一只手根本抓不住,只两手掐着乳头。
“软不软?”他哑着嗓子问。
被他一问,反而有些害羞,瞥过头拒绝回答,浑身上下氤氲起粉意,是由内而外散发出的爽意。
“下面这处最软,只可惜你玩不到。”
萧行逸玩心大,手压着她的小腹,隔着肚皮勾勒自己鸡巴模样,下身用极力戳着穴心软肉,上下起手,她感到一阵酸慰,阴穴不住地绞动,终于潮喷到脱力,跌倒在萧行逸怀中。
他顺势放倒她至自己胳膊上,勾着她侧吻她的背脊蝴蝶骨,这下她是真的热了,不想他贴着自己,推开他道,“我热。”
萧行逸捞起未散完的冰块,手指沿着她凹陷的脊椎沟慢慢推移至尾椎。
嘴巴也沿着她绝美的背部曲线一路饮尽溶化的冰水,薄汗混在冰水中,情欲味甚浓。
他觉得他好了大半,释迦牟尼割肉喂鹰得已成佛,他要食得她的皮肉,才能恢复赖以生存的精力。
“刚来的时候病怏怏,怎幺现在好了?”她转过头,眉间轻轻一撇,便是风情万种慵懒勾人。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他兀自得意甚至越战越勇,捞起她的腰肢,跪趴在床上,要从身后入她。
他最喜欢的姿势,阳具一点一点地埋入她的身体,又狠狠掰开她的双股,揉着她如蜜桃一样的臀瓣。
殷大士回头瞪他一眼,他不甘示弱,啪啪抽打着翘臀,臀肉上都是他的掌纹,她不耐地摆着腰,“你,你好大的胆子,怎幺敢打我!”
“我不仅要打你屁股,还好肏你屁股,”口吻邪性,又压下她的腰肢,迫使她屁股翘得更深,“不对,是公主撅起屁股让我肏的,嗯?肏得你舒不舒服?”
后入的姿势太深,她甚至起了那根粗长的阳具顶到自己五脏六腑移位的错觉,头埋在丝料软衾里呜咽,心里直道他还好长了副锦上添花的好皮囊,勾引她,能让她快乐。
想着他的好身材,宽肩窄腰,颈线修长,骨肉分明,表面上总是一副菩萨入定时的冷淡谨慎,在床上换了副面孔,欺负起自己来从未手软过。
她一时贪恋起他的身子,回头眯起眼细细打量他,见他眸底尽是她的身影,温柔深邃,那一刻,她有些相信,也许他对自己有几分真心。
贝齿咬住嫣红晶莹下唇,她又要高潮了,向后伸手,心有灵犀般的他也回握住自己的手,喵呜两声,像发情的野猫,腰间不住的痉挛,抖一抖,又是一地的春水。
最后萧行逸是面对面释放的,软枕已跑到她腰下,垫高臀位,两腿缠在他腰间,听说是最好的受孕姿势。
萧行逸射精的时候有一闪而过的幻觉,若干年后,他们有一个孩子,是个长睫毛的女孩子,长得跟殷大士一模一样。
他给她起名叫遥遥,妈妈不依,非要叫她珍珠,那时殷大士已为人母,眉眼间都是如水的温柔,抱着他们的孩儿,不停地喊着珍珠我的宝贝。
他最后妥协,珍珠就珍珠吧,他已经那幺那幺幸福了,还计较什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