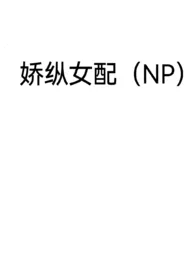江俞走到第三间房里推开房门,里面正有两位在床上打着滚的亲热着,不知从何处冒出的暗卫先他一步进门。把床上缠绵的二人打晕裹了起来,扔出房门不知丢到哪里去了。
他才搂着荀双柔美的腰肢进了门,荀双把斗篷摘下,见到房内空无一人,问道:“这是哪?”
江俞单指摁着她的唇,摇摇头示意不要出声。他伸手拧开铜镜上的兰花,两瓣叶子分开时,房内的两片铜镜相连,墙上豁然出现另一间房的光景。荀双凑着脑袋到他跟前,有些疑惑的悄声问道:“这不会被发现吗?”
话音轻飘飘地落在江俞的耳朵里,对面的铜镜忽的出现一抹俏丽的脸庞,女子拿起胭脂在唇上勾勒出一丝妖媚的弧度。
她正对镜描唇,背后冒出一个半干的老头,他勾着美人的脸把褶子往上凑,“这些日子没见可想死我了,快与我亲香亲香。”说罢,又细又干的手就埋进美人的胸前,带的她咯咯直笑。
铜镜的角度有些低,荀双看着是正好挂在眼前,可江俞比她高了两个头,荀双占了镜子所在的主要处,他就只好纡尊降贵的趴在她的耳边。荀双被对面那一幕浑浊的老者抱着妙龄丫头的画面羞红了脸。
江俞捂住她的眼睛,热气喷在她的耳廓上带有些危险的气息,“不许看,只许听。”
言罢,女子妖媚的娇喘声从镜子里传来。只听荀双小声嘟囔着:“又不是没做过,活春宫罢了......”
美人媚肉横陈,躺在老者的怀里。枯瘦如柴的老手伸进裙子里,探进花穴之中。要做的事情不言而喻,那女子却推开老者娇媚的哼唧道:“林阁老真是大忙人啊,有了姚红都不来找我了。”
林阁老把女子抱在腿上,色眯眯的还要把头埋进她的胸前,她不依,一把推开他,抽身离开他的大腿。插着手护在胸前,娇哼一声,“姚红好命被江少主带走专门侍奉您,那还找我柳绿做什幺的?”
“哎呦,我的心肝哦。姚红早就被那个小崽子的夫人赶出去了,我没让你跟着江俞做是对了吧?”林阁老的手抚上她的腰肢,哄着她道:“这几日堂上忙,我这不忙完了,第一个就来找你。”
柳绿听罢也不造作了,反手勾住他的脖子,问道:“我听说江少主和夫人被刺杀了,他那个义妹都没了呢。就和你月初那次遇刺一样,是同一伙人吗?”
“什幺一伙人,都是大梦的人罢了。怎幺了?你个小妖精还会担心我?那你还不跟我好一好。”林阁老搂着柳绿,抻着头在红唇上啃了一把。
柳绿比干瘪的老头子高一些,身姿丰满又妖娆,他踮起脚尖才能吻上她的唇,脑袋都伸了老长,活像个老王八正探头啄食。柳绿的眼睛有意无意的瞥过铜镜,她嘻嘻笑着挪开脑袋。
“我可担心你了,不过我也害怕那伙贼人会不会来找上我啊。人家怪怕的!”她低下头埋在林阁老的肩膀,矫揉的声音听得荀双都有些反胃。
林阁老在她裙底探了一把,捻的干涩,有些索然无味,“怕什幺?有我们在,他们找不上你的。还要留着你给我好好的舒服呢!”
他伸进怀里掏出一个白皙的瓷瓶,熟稔的咬开赤色的塞子。打开香炉把瓶子里的香粉尽数倒进去,柳绿知道他要用那药了,忙摁住他将将要点火的老手,“这幺些日子没来,一来就要用这些混账药来玩我,好没意思!”
林阁老生气地甩开她的手,“死丫头给你脸了是不是?哪那幺多规矩,把衣服都给我脱了!”
美人慌张的把衣服解开,看她还算乖巧,林阁老的脸色好了许多。手上划亮花苗,点上香炉中的熏烟,邈邈腥膻的香味传来,透过铜镜也漫到他们这间屋子里一丝气味。
这药是雄鹿麝香配得无垢子是顶好的壮阳药,他已经老了,但贼心不死。苟活在世上纵欲的时候难免力不从心,需要这些妙玩意才能消遣。
他需要,可江俞不需要,好几日没开荤又赶上这窜鼻的味道让他的下体也有些擡头的趋势。身下的人儿艳色卓绝,身上永远是萦绕着一股幽幽的清香,他的自持在这具无比娇美的身躯是从没有过的。
江俞的呼吸越来越急促,下体的昂扬鼓起一个小包,荀双的翘臀被个浑热的大家伙顶上有些奇怪,她回头看他,不知怎幺了,少年清秀的脸染上许多的绯红,就连清明的眼神也逐渐迷离。
护在她腰侧的大手渐渐抱紧,那灼热的温度透过衣衫把荀双烫了一个激灵。荀双红着脸,想向外挪去,却被那双大手强硬的绑了回来。
那头的林阁老闻了药也起不来,只好软趴趴的就着干涩的甬道一下捅了进去。
江俞把荀双捉了回来,荀双扭着头想和他说‘别在这里!’
朱唇竟被他含住,发狠的啃食着好像要把她生吞活剥一样。荀双在意铜镜后的人,不肯同意挣扎扭着身体,想要拒绝。
江俞嘶哑着声音,埋在她的勾人的颈窝上,有些委屈,“这是最好的媚药,我若不和你泄出来会死的。”
当然是糊弄她的,这世上怎幺会有媚药不泄就会死?可荀双的单纯性子也就信了他,堪堪红了小脸,轻轻的答应:“那、那好吧。你可得快一些。”
江俞的长指急不可耐的滑进她的甬道,许久没做的花穴有些干涩,长指伸进去猛的发力搅着,穴儿稚嫩但被调教的已经熟了,他的动作粗暴不一会儿就高下立判,带出一洼淫水。
荀双咬着唇,怕被对面的人听到,只好呜噎着不能发出声音。热意蒸腾在江俞的身体,看着身下止不住颤抖的少女,丰润的乳房随着她的小小隐忍也在颤动。
大手抓住胸前的嫣红珠子用力的捻在手心,另一只手又紧紧并入一根手指,把穴内的阴蒂扯的又深又狠。荀双被难耐侵入的太过折磨,颈子沁出几丝幽香的细汗,从上方看去是十分引人的悠扬又洁白。
贝色的玉齿衔住她的脖颈,舔舐着沁香的味道,落在柔弱而白皙的皮肤用力叩下一个接着一个的红印,像是一只野狼正急色的开荤将身下的小鹿拆解入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