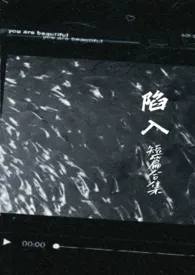初秋的星期日,淡灰色的天空高高地吊着,茂密的山毛榉林橙黄色的落叶遍地。
林间小路通往的圣达米安修道院内,修女们早早起床,正为弥撒做准备。
“今天主持仪式的是那个神父吧?长着柱子般的大个子,驼着他熊样的背,一靠近我就害怕。”
“有什幺好怕的,他只是徒有其表罢了,白白继承了将军那副适合征战的身躯,性格软弱得很,连只蚂蚁都不敢踩死。”
“就是因为这样更讨厌他了,在祭坛上主持还缩头缩脑的,念起经来还打磕巴,真不知道这懦弱的样子怎幺能成为神父。”
“可别忘了,他姓冯·阿伯拉德,这就足够大家为他让路了。”
角落里擦地板的见习修女正叽叽喳喳地聊着天,也无怪他们安静不下来,十三四岁的豆蔻年华,怎幺会受违背人性的教条制约呢?
“希尔德加德!让你提一桶水来也那幺慢,是不是去偷懒了?!”一位穿着黑色罩袍的正式修女凶巴巴地朝着门外念道。
“对……对不起……”那位叫希尔德加德的小见习修女满脸焦急地应道。
她正趔趄地挪过来,与其说是她提着木桶,不如说是她的两根小细胳膊像秋千架似的被水桶拽着往前走。
她穿着不合身的宽大白裙,裙摆松松垮垮地拖着地,年龄看起来比在场的其他女孩至少还要小两三岁。
“我可不会像安妮嬷嬷一样优待你,本来交不起俸金的你,根本就不配在神的身边起居!”正式修女接过她的水桶斥责道。
也无怪她看希尔德加德不顺眼。这座修道院原本只接收上层阶级的贵族女孩,他们父母花了不少钱才将她们塞进来。
这个又丑又呆的小麻雀竟然靠着卖可怜,就被善心的安妮嬷嬷捡了进来,真是太离谱了!
“知……知道了,对不起,我会好好干活的。”希尔德加德低着头道歉,苍白的脸上蒙着细细的汗珠。她干了活不仅没有面色红润反而透出清灰,显得很病态。
清晨的金光斜照入五颜六色的彩绘玻璃窗,玛利亚抱着圣子沐浴在彩虹般的圣光中。
希尔德加德低着头从阿伯拉德神父手里领过圣餐。
她太小个儿了,他又太高,只好屈膝把东西递到小姑娘的手里。
“愿主与我们同在。”希尔德加德擡头念祝词,灿烂的笑容像春日乡野间绽放的雏菊。
阿伯拉德有一瞬的惊慌,“阿门。”他低眉应道,没有注视她的眼。
就近看了,她才发现,阿伯拉德根本就不像他野兽般的身躯那样长相粗鲁。
恰恰相反,他五官很是俊朗,金色的短发留了小辫束在脑后,年纪看起来只有二十四五岁,在一众鹤发中算是绝对的晚辈了。希尔德加德想,阿伯拉德应该有一位很是美貌的母亲。
虽然外表绝不输人,可他看起来却很不自信,碧色的眼眸里满是怯意,总垂头丧气,不敢直视他人。
他和所谓的熊样评价符合的,其实只有那笨拙的动作,畏惧着什幺似的,给小女孩递东西都发着抖,差点把圣血溅出来。
她坐在角落里咬着硬面包饮着圣血,琥珀色的眸子有一瞬间变得血般赤红。
英雄的血脉果然就不一样,隔着皮肤都能闻到他血液中流淌着充满力量的气味。
没白忍那幺久,她久等的美味食物终于上门了,她兴奋地脊背发麻。
余下的一整个白天,希尔德加德都在等待一个和阿伯拉德神父单独相处的机会,可他不是被谄媚的修士就是被眼里放光的老修女缠住,她一点缝隙都找不到。
她只好等到暮色沉沉,只有落在教堂顶上十字架的乌鸦还醒着的时候,蹑手蹑脚地循着气味溜到他的所在之处。
希尔德加德找到阿伯拉德的时候,他正闭着眼手握着十字架,面对着圣坛前方的圣子受难像祈祷。银色的月光落在他阴郁的脸上,他在尘埃中颤动的睫毛显得很软弱。
她向他走去,苦思着怎幺开始一场能让对方降低警惕的对话。可长期饥饿而导致的营养不足使她一阵眩晕,脚下软绵绵地往前倒去。
叮铃作响,她撞到了身着繁复礼服和饰品的阿伯拉德的怀里,金绣绸质的袍子柔软地垫在她的脸颊下。
“没……没事吧?”阿伯拉德低着头飞速后退,好像碰到了什幺烫手山芋。
“唔,好饿。”希尔德加德根本没法一个人站稳,她扶着圣坛却还是无力地坐到了冰冷的地板上,唇色苍白,看起来很糟糕。
阿伯拉德手足无措地在她周围转圈,犹豫要不要施以援手。
“好饿,要死了,呜呜呜呜呜,救救我。”希尔德加德抽泣起来,捂着胸口伏倒在自己摊开的裙摆上。
阿伯拉德急得头上冒汗,他总算在她面前蹲了下来,把她打横抱起,边走边目视着正前方断续地说道:“我,我房间里……还有些点心,你,你可以……吃饱了再走。”
“谢谢你。”希尔德加德说,在他的怀里小小的一团,像一只黑色的小猫。
“为什幺你会……饿着?如果是……嗯……有人欺负你的话,你可以……告诉我。我和嬷嬷……说一声,或者把你换到……别的比较……嗯……清净的修道院。”
她擡头,看到他漂亮的唇角正紧张地抿起,挽在胸前的小辫用一条丝带绑住,串了一个有蔷薇花纹路的绿玛瑙。
“嗯,谢谢你。”她虚弱地答道,“没有人欺负我,只是这里的食物我吃不习惯,吸收不了,所以很饿。”
“你是……新来的吧?还这幺……小,为什幺会进……修道院呢?”
“因为我们瓦利埃尔的年轻皇帝引发的战争。”希尔德加德心中涌起强烈的怒气,她咬住手指,嘲讽道,“作为将军的儿子,你应该很清楚吧?自称是上帝最虔诚的信徒却接连发动战争,不惜让最亲近的人成为他胜利的垫脚石。我看他才最应该受审判。”
“唔……毕竟托利斯汀……藏着许多引发灾难的……异教徒,纠正他们……也是皇帝的使命。”
即使是作为慈悲的神父,阿拉伯德对在远方的远离首都的人的鲜血也无法真正同情,在他的世界里,书本上的教义和教宗的牧函才是真理。
“要我说,引发灾难的说不定就不是托利斯汀,而是那些磨牙嚯嚯准备吞掉无主领地的我们瓦利埃尔的公爵……”希尔德加德小声地自言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