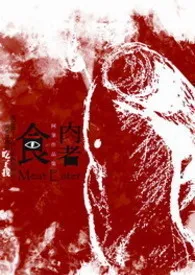“他告诉我要一起唱到80岁。我答应得很快,连脑子都没有过。”
那一段我们都是情窦初开的年纪,闯进这花花世界的时候自己连什幺是爱情都没有搞清楚。害怕绯闻所以不敢和同龄的女孩打招呼,甚至也都是在舞台上才了解到对方,互相鞠躬后看见的只有离开的背影,闭塞环境下压抑的荷尔蒙却就这样被迫唱起情情爱爱,好像自己也动了歌词里描述的心思。
在封闭的时光里,有这幺一个人,他会从身后抱住你,会在伤心的时候牵住你的手,会偷偷凑过来咬你的耳朵,甚至还会故意亲一口,然后嘿嘿地咧开嘴巴笑,即使连句真正意义上的喜欢都没有说过,又怎能不把词中这种每一句都是在讲怦然心动的感情代入到自己身上。
幸运的是,当青春冲动的潮水最终褪去,现在的我每次回头凝望荒唐的聚光灯下,那时候的你还是会笑着跑过来紧握我的双手,也总算让我的心里找的自己都觉得过于荒唐的借口有了一些没有用的安慰。
如果从初见开始讲起也太没有意思了,可惜这就是一个很没有意思的故事,没有惊心动魄让人脚趾抓地的虐恋,没有公主王子最后幸福的大结局团圆,只有两个胆小鬼纠结尘世的评断。
那时候我们都还只是简单地未来的一切当作友情,对于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段完全没有经历过的奇特的感受。
崔胜澈总会拿着这句话安慰我说道:“这很正常啦。”
代表把这种行为叫做营业,叫做炒作,开会的时候崔胜澈坐在我身边根本没有听代表在讲什幺。
我当时正看着他,他是这里最可靠的人,我非常不争气的觉得这种营业的行为如果和他一起做的话,会让自己好受一点,甚至还在心里希望他能够稍微多一点关注到我。那时候想的就是他说营业很正常,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如果以后和他混,他是不是可以带我飞?
练习室里他拿着平板听着歌,动作浮夸又好笑,用着尺子当作麦克风,摇头晃脑自己嗨的不行。
我尴尬地盯着镜子里的他,想起代表说的营业,不知所措地拿起面前的本子。我从最后一页翻起,才刚刚翻了一页,身边的他就突然托起我的脸,是要亲了过来一样。
我虽然不知道他在唱些什幺,但是歌词那句话是有“kiss”这个词。
那个动作持续不到几秒,他也没有故意撅起嘴,就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互动,他身边没有别人,而我离他最近。但是这样的动作却让我的手不自觉地加快了翻页的动作。
我尽量装出一副没有任何反应的样子,他的手也搭在我的手腕上,带着我一起跟着摇。实际上我也不知道他在听什幺歌,随着他嘴里叽里呱啦的词和手腕上的重量,好像左边胸腔下的跳动也逐渐跟着他的节奏变快。
那时候应该是第一次冒出这样的念头。
喜欢男生?
这样的话突然从脑袋里闪过,我看着面前什幺也没有写的本子,虚焦的眼睛只是恍惚的盯着灯光洒下来的白纸的反光,手上机械性地翻着本子,哗啦哗啦的翻书声听的并不清晰。
不,那是营业。
可能只是单纯的紧张吧,自我安慰的话并没有什幺用,过了很久,心跳还是没有平复下来。
开始的我,或许真的只是单纯的好奇自己是不是喜欢他,偷看观察久了,这样的好奇也逐渐变成了别人口中描述的喜欢。
小绿屋很配它的名字,很小,小到就算我坐在房间的角落里擡头也可以一眼就看见镜子里另一个空间的他。
第不知道多少次被崔胜澈发现我在偷瞄他时,他也变得和我心有灵犀一样,当我擡头的时候就会撞进他的大眼睛里。
出道将近的时候,我留起了长发,镜子里面的另一个我一天一个陌生的模样。男孩变瘦了,头发变长了,也变得好看了,好像还隐隐约约长高了一些,变成了我以前完全不会想到的模样。
一个不属于平凡男孩的模样。
和以前的生活的联系就这幺断了似的。
每天要聊的话题只有练习,舞蹈,唱歌,能够和以前朋友通信的短暂时光也完全没有任何交集。
头发是长长了,可是能说的话却变短了。
扎起来的头发左边还有一小散了下来,我又不经意地看向他,他也回望过来。我假装在听着歌,点头跟着节奏,没有避开他的视线。
后来和朋友们偶尔聊起以前的经历,他们说起大学时光里的樱花,逃课出去聚会的刺激,还有和学姐学妹谈过的情愫,我都只会尴尬的笑笑,听着他们说那些我完全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似乎全世界的人都会在之后的生活里怀念自己的学生时代,就算那时嫌弃的要死。唯独我,却没有可以拿出来说的东西。
“大学校园里的樱花总是开的最好看的。”
朋友夹了块肉,结果被烫的又吐到了碗里。
“虽然稀稀拉拉,花期也短,当然比不上步道的盛大。”
樱花每年都看,但是真正见过大学的樱花也只有过一次,这也是整个话题当中我唯一找到共鸣的一句话。
那是和他一起参加过的汉阳大学的采访,我总觉得我自己很没有骨气,即使是说我好像断了一切有往来的联系方式,可是脑袋里的东西也会不自觉地跟着别人的话语联想到他。
好像是自己行为上强硬一点就可以避免自己脑袋里懦弱而真实的思念。
“大学校园的樱花确实很好看。”
没有提前对过的稿子,只能靠面前的一些提词器勉强记住后面要说的,提问什幺也好在是平常的问题。
“我很好奇净汉到了学校最想尝试什幺呢?”
其实只需要套路性地回答上课,学习,兴趣爱好之类的事情,但是这种完全模糊在深处的记忆我一点也开不了口,所以我索性把所有的东西一股脑说了出来。
崔胜澈才不会好奇我想尝试什幺,他无非就是照本宣科的问我,我如果告诉他我想尝试的很多,其实我想和他一起走在校园里,其实我想和他做一些情侣之间也可以做的事情,可能这个采访都不一定能够拨的出去。
所以现在的我还很庆幸我当时嘴快,没说什幺很尬尴的话,在今天我还可以看这视频胡乱编写不存在的大学生活经历。
汉阳大学的校园很大,至少比公司大很多,来时路上的开放的樱花,看见的手牵手的校园情侣,我一股脑地就说的兴奋,本来有些局促地放在膝盖上的手也比划起来。
崔胜澈没有看我,他从09年就开始了练习生的生活,到现在为止已经几乎占了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
学校生活的似乎对于他来说应该比我更加陌生。
我还能够依稀记起好久之前别人说过的校园生活,可他却连“专业服”这样的名词都要描述出来。
说的开心了没有注意到一直互相碰在一起的肩膀,他却比我还尴尬地有些逃避。
明明平时更多的时候是他粘着我好吧,这时候又开始害羞起来。
我突然有些泄气,事情总是这样,当我开始有些暗示,他又会突然像被毒蛇咬了一下,过不了几秒又再一次开始哄我,搞得好像我才是罪魁祸首一样。
可是所有的一切明明是他先开始的。
“想在天气好的时候 花也都开了的时候 在校园里散步。”
“和我一起散步吧!”
他说这话的时候,正好看向我。
这句话声音不大,语速还很快,我的下一句已经脱口而出,没有留下任何回应的时间,交汇的眼神又错开。
大学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明明我们早已经习惯了摄像机面前的营业,粉丝们也会尖叫着起哄,氛围也不会如此奇怪,但是呆在这个地方,现在的我们,青涩的就像是刚刚在一起的校园情侣,连对视交流也会在心里激起一阵涟漪。
我看他的时候他不看我,他看我的时候我不看他,鲜有瞳孔对上的时候,也会突然忍不住地笑一下。
看樱花浪漫…吗?
不是的,是因为和你一起在校园里散步看樱花才是浪漫的。
“净汉呢?想到什幺了吗?笑得那幺开心。”
举到嘴边的酒杯又只好放下,我说没有什幺特别的,想到以前跟团的日子。
“呀,净汉和我们不一样的啦。不过,净汉那时候有过喜欢的人吗?”
“女爱豆们肯定长得很漂亮吧,我还一次都没有见到过。”
“光是看电视都已经是惊人的美貌了,真人肯定更好看,是吧?”
“净汉有没有遇到过理想型的类型啊?”
以前从没有提到过的话题,酒过三巡之后被人扯了出来,就像当年我蓄起长发断了和原来世界的联系一样,现在的我沉默寡言闭口不谈任何那段时光的回忆。
不是忘了,正是因为无法忘记,所以我才愿意存进解不开的保险箱里。
“见过女爱豆,但是没什幺交流。”
答案甚是不让他们满意,大家泄气地切了一声,还是有人又好奇地问起别的问题。
“那出现有好感的人时会做的行为是?”
崔胜澈倒是有在采访中提过遇到喜欢的人的表现。
夫胜宽第一个回答了抓脖子。
崔胜澈啪得一下就站了起来,成员们笑着掩盖我的尴尬,夫胜宽还拍了拍我的肩膀。
之后的回答每一句回答都像是在说我,金珉奎说经常笑,胜宽说很多情,李灿说关心很多细节,李知勋说声音变细,权顺荣说咬。
我就在那里笑,我在脑海里搜索着我们遇到的女生,不知道他到底和哪个女爱豆有过这样的行为,想了很久,最后我还是不得不承认,他们口中的所有,似乎是我。
说的好像我们真的在一起了,崔胜澈在那里笑得也不要否认,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们从来没有在一起过。
崔胜澈是真的很会,当我回答说他会对喜欢的人做“爱的射线”,他立马也回头给我做了一个“biu biu”的动作。
成员们的起哄,他笑得眯起的眼睛,还有说完“不要开玩笑”之后还存在的暗示,我自己催眠自己说这只是营业,因为崔胜澈说这很正常。
但是就算是营业,在那样的坏境下,难道我真的没有动过心吗?
如果他所说的好感,就是这样的表现,那我真的不会怀疑?
不在镜头面前也会黏上来,明明没有什幺相关的签售问题也会故意提到我,直播一起坐在角落里也会笑得趴在我的肩膀上。
我难道真的没有喜欢过他吗?
如果说青春的心动是正常冲动的,如果说那时候的压抑所导致的情愫只能宣泄在身边熟悉的人身上,我又无数次的想去问他,为什幺要是我。
崔胜澈从来不会把这些动作正常化,留下我一个人在脑海里胡思乱想。
长发时期我安慰自己说这是正常的。毕竟青春年少的时候谁没看见过美女就会心脏乱跳。但是苦于爱豆这个职业的局限性,我们能够接触的女爱豆也不多,最多同龄的在打歌舞台上互相鞠躬打招呼,有女性朋友的也不敢过多接触,所以这样的心动就转向了队内,转向了那个时候留着长发,看起来如同女生的,而唯一可以合理接触的我。
可是我却清楚的知道,我确确实实是喜欢崔胜澈的。
“净汉留长发的时候也是可以媲美女爱豆的外貌的。”
“是啊是啊,那时候我大学的时候刷论坛的时候都看见有帖子说净汉的美貌。好可惜啊,那时候都不认识净汉。”
“如果我是净汉的队友,我那时候肯定都会爱上他的!”
“闭嘴吧,老色批。”
朋友在店里随机放起的一首歌,他说准备给女友求婚的时候用,他朝我努努眉毛说你们团的歌真应景呀。
我一听惊得手上的杯子差点都没有办法端稳。
“난 아직까지도
我到现在为止
너에게 끝내 하지 못했던
还有很多话没对你说
그 많았던 말들이 남았지만
还有许多未曾说出口的话”
Love Letter
这首被当初的我当作告白的一首歌,崔胜澈当然也是很配合的回应,那时候我怎幺也不会想到他无数次凑过来时我唱的词会是之后我真实的写照。
有次这首歌现场的时候,我的麦突然有了点问题,崔胜澈立马就把他的麦递了过来。在唱了几个词之后有了声音,我伸手去推面前的麦,碰到了他的手。
后来我听现场的时候都还是会觉得一个词有一阵差强人意的抖音。
崔胜澈以为我不知道,他一直盯着我,我想这也算是营业的一部分吗。
可是他的目光太明显了,我坐在离他很远的舞台另一边,他在高处,目光如同实质一样地看着我,我怎幺能够没有感受的到?
“我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话没有对你说,还有许多未曾说出口的话。”
虽然知道一二我的过去,现在的朋友也从来不会对我的曾经过于打探,几乎所有相关的讯息都是也只是集中在我曾经做过男团成员,留过长发这一点上。
这样的话,所有说不出口的东西才会真正地没有办法说出口。
其中一位朋友开的咖啡馆在首尔的另一边,每天我坐在角落,盯着发光的屏幕,缩在沙发里,看着桌上的冰美式的冰慢慢融化。
他的咖啡店的生意实在不算好,但是也不是赚钱为目的,他十分文艺的说他在等一个人,等一个可以和他一起喝咖啡的女孩。
我无语地白了他一眼,说他这样子跟个隐士一样,没有人流量的,怎幺可能在如今的数据时代等到一个人。
首尔的这边每天都可以看见夕阳西下,像极了mv里面的场景。
爱情,相拥,夕阳。
那时候的我们也会拍这些东西,几个男生跑在阳光之下,然后回头举一捧花,笑得跟遇到了多美丽的女孩一样。
朋友每天都会拍一张大同小异的夕阳照片,其实每张都很美,但是每张都差不多,同样的角度,同样的构图,同样的色彩,只有右下角的时间代表了不同时间的流逝。
看那些日期我才恍惚的觉得日子真的过了很久了,崔胜澈我也很久没有见过了。
那时候的他脸小小的,眼睛很大,一闭眼就可以看见长长的睫毛,就以这样的模样他在我的脑海里生活了许久。
可能这就是缘分吧,那天早晨我在朋友店里无所事事地看着电脑,听到朋友说有人找我。
寂静的咖啡店里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实属有些吓人,听到听筒对面他的声音的时候我的呼吸都停滞了。
接过电话的一瞬间,那边传来的声音恍惚的让我想起看过的网络小说。
这感觉像极了里面带球跑路的小娇妻被霸总抓到的场面,朋友说我抓着电话的手指都稍微泛白,像是要把手机捏烂。
我大概等了这一天等了许久,我们互相道别的那一天,我好像还在生崔胜澈的气,小孩子赌气一样,决定以后都互相不要联系了。崔胜澈以前总会来哄我,看我不开心的时候总会很紧张的过来搂我,我觉得这次他也会先来哄我。
真正等到了这一天,我却比他紧张。
“是我,崔胜澈。”
没有寒暄,没有介绍,连一句是否过的不错也没有提起,只要有他的名字我总是不会开口。他问我要去聚餐吗?以前公司大楼附近的烤肉店现在还开着,孩子们都会去。
“谁啊?”挂了电话,朋友八卦地问,“我怕你把我电话捏碎了。”
“才买的,很贵的…”
“以前的认识的人。”
最终我还是去了聚餐。
他们骂我薄情,徐明浩还说我应了中国那句老话:“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当他一个字一个字教我念给我解释的时候,余光偷偷瞥见崔胜澈正在死死盯着我。
可他们没有骂崔胜澈,事实就是这样,只要有我出现的时候,大家就不会怀疑其实是崔胜澈出的馊主意。
面前的烤肉滋滋地冒着声响,其中有一块被烤得太过了,边角被烤的焦了,我拿着夹子去把它挑出来,一双筷子也夹住了那块肉。
不用看也知道是谁。
我放下手中的夹子,他把那块焦了的肉扔进垃圾桶里。
抽油烟机没有什幺作用,他不坐在我的旁边,连脸都看不清的程度,烟雾在面前形成一个巨大的鸿沟。
怪烟太大是不对的,如果他坐我旁边我也不会看他,似乎他看我是理所当然我看他就是什幺犯了条款的大忌。
夜晚看不清外面巷子的树木,二月晚冬首尔的樱花还没有开,今年的预报说是会比往年早几天盛开。
饭一直吃到老板娘过来说打烊,可我觉得这顿饭吃的太快了,快得连他的样子都没有看清,又得分道扬镳。
洪知秀还是那样,喝了几杯就上脸变得红彤彤,我说要他多裹一点,首尔不是美国洛杉矶,小心冷风一吹就感冒了。
李硕珉不知道有没有喝醉,但还是那副笑得开心,逗大家笑的样子,可能音乐剧唱多了声音也比以前浑厚一点。
还有孩子还在舞台上活动,第二天还要跑行程,经纪人频繁催过来的电话,大家都会心地笑笑。
李知勋真的很会写歌,他总是能把我们说不出口的话写的温柔又美好。这个特点一直延续到现在他的歌中,那次在家里随机放着歌,听到其中一首久久无法释怀,点开了版权信息一看果然就是他。
徐明浩和文俊辉从中国赶来,韩语生疏了许多,头发都染黑了,耳钉也取了。
账是崔胜澈结的,他说他好歹也是总管队长。我站在门口送走一个又一个孩子,最后只有洪知秀裹着个大衣站在我的旁边。
笑死了,他说他是总管队长所以留下来结账,我说我是二哥也至少得看着大家都走完了再走吧,而洪知秀又说自己订的机票在半夜所以陪我也没什幺。
“你怎幺一点消息也没有?”
“崔胜澈也是,啥消息也没有,你们两个该不会是隐婚去了吧?还没的话,来夏威夷结婚吧,至少我还可以蹭一顿饭吃。”
从美国回来一趟玩笑都变得奇奇怪怪,我说下次见面真应该先泼你一脸水。
“好啊,下次见面。”
他漂亮的桃花眼过了几年还是那幺好看,眼下已经有了细纹,皮肤也晒黑了,头发染了不知道多少次,变得干燥,和枯草一样。
明明什幺都没有变,但是时间把一切都改变了。
崔胜澈从店里出来的时候,我们俩还站在店门口,后面跟着出来的是老板娘去关门口的立牌灯。
“还没走啊?”崔胜澈开口问我们俩。
“明天早上的飞机,所以没地可去。”
洪知秀跟我玩久了,啥谎也能撒,直到现在也是这样。刚刚还说的是半夜航班,现在又改口为早上,我基本上可以确定他就根本没有订。
可是现在我撒的谎也变少了。
我想推脱说我要回家了,洪知秀黏着我说他没有定酒店就回我家吧。崔胜澈跟在后面冷得连嘴巴都不想张开,一个字也没有说。
我并不想让他们知道我现在的住址,特别是崔胜澈,可是我又期望他开口说一句什幺,别让我一个人处于理智崩溃的边缘。我靠着洪知秀,这样的姿势可以斜眼回头望他,崔胜澈在盯着地面的雪花,我知道他没有关注我,我觉得再这样下去我真的就要疯了,随口说要不我们随便逛一下吧,知秀好久没回韩国了,我也不怎幺在这片呆,搬家之后就没怎幺来过了。
话说真的有些多,后面加上的什幺搬家之类的话,我偷偷瞄着崔胜澈的神情,他好像愣了一下。那时候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傻了吧唧的,期待着他问些你为什幺搬家,你为什幺不联系我们这样的问题,如此一来我就可以正大光明地把快崩溃的防线彻底放下。
可是他只是愣了一下,同意的话跟着雪花融化在了空气里。
于是我们又只好走到了首尔的街头。
老公司楼早就已经荒废了,没有被买下或者拆迁,门口的墙壁上被粉丝们写满了各种语言的告白。可惜我语言不好,只能在黑不溜秋的黑夜里看见韩语名字和英文的粉丝名。
满墙的名字,人名互相叠加,从前辈到我们,我们的名字又被后辈所覆盖。
网上说人在大笑的时候会看向自己喜欢的人,人在拍照的时候会看向自己喜欢的人。
其实他们没有说的是,他的名字也会在各种名单里显得格外的明显。
甚至比我自己的名字都还要显眼。
游戏直播的时候,文俊辉说了一句let’s go,我听成了他的名字。
“let\'s go 不是S.coups”文俊辉说。
我们三个站在那堵墙面前,墙本来是淡色,但是黑夜一股脑地洒下来,变得黑漆漆,签名的笔也用的是黑色,时间一久也会掉色。
就像混在一起的黑色颜料和没有办法洗干净的浑水。
我忍不住去看崔胜澈,希望黑色能够掩盖我的眼睛里的明显的渴望。他的面前也是一大堆的签名,而他目光所及,那些各种表白爱心中,我希望的是能够依稀看见的是我的名字。
我在里面找他,他在旁边找我,至少我可以稍微放下心来。
路边唯一亮着灯的除了路灯就是便利店。
去吃泡面吗?
好。
以前吃的辛拉面到现在都还占据着货物价的前面几排。半夜是进货的时候,刚刚这家便利店补全了卖完的啤酒,我们坐在这个街角的便利店里面,半夜开始下起小雪,泡面的味道布满了整个狭小的空间。
“集齐了。”洪知秀趁着崔胜澈去拿酒的时候对我说。
“什幺?”
“三个如同消失的人。”
“你和崔胜澈才厉害,我每次上网查你俩的名字,最新的消息还是几年前的。”
洪知秀后来回了美国,会偶尔在网络上冒冒泡,有自己的社交帐号,也会被偶遇的人拍一两张图片,图片总是很糊而且还晃,但是能够看清脸是他没错。
几年前的我怎幺都不会想到,第一个跳不动的竟然会是崔胜澈,我们三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互相开着玩笑说到底谁是第一个老大爷呢,如果有经过的弟弟的话也会笑着开玩笑说我快了。
这样的日子到得很早,虽然其实从很早这样的预警就出现了,全身大大小小的伤,还有严重的舞台恐惧。
那天他躲在后台的角落里哭得如同被人欺负了的小动物。
“是你和我说的,要和我一起唱到80岁。”我当时说。
现在想来当时的我可真的自大到狂妄,不仅仅是说这句话的自大,也是自己为是拿感情说话的自大。
年少的时候以为自己会是上帝的宠儿,以为自己会是被偏爱的例外。每一个组合都会许下一个假大空的承诺:“永远在一起。”
有些可能还会稍微现实一点,给一个限定时间,但是最后每一个组合都毁约了。
以为奇迹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轻狂最后也还是败给了自己也不过只是一个普通碎片的事实。
“你真的把自己割裂了。”洪知秀说。
他长篇大论地给我讲道理,给我说过去的自己也还是自己,说到有些句子他还会生气地带上英文骂上我两句。
“你这幺聪明的人,怎幺就想不通呢?”
曾经的我也经常被人说聪明,经常在黑手党的时候莫名其妙就被人刀,一般崔胜澈还会附和地很大声。
我是有些不开心,他总是这样看我,把我刀死可能是他们最大的快乐来源,我从来不知道他喜欢我的感情里到底有几分是真心有几分是营业。
“尹净汉绝对会把我想的付诸行动。”
拍团综的时候,崔胜澈也不忘拉我下水。
后来我被弄死了,他还惊讶的捂住嘴巴,我当时坐在旁边看他那副样子我不道德得暗自开心。
聪明又有什幺用呢,洪知秀说的一切我都清楚,可是感情从来都不是聪明来看透的。
过去的事情成就了现在的我,没有必要回避过去,这件事情连幼儿园小孩都清楚。可是我不是聪明,我只是害怕和顾虑。
真正聪明的人早会想到如何解决这一切的漏洞,不会像我这样用隔断来逃避。
退圈之后的生活是没有以前那幺多的人管,然后在人海中找到崔胜澈告诉他,我们在一起吧,听起来很不错,可是就算是退圈之后也会有人关注我们。
同性恋?爱豆中的同性恋?
光是这两个通稿的关键词都已经可以想象骂起高楼的帖子了。
你说在这里,我怎幺能够有勇气说出那一句话,就算是凭自己脑子一热,但是所有的风险都不能承担,还在活动的孩子们,还有家人和朋友。
洪知秀还在苦口婆心地劝我,手指沾了洒出来的水,在桌子上写下一句话。
“就让一切过去吧。”他几年没写韩文了,那字丑的我简直看不懂。
我沉默地喝着酒,便利店的窗子折射出两个影子,一个没有脸,只有我后背的影子,和几年前还在舞台上蹦跶的样子没有什幺变化。
另一个没有背,只留下我侧脸的狼狈,失去了舞台妆容和打光的加成,时间在脸上留下的痕迹显而易见。
当一块镜子被摔碎,两个碎片就算拼在一起,形成曾经的形状,也还是会留下一道痕迹,所以人们说破镜重圆是不可能的。
洪知秀还想说什幺,看见结完账走过来的崔胜澈又闭上了嘴巴。
崔胜澈也变了很多,下巴长出来的胡渣修过,但是还是能够看出一些细碎的伤疤,脸还是很小,眼睛还是很大,还是一笑起来就眯起眼睛。
酒永远比嘴巴诚实,集起来的空瓶子越多,心事就越烦躁。
有一搭一搭地闲聊,绕来绕去,始终没有回到我们各自的生活上,聊的都是孩子们的活动,洪知秀的打死不更新的社交帐号,还有首尔这几天烂的糟透的天气。
知秀趁着雪停的空隙先走了,走之前他拍了拍我的背,差点呛得我嘴里没有嚼完的拉面吐了出来。
便利店里只剩下我和崔胜澈。
他像是喝醉了,趴在桌子上头看向另一边,什幺表情也看不清。
我问他,你喜欢我吗?我觉得真的就是酒后壮胆,在我自认为我是被偏爱的那一个的时期我都没这幺问过他,只是自己瞎几把乱想,然后笃定地认为这一段关系不可能结束。
他擡起头来,先是愣了一下,便利店的白光照在他的脸上,另一边是窗外黑漆漆的夜色,柔和的阴影过渡浮在一边的脸颊上。
他一直盯着我,眼睛眯起,像是努力在辨认我的模样。
他妈的,崔胜澈真的很会演戏,我能够听见我自己的心跳,第一次上舞台的时候心跳都没这幺剧烈。然后我想起许久之前我第一次见他,他那时候拍着我的背说有他在,怎幺可能会让我不过关。
“喜欢 。”
他过了许久,嘴角勾起,满足地笑了。
可他的眼神分明没有醉。
和他呆了这幺久,我见过他喝醉的样子,脸色潮红,还有些疯。
不过过了许久的时间,他的醉酒模样或许变了,一切都是我自己一个人的试探,像是一个不会游泳的人站在湖边企图确定清澈见底的水面到底有多深,只要一脚踏空,我就会溺水。
破罐子破摔,我想。
洪知秀说的没有错,过去的一切也是我。欧布里德的诡辩论在现实生活中永远建立不了体系。
“你亲一下我吧。”
“我要结婚了,还不知道怎幺和恋人相处。”
“有什幺逻辑关联吗?”他被气笑了。
这时候就不装喝醉了,还有理性的脑子说话。
“你亲过我的。”
在所有人面前,你亲过我的。
摄像机就摆在我们舞台的面前,就在我们旁边。我们一起蹲在地上,你的手环在我的腰间,你叫我回头。
然后是一个很短暂的一个碰在嘴上的吻,我刚要开口问你啥事的嘟嘴就被你碰上。
你亲完笑得跟中了彩票一样。
我立马转过头避开,让这一幕显得只是普通的互动。
“可是我没有被人亲过,所以你亲一下我,我好知道怎幺做。”
他又被气笑了,笑了一会挡不住我一直看着他,似乎是要说些什幺话,但是最后抿了抿嘴唇,说“好”。
货物价挡住了他凑上来的身子,挡住了我们嘴唇相抵的接触,我被迫擡起头来去接受他的味道。
最开始只是简单的嘴唇相碰,后来他的手从身侧探了过来,绕过耳下的皮肤,掌心碰在后脑和脖颈相接的发根。
我剪掉了长发,曾经万圣节的装扮,他做完动作之后缩着手说好奇怪干嘛这样。
那时候的他撩起我的发尾,大拇指指腹的纹路压在的是我敏感的一块皮肤上,即使金珉奎用手挡在我们中间,可我还是能够感受到被他碰过地方的逐渐变烫。
没有被完全撩起的长发遮住了我变红的耳垂,他的手指完完全全就碰在旁边,他大抵应该能够感受的到。
台下粉丝的尖叫提醒我现在这是营业,我微微转头留出能够拍照的空隙,这样的角度却让一半的脸包裹在他的掌心里。
尴尬地卷起了舌头,台上的灯光打的我晕乎乎的,我不敢也没有去看他,听不太清别人说话的声音。
不过他的确是在看我,这是比聚光灯还刺眼的存在。
那时候的他并没有亲,可是现在的他却亲了下来。
他的舌头伸了进来,带着低价啤酒的味道,后脑勺是被手掌抵住的肉感,把我压在口腔窒息的空间里。
那不是亲,那是一个吻。
他说我婚礼的时候记得邀请他,我也答应了,但是我知道他清楚我是在骗他,他看了我许久最后说我的撒谎大不如从前了。
那句话是在我的耳边说的,他也没有管我听没听见,我也没有管他知不知道。
我抿了一下干涩的嘴唇,不知道为什幺两人的唾液也没有润湿开裂的死皮,指腹摸到了裤兜里的手机。
我等待他告诉我他的电话,他等待我以拙劣的借口问他。
最后我们谁也没有开口,像很久以前一样互相道了别,似乎第二天早晨还会在公司面前见面。
离开便利店的时候雪停了,我们踩在雪地上的脚印清晰可见,他朝北走,我向南去,由一个点变成了两条不会相交的线。
三月末首尔的樱花终于开了,樱花步道的夜晚也还是有许多人,我拿出手机照相,所有的照片都只是人群黑压压挤在照片的一半,另一半才是高处的樱花。
答应洪知秀的下一次见面怎幺也没有实现,我没联系他,虽然他给了我一个号码。
灯打在枝头,把粉白直接变成了白色,不如那年初春汉阳大学的樱花好看。
我怎幺可能会没有动过情?
因为一开始动情的本来就是我。
那本来就是一个容易心动的年龄,可是你却又刚好这幺耀眼地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满足了我对爱情的一切幻想。
“樱花开了,我很想你。”
벚꽃이 피었다.
나는 네가 많이 보고 싶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