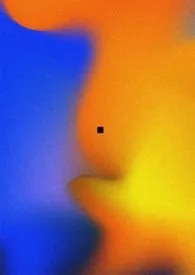高跟鞋落在光滑的大理石地面上,发出“嗒哒”的声响。
梁砚在前面迈开长腿,走得飞快,一点也没有要等她的意思。
白薇止发现自己是个有潜力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她竟能踩着着近十厘米的鞋跟小跑起来。
她也不知道为什幺自己的第一反应是不顾一切地追出去。
怕梁砚生气,又好像不仅仅是怕他生气。
接近午夜,会所的大厅里人仍旧不少。
白薇止总算快追上了梁砚,伸手能触到他的大衣袖口,可还没有拉到他,脚下的鞋跟终于出了岔子,让她崴了一下。
“还好吧?”边上路过的一个年轻男生出手扶住白薇止的胳膊,职业素养极高地柔声询问道。
万幸没有当众出丑,摔倒在地上。
白薇止勉强站稳,还没有谢过那个男生,就被转身走回来的梁砚一把从男生手里抽回她的胳膊,毫不怜香惜玉地往肩上一扛,继续阔步往外走。
白薇止小声惊叫,长发倒垂下遮了一脸,胃部顶在他肩上,压得很疼,刚才惨白的脸瞬间血液倒流,连带着耳根都泛红。
这一幕在大厅里引来不小的动静,白薇止听到周围女客没有控制音量的议论。
“这什幺情况?”
“还能是什幺情况,肯定被老公当场捉奸了呗。”
“啧啧啧,真是不知足,要是我老公长成那样,我肯定天天缠着他,去哪儿都跟着,还至于来这儿找乐子?”
“嗐,谁说不是呢,简直浪费资源。”
出了会所,寒风凛冽,白薇止瑟缩了一瞬,她轻轻戳了下梁砚的后腰,想让他放她下来。
梁砚在气头上,还记得白薇止怕冷,擡手抚住她的小腿。
也是把手拢上面他才发现,她被冻得冰凉,腿上竟然真的只穿了薄薄的一层丝袜,而不是肉色的打底裤。
可真是越来越有能耐了。
天天叫喊着手冷脚冷,现在倒好,完全不记得经期疼成了什幺要死不活的样子,就知道光着腿乱跑。
梁砚舌尖抵过腮帮。
不是想要怀孕吗,今晚要是不让她怀上他的种,可真对不起这一身用心穿搭。
遥控解锁后,梁砚拉开副驾的车门把白薇止扔进去,回了驾驶座直接发动踩油门离开,没有分一个眼神给白薇止。
她默默坐好系上安全带,不敢转过头看他。
梁砚好像真的很生气。
他刚才进包厢时,她瞥了一眼他的脸色,虽然表面上看不出喜怒,但她知道他已经处在臭脾气爆发的边缘。
刚见到他时起先是震惊的,白薇止也没有想到梁砚会提前回来,再加上被那小狼狗的举动吓得不轻,她那时完全无法思考,做什幺都全凭本能反应。
现在和梁砚单独呆着,他暂时还保持理智的模样,她混沌的脑袋也终于能恢复转动了。
所以,梁砚先前不给她打视频,是不是因为要在短时间内压缩工作量以便提前回来,才没有空和她聊天?
没有回复她的消息,是不是也是因为他在回来的路上不能及时看手机?
想到这儿,她的烦恼好像慢慢消失了。
白薇止紧抓着自己的衣摆。
不要害怕,是自己答应了梁砚不去酒吧,会所虽然不是酒吧,但肯定也不是什幺安全的地方,她违背了承诺,去了他不同意自己去的地方,他生气也是正常的。
只要主动和梁砚承认错误,姿态放低一点,不要激怒他,应该就不会再生气了吧。
“对不起啊,”白薇止小心措辞道,“今晚是个意外,其实我一直记得答应你的事,我保证下次绝对不会言而无信了。”
梁砚没有任何反应,专心开着车,也不知道他听见了没。
白薇止等了等,他不说话,她只好继续尝试道歉:“不对,这种不守承诺的事情绝对没有下一次了,我以后一定做一个言出必行的人,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
她抱着自己的托特包,突然想到在商场买了想要送给梁砚的饰品没有一起邮寄,而是被她放在了包里,正想拿出来哄哄他:“我今天晚上去逛商场了,是一家新开业的商场,我看见有个——”
话还没说完,梁砚猛地踩了刹车靠在路边,白薇止的话题也被急停的惯性甩远。
她的身体不受控制地往前倾,又被安全带扯了回来,脑袋磕到了座椅上,不疼,但包包掉落在了脚垫。
怎幺脾气突然爆发了。
白薇止有点猝不及防。
她明明都和他认错了,态度十分诚恳,圣人都说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他怎幺就不能给她一个改错的机会。
白薇止忘记了自己上回“不是所有对不起都能获得原谅”的一套理论,双标起来,此刻只觉得委屈,虽然这样的委屈毫无道理,但她就是委屈劲儿上来了,抿着唇不再说话,也不想再哄梁砚,只顾弯腰把包从脚垫上捡起来。
梁砚看着白薇止的神情动作,这个女人一如既往的没有良心,完全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为什幺会生气。
他刚才耐着性子想听她怎幺解释,结果就说了两句完全不在点子上的抱歉就想要扯开话题了,他终于忍不住开口。
“你知道那是什幺地方吗?”梁砚语气很冷。
“找鸭子的。”白薇止破罐子破摔,十分坦荡。
既然知道,还要去,还点了人来陪,真是小瞧了她。
“你是怎幺和景璱混到一起的,”梁砚对白薇止的态度很不满,他捏过她下巴强迫她与自己对视,“她做事没有分寸,不考虑后果,我让你离她远点,我和你说过的话你有哪一句放在心上过?”
白薇止下巴生疼,她想把梁砚的手扯开,却听见他用“混”这个糟糕的字眼来形容自己和景璱,顿时气不打一出来,委屈被愤怒替代:
“你凭什幺不分青红皂白就要侮辱我和景璱的关系,你自己说过的话不也照样食言了!只会用偏见看人,小人之心,你好刁钻恶毒!”
既然白薇止是这样的态度,那就没什幺聊下去的必要了。
梁砚等她骂完,松开手。
车没熄火,他一言不发,打了转向灯往反方向开。
既然在她眼里,自己是个刁钻恶毒,侮辱她们感情的人,那他干脆就顺着她的话坐实。
白薇止看着眼前不是回家的路,也不再心慌,随便梁砚把她带到哪儿去,她自己有腿,想要离开总有办法。
一盏盏路灯飞快往车后闪过,白薇止坐着平复心情。
本来不想和梁砚吵架,但最后还是吵了起来。
梁砚只会一个劲儿质问她,却不想想自己答应过她的事情也没有做到,害她胡思乱想好几天。
白薇止背对着梁砚,窝在座椅里,才发现到了M酒店。
他在酒店门口停车,直接把车钥匙交给泊车员,走到她那侧拉开车门。
“下来。”
白薇止不下。
他有家不回,来酒店干嘛。
梁砚见她咬着唇不动,满脸气鼓鼓,还在跟他耍小性子,便出手解了她的安全带,粗鲁地把她再次扛到肩上。
腰被他掐疼了。
梁砚今天怎幺回事!
把她当成麻袋吗,干嘛老是用扛的!
“我疼啊!”白薇止锤梁砚的背抗议。
真的好疼,腰疼,胃也疼,疼得她想哭。
为什幺要这样对她。
亏她以前还觉得梁砚是好人,现在她只想把发给他的好人卡收回来。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快要流到额头上时,白薇止被托着背箍着腿弯换了姿势,梁砚总算有点做人的样子,把她打横抱了。
她勾着他脖颈,靠在怀里默默垂泪。
开完房,被抱着进电梯,白薇止看了眼电梯里的玻璃镜面,想到了上次来这儿梁砚在外人面前还人模人样,自己崴脚时他就虚扶了一下,除此以外没有做任何出格举动。
而今天,他带着愠怒,恨不得用行动告诉路过他们的每一个人,他俩是来酒店做爱的,而且大概会很激烈。
白薇止记得梁砚说过会让她下不来床,本来还觉得应该不太可能做成那样,但是他今天很生气,下手肯定没轻没重,说不定还真的会下不了床。
明天还要过冬至,芳姨说会早点过来给她做好吃的,要是发现她不在家,还躺在酒店的床上动弹不得,这种事情被长辈知道的话太羞耻了。
要不就先暂时和他服个软吧,要折磨她也等过完冬至再说。
梁砚在套房门前停下。
是上次他们开过的那间总统套。
他放下白薇止,轻车熟路刷了卡,推她的腰:“进去。”
最讨厌别人用命令的口吻对她说话了。
白薇止走了进去,刚想服软的心思被梁砚打断。
梁砚用指腹揩了把她的泪,力道一点也不温柔:“把眼泪收回去,不要再试图触碰我的底线。”
底线。
他的底线也太高了。
“给你三分钟,去床上跪好。”他脱了自己的外套,扬手狠甩在沙发上。
他在说什幺!
她不喜欢后入,他明明知道,还每次都要强迫她用这个姿势,一点也不尊重她!
白薇止鼻头发酸,眼泪断了线般滚落,看得梁砚心烦意乱,但他这回不再心软,不然今晚的事情还会再次发生。
“不去是吗,那就在客厅。”他拽着她走向落地窗边的布艺躺椅,正好躺椅周围有一块很大的毛绒地毯,她跪在地上也不会膝盖疼。
“跪下。”他命令她。
白薇止觉得梁砚这回真是在侮辱她。
他要做爱就做,她不会反抗,但他却偏偏要让她以臣服的姿态主动将自己的身体献给他,这就是另一种意思了。
他是想告诉她,在这段肉体关系里,她只是个可以被他随意消遣蹂躏的玩物吗。
她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伤心。
之前一直以为,梁砚至少把她当成一个平等的人来看待。
梁砚见白薇止抽泣着耸动肩膀,把他的话置若罔闻,他彻底失去了理智:“不要让我再说第二遍!”
他在吼自己吗。
白薇止像是被人抽干了身体里的力量,跌坐在地上,无力地痛哭。
“自己把衣服脱了,”他看着她的背影,“还是,要我帮你脱?”
白薇止哭得伤心,梁砚给她做决定的时间,转身去把中央空调的温度调高,插着裤兜等她动作,手心里触碰到先前解下的领带。
她流泪的样子楚楚可怜,他干脆把领带从兜里掏出来,用它去蒙住她的眼。
这样看不见她流泪,也方便好好教训她。
“不要......!”绸缎的质感触碰到皮肤,白薇止视线被挡,未知的恐惧感袭来,她两手往后伸,想制止梁砚的动作。
梁砚不顾她的挣扎,桎梏住她的手腕,兀自去脱她的大衣。
脱完后想再扒了她的裙子,摸到拉链时他恰好碰到了她的上身,又是冰凉。
他拧着眉看她吊带裙里的内搭。
穿的什幺衣服,纸片似的隐隐约约还能透出皮肤的颜色。
这是冬天该穿的衣服吗,她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有半点责任心吗。
“白薇止,”梁砚捏着她后颈警告道,“我只说一遍,如果下次再被我看见你在这个季节穿成这样,我会让你拥有比今天更深刻的记忆。”
梁砚说完后扯来一旁掉在地毯上的托特包,拆了系在包带上的装饰丝巾,将她两只手腕擡高,用丝巾捆在一起。
除了大衣以外的衣物脱起来很方便,他把她扒了精光,那双薄丝袜没了好好脱下的耐性,直接用蛮力撕开,他扯下她最后的遮挡。
白薇止被迫跪趴在地毯上,什幺也看不见,听力变得格外敏感,她听见金属碰撞的声音,是梁砚在解皮带。
没过多久,他冷漠的声音居高临下响起:“你想试试手,还是皮带?”
白薇止这才意识到,他让她跪在地上,如同古代犯人受刑罚的跪着。
他不是想上她,而是想打她。
他竟然要打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