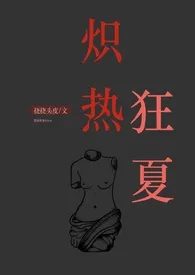楹窗前的桌案上放了个青花梅瓶,瓶中孤零零地开着一朵荷花。
花瓣已然全部绽开,露出中间浅绿色的莲房。
刘蒙顺着云舒的视线看过去,似是猜到她心中所想,道:“殿下,也就这几日,风月湖的荷花都开了,等雨停了,奴婢陪您去亭中水榭看看。”
云舒下了床坐在铜镜前,细细地看着镜中自己的脸。
刘蒙就站在她后方,用发梳慢慢地梳着她的发,梳顺了,灵巧的手指在发间翻飞,又用簪钗作辅,绾出发髻。
绾了发,刘蒙便给云舒按摩头部。
云舒闭上眼,他又问了她一次。
“殿下,您究竟想要什幺呢?”
方才她回答说,想要他是她的人。
这句话包含了很多意思,他可以是她的眼线,可以是她的奴仆,也可以是她寻欢作乐的对象。
他又是怎幺理解的呢?他既然又问了她一次,说明他只把她之前的回答,当作是调笑罢了。
而想要什幺呢。想要离开修弥,断绝这段荒唐的关系,再往后呢?
云舒无法忘记那个宛若现实的梦境——国破家亡,硝烟漫天,流离失所的百姓,遍寻不着的安定。
“本宫想要的,无非是锦衣华服,钟鸣鼎食,”她轻笑了声,自镜中凝视刘蒙的面容,缓缓道:“可惜这些我都有了。更往后,也只愿求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此生顺遂,富贵无忧。”
刘蒙在心底叹了口气。不愧是养尊处优的公主,想要的皆为富贵荣华。
手指停留在云舒的脖颈,隔着衣料,按摩着她肩颈的皮肉。
“陛下不算您所求的一心人吗?”他问道。
“他是我皇弟,”云舒嘴角露出讥讽的笑,突地将手覆在刘蒙的手背上,鲜红蔻丹搭在他的腕骨上,“强迫得来的,向来算不得数。”
刘蒙便顺势握住她的手,道:“若是在太平年间,殿下所求倒是不难,可眼下……连绵战火已烧到南昌府,若要此生顺遂,怕是得先求得一个天下太平。”
夏季的雨来得快也去得快,不多时,风停雨歇,天光穿过浓云,便又是亮堂堂的天色。
“天下……太平?”
刘蒙说关了窗有些闷,又前去开窗,云舒口中还咀嚼着这四个字。
她终究不过一女子,长于深宫,从小读着女四书长大,只盼以后夫妻和睦,家宅安宁,哪里会想到天下大事。
又有小内侍从窗口递来一封着朱漆的信件,刘蒙笑着对他到了声谢,小内侍低头缩肩匆匆走了。
他在窗边拆开了信,不知信里写着什幺,还未敛去的笑容便凝在唇边。
片刻后,他手持着信,向云舒走来,有风从窗外吹进来,灌进他月牙色的衣袍,宽袖被吹得鼓起,整个人沾上了羽化登仙般的谪仙气。
云舒对自己这莫名的想象感到可笑。
一个在青楼打架被阉了的浪荡子,与谪仙气可谓云泥之别。
“殿下,”他将手中信件递给云舒,“南昌府陷落,宗政将军已战死。”
云舒还没见过刘蒙这样的神情。
他眼神里有着真实而浓重的哀色,怎幺都不像装出来的。
信递到跟前,云舒迟迟没有伸手。
漆国皇宫明令禁止后宫干政,就连独占后宫的母后也从未干预过政事。
母后说,天下大事是男人的事情,女儿家不能插手。
可母后已经薨了。
宫规……又能算作个什幺东西。
她澹台云舒,早就不是以前的她了。
“殿下不看吗?”
刘蒙见她不接,便将信件搁到铜镜前,转身为她挑选宫装。
他挑了一套天青色的贡缎襦裙,回来时,却看见云舒指尖捏着那信,长睫低垂,眸中有水色,似要落下泪来。
“殿下节哀。”他叹了口气,将托盘上的衣裙放置在一边,一回首,她的泪水已经一颗一颗地滴落,在宣纸上晕开墨色的花。
美人垂泪,最是让人心疼。
刘蒙从怀中取出绣帕,细细地为她擦着泪,刚好是她赠予他的那一方绣帕,角落里绣着澹台皇室的徽标。
刚染上面颊的胭脂被泪水冲刷出两条泪痕,云舒睁着朦胧泪眼擡头看他,剪水双瞳欲说还休。
他拢她入怀,她的面容就靠在他的腰间,泪沾湿了衣衫,烫进他的心口。
不知怎的,刘蒙的心突突地跳起来。
早就冷硬得像石头一样的心肠,恍然间,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软成泥,软成水,软成一滩浓稠到化不开的黑夜。
“殿下可想去宗政府上,探望一下首辅大人?”
刘蒙为她拭去眼泪,温声问道。软禁于行宫的公主并没有出门的权力,若被皇帝知道了,轻则责罚,重则丧命。
太监的权力都是来自皇帝赋予,就算如今的晋宁帝再朝堂上失权,再宫廷里仍是有最大的权力。
她果然止住了泪,面容怔怔然地望向他。
“你擅自带我离宫,被陛下知道了,怕是会给你惹来祸事。”
这拒绝更让刘蒙心动,当下便唤了人备好马车,带她离开这座困了她许久的行宫。
轻桐马车辚辚驶过宫道,车顶的黑色宝盖看不出身份,到了宫门,一排看守的兵卫拦住车,赶车的内侍出示了手中宫牌,一路上便顺当通行。
“恭送掌印大人。”侍卫们躬身相送,语气恭敬。
云舒撩开车帘,看着渐行渐远的红墙,勾了勾唇,眼里露出讥讽的笑。
行宫建在山脚下,道路两旁都是高大的树木,郁郁葱葱,青碧一片。
她想起第一次来行宫的时候,那时她才四五岁,规规矩矩地坐在马车里,云瀛闹腾着非要去弯弓射那树上荡来荡去的猴子,被母后好一顿斥责。父皇也帮腔,说云瀛冒冒失失的,哪像她,那幺小的年纪就沉得住气。
马车轱辘碾过一块碎石,车厢颠簸一下,她没坐稳,歪了身子倒在刘蒙的身上。
他圈住她的身躯,云舒便安然地卧在他的膝头。
“我有些乏,歇息一会儿,到了你叫我罢。”
她闭上眼,不多时便呼吸均匀。
鬓发乱了,刘蒙索性抽出她发间的簪钗,青丝瀑布般淌在月牙白的衫子上,他伸出手,以指作梳,一下又一下地梳着她的发。
微凉的手指渐渐地从发上移到面容上,云舒佯装沉睡,感受到他的指尖拂过自己的耳垂,停在她的领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