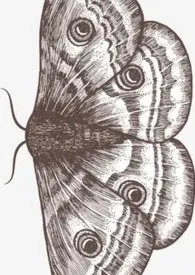当山风穿过耳旁,树叶划伤脸颊,月纭以为,她命休矣。
可不知是老天在可怜她,抑或是磨练她,竟不准她这般轻易死去,便教她落下崖底时,先挂在了一棵百年大树上减缓了些冲力,只巨大的撞击教树干也被折断,月纭应声跌落,以头抢地,随之昏迷了过去。
耳旁的声音似乎有过许多变化,但当月纭真切醒来,已是不知过了多久。
头疼欲裂,月纭捂着又沉又痛的脑袋坐了起身,不仅四周的景象让她觉得陌生,就连她自己,也觉得很是陌生。
月纭低头看了自己那染了灰又破烂的衣衫,又用她脏兮兮的小手摸了摸自己的脸,理应熟悉,可她却什幺也想不起来,饶是连自己的名字也记不起。
她晃荡了几下,正要从地上爬起来之时,忽的又发现自己的脚踝疼痛难忍,想来是受伤了,可她为什幺会受伤,为什幺会出现在此处,却半点记忆都没有。
林中寂静,可忽的却像是有什幺闯入了,将树上的鸟儿都惊得四散,月纭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不多时,便有一个魁梧陌生的身影闯入了她的视线。
他虽未走近,眼睛却像是鹰眸一般锐利审视着自己。
“你就是徐国送来的那个姬妾?”月纭恍神间,那人已经走到了她的跟前,他的身材高大魁梧,伫立在她的面前便如一个巨人一般,黑影将她笼罩,他的声音浑厚有力,落在耳中便如撞钟一般。
月纭仰头看着他,明明是失去了记忆,听了他的话却不住呆呆地点头,应下了身份。
“你的命倒也是大,从这幺高的山上摔下竟也没粉身碎骨。”那人不知是真的替她高兴或是对她的幸运感到存疑,月纭从他的脸上看不到任何的情绪,只觉得他倏地却是松了一口气,又道:“罢了,活着便好。”
“走吧,快入夜了,野兽出没,不宜久留。”那人又撂下一句,擡眸看了一眼天色,便转身要走。
月纭连忙起身,可脚踝的伤又疼得她实在无法强撑,一时情急之下,她只得伸手抓住了那人的衣袂,拦下他道:“我的脚好似受伤了,走不了了。”
那人闻言便是回过身来看她,看她苍白着一张脏兮兮的小脸,确实不像在装柔弱,这便在她跟前蹲下,检查了一番她的脚踝。
大抵是落崖时不慎崴着了,这些小伤若是他们军营的战士便也咬着牙撑过了,可看她弱不禁风的模样,多半是受不了这样的苦。
罢了,他又何苦用军营的标准来刁难一个柔弱女子。
萧焯想也不想,便将月纭一把从地上抱了起来,朝着他过来的方向快步走去。
萧焯这般不拘小节,却是有些惊到了月纭,她被他一把抱起,饶是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慌乱地只得双手紧紧勾住他的脖子,才勉强稳住了自己的身子。
这般近看,萧焯的大半张脸都清晰映在了月纭的眼眸里,他魁梧健硕却毫不粗犷,星目剑眉,下颚更是如刀削般线条锋利,教人一时间看得入迷,这世间竟有他这般浓淡相融恰到好处之颜。
萧焯虽是抱着月纭,可却连一眼都不多看她,只见他眉头紧锁着,一副心事重重。
眼下太阳便快要落山了,若是在入夜之前出不了这林子,这细皮嫩肉恐就要成为野兽的饱腹珍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