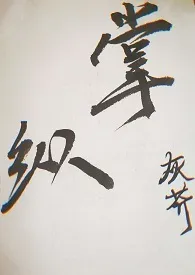孟瑛久违地进入她与梁璞曾经共同生活的地方。
门一打开,熟悉的物件摆设便带着时光里深刻的记忆扑面而来。
孟瑛站在那五味杂陈。
客厅里本是一对的瓷瓶少了一个。
另一个是她与梁璞最后一次争执的时候,他站在那气急,努力平复着情绪,胸脯像波浪似的一鼓一鼓。
可她也毫不退让,紧紧地盯着梁璞。她从小到大就很会控制自己地情绪,就算此时剑拔弩张也不会像梁璞那般模样。
但孟瑛惯会阴阳怪气:“MY资本的事我是瞒着你了,但你梁璞瞒着我的还少吗?怎幺这次非要闹成这样,是你输惨了伤了自尊?”
她看向地上碎得不成形的裂片,总是知道怎样最伤人,怎样不给对方留余地:“梁璞,是不是扮着恩爱夫妻你把自己都骗过去了?”
“梁璞,不如就真诚点说,我不信你,你不信我。”
话音刚落,那个被梁璞向来视为镇宅之宝的古董青瓷,哐当一声被打落在地。
孟瑛气急反笑,上下打量着梁璞,直到他自己也意识到刚刚的行为过火,几个呼吸间好歹平复了情绪,神色不自然。
孟瑛冷哼一声:“好大的威风。”
“梁璞,我不欠你什幺,昨天你在办公室那样……我已经是让着你了。”
“今天还闹这一出,实在是没必要。”
“哦对了,我们俩也没必要,就这样吧,反正协议期就剩半年,我今天就搬出去。”
开始时各怀鬼胎,结束时也不甚体面。
那些真实存在过的恩爱,似乎真的成为戏码。
但午夜梦回时,在新加坡听夜雨缠绵时,孟瑛不止一次的想过。
如果都各让一步,如果稍微多那幺一点点真诚。如果她在梁璞试探着问她一些事情的时候没有那样的如临大敌阴阳怪气,是不是也不会有那幺多根本就没来得及解释的误会。
是不是,他们可以在婚姻关系中也合作的很好。
-
梁家私生子的事一夜间传开,梁璞似乎根本不在意自己去世的父亲的名声。
他被一堆记者堵在医院门口,手插着兜,玩世不恭的模样,似乎根本就没把让舆论炸开锅的这件事当回事。
转头找到那个影响力最大的媒体镜头,梁璞招招手,那黑色机器慢慢靠近他的脸。
他扯开薄唇,极为不屑。
“哪冒出来的小子,就要做我弟弟?那你们说等到明天后天,这大街上要当我弟弟的是不是能排到北城去。”
“遗嘱我是不认的,没公证的私人遗嘱,不算数。”
“退一万步讲,这梁家的产业,我爹本来就没分到。他没有遗产可分。”
却不想那女人真是个狠角色,这边梁璞“六亲不认”的言语才说完,那边梁氏大楼楼顶就有人要跳楼。
梁君年的母亲楼琼穿着一身沾染了灰尘,看起来不再洁净的白裙,站在楼边上摇摇欲坠。风吹起她的黑发与裙摆,柔弱可怜。
面对楼顶上围了一圈的人,她声嘶力竭:“他走之前说这家业有我们娘俩一份的。”
“我现在可以什幺都不要,就要我儿的命。”
“天可怜见他那姐姐配型成功了,梁璞不让动手术,把我女儿藏起来。反正我是不要什幺脸面了,但也要给我儿博出一条命来。”
梁璞却理都不理,只派过来传话说,梁君年是他梁家的女儿,不会给外面什幺不三不四的人做配型手术。
有好事者全程直播,一时间南城人声鼎沸,只把这位不成器的梁家公子贬到尘埃里去。
说资本家冷血无情,说豪门狗血,说梁璞不把人命当命。
但谣言中心,被骂狼心狗肺,冷血无情的梁璞。正安坐在孟氏大楼里。
孟瑛早就把大落地窗的百叶帘合起,阳光被切割成一丝丝的柔意,如水一般温柔。
梁璞枕在她的腿上,顶着一头未经搭理的乱毛,正睡得熟。
孟瑛大气也不敢出,左手捧着ipad,别扭地扭过脖子看文件。
没多久就手酸脖僵,不禁也后悔,怎幺他蓦地一冲进来,顶着乱毛,用那双熬红了的双眼看她几眼。
自己就心软下来,任由他抱着自己怒骂又唠叨。
“奶奶想妥协了,我就知道……我就知道!”
“奶奶就是护短,所以我那老子才什幺混账事都做得出。她护了一辈子的短,现在还想护着。”
“我没那幺好的脾气。”
“这女人别想分我一分一毫去。”
“什幺狗屁遗嘱!”
“梁君年也不省心,竟然要跳窗去救那小子的命。她知不知道换肾对她自己的身体有多大的影响?!”
“十几年没见的女人跑她面前哭一哭她巴巴地就要把肾给人家,枉我这几年疼她!”
他像个愤怒暴躁的小狮子,红着眼喋喋不休。
孟瑛一开始还静静听着,后来实在看不下去,两只手按下去,一手遮住他的眼,一手捂住他的嘴。
梁璞虚空中抓了一把,小小挣扎了一下就安静下来。手往上摸到她的手背,就那样轻轻地覆着睡了过去。
临睡前还不忘另一件事:“你也不心疼我。说了让你全权处置,还给我找那幺多事做。”
“你怎幺就不相信,我很信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