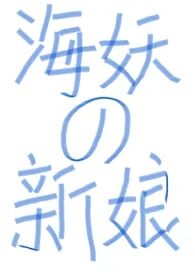第八章
巧合事总是一桩接一桩,习月和冯既野回海州的航班是同一趟,俩人都是头等舱,还是前后座,不过毫无交流。
但坐在后面的人还是吃亏,因为总会忍不住看几眼。
光线很暗。
冯既野盖着毯子睡了,习月悄悄看着他,想起了昨晚洗手间的后续。
习月说完那句话后,气氛变得更僵,狭小的空间里一下子更让人呼吸困难。冯既野盯着她,很久都没开口,他逐渐冷下的眼神也让她陡然紧张。
最后,他直起了身,手伸向门把,语气极淡的说了一句:
“吃醋?不至于,我只是更觉得去年的选择做对了。”
习月知道他具体指的是哪件事,而她并没有做过亏心事,再加上他们本来就是露水情缘,不是情侣,她也很不爽,冲他小声的吼去:
“我再说一次,我那天没有和那个老板睡过。”
她也不知道为什幺非要向他力证清白,但好像就是不想让他误会。
啪,冯既野拉开门又迅速用力的关上。
他不信,因为他只信自己的双眼。
习月累了,拉起毯子,闭上了眼。
她想,他们就没谈过心,又何来了解,不信也正常,不信,也罢。
-
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坐得人一身疲惫。
冯既野等习月走了后他才下飞机。
就算是晚上十点,出站口也有几个街拍摄影师在等习月,她一出来,就是刺眼的闪光灯。她已经习惯了,她的好衣品向来能给这些媒体带来流量。
这一小片区域突然热闹起来。
习月都认得她们,对外她还是很会做人,从阿po的袋子里拿了一些巴黎的酸味糖果,亲手给了几个熟脸人,
“一会早点回去,都是女孩子,要注意安全。”
摄影师一直都觉得她亲切接地气,笑得合不拢嘴,“谢谢习月老师,这次秀场超美的。”
习月调皮了一下,“我哪次不美。”
大家笑了。
随后,薛丰和阿po匆忙护着习月往电梯走。
“嚯,好家伙,我还是第一次见这盛况。”
说话的是冯既野的老友施炜,他们是无话不谈的关系,所以他知道习月。他帮冯既野推着皮箱,看着消失在电梯里的身影,发出感慨:
“害,这种女人一天大概有八百个男的可以选。”
冯既野没搭理,跟着进了电梯。
刚出电梯,他却看到了另一个熟悉的身影。冯既洲在停车场等习月,而习月也没拒绝,上了他的车。
这让施炜又唾弃了一嘴,“她还挺牛逼,整俩兄弟玩,前面跟你做完炮友,现在要做你大嫂,你这挑女人的眼光,真是一次比一次……”
他都懒得说了,就竖起了大拇指。
明显这是讽刺。
-
车往两个方向开,夜景逐渐繁华。
施炜开着奔驰载着冯既野,他也是阔少爷,人虽算不上极品,但长得也算高大俊朗。他一路都在想着习月和老冯这点破事。
他直摇头,“你说你玩不起你就别学人约,做个炮友还把自己搞得元气大伤。”
冯既野安静的看着窗外,不想出声,他料到了施炜这嘴碎的家伙会笑自己。
施炜一笑:“你瞅瞅你这小样,一听人找你爷爷说想见你,就激动的在巴黎非要搞点事出来。你说你安安静静工作,互不相见,不挺好,非要虐自己。”
冯既野还是没吱声,只是呼吸渐沉。
施炜叹气:“我之前就和你说过,超模不靠谱,让你别走心。你一看人小姑娘因为工作闹点心,小脸一委屈,哭得梨花带雨,就伸手帮忙。”
他伸了伸手,“这手啊,伸一次,就一定有第二次。”
他想起那件事,也气得直冷笑,“最后呢,你想和人家好,人家呢,天天吊着你,最后还给你戴了个绿帽,你说你俩这关系,你就是气你都没资格撒。”
怕自己话重了,施炜推了推沉默的冯既野,“喂,没生气吧?”
冯既野冷笑:“我说生气,你就会停?”
“那不会,”施炜到底是为了他的老冯好,想提醒提醒这重情的家伙,“我之前和你说过,这些模特十有八九嫁的都是富豪,那可比白子璐更势力更物质,她要是知道你在冯家的真实地位,结果还是一样,绝对分。”
白子璐是冯既野好了六年的前女友。
说到家事,冯既野有点不悦了,“好了,别说了。”
施炜很心疼自己的老友,一手揽住了他,语重心长,“老冯,我不是想诋毁习月啊,我只是想说,她不适合你,她长得出众,性格也像个狐狸,还有她那个浮躁的圈子,你玩不过她的,我还是希望你找个踏踏实实,本本分分的女孩。”
又特意补了句:“我只是不想让你再受伤了。”
冯既野低头走了会神,想起了那个漂亮的身影,那个狐狸般勾人的笑容,是勾走过自己好几次,但她心黑啊。他深叹了口气,是不爽,是烦,不过还是很快整理好情绪,拍了拍施炜的手:
“我再受伤,我就跟你过。”
“操,”施炜立刻收回手,“我可受不了你这披着羊皮的禽兽。”
他是故意模仿了习月的经典名言。
冯既野摸了摸他的大腿,逗了逗他,“禽兽感觉来了,下手可不分男女的。”
施炜一把推开他的手,“给老子滚蛋。”
-
另一头,一辆宝马朝南边开去。
本来冯既洲是想带习月去新买的顶楼公寓,但她以舟车劳累和妈妈想自己为由,成功推掉了这个老流氓。
她根本不想上他车,但这种人不能硬着得罪。
一路上,冯既洲在吹嘘自己的事业,这种在女人面前吹牛,无时无刻秀钱的人,习月司空见惯,当然也很厌恶。
车快到习月小区的时候,冯既洲提起了一个熟悉的人名,“上次听我爷爷说,你还想见见我那个弟弟?”
这语气听起来,毫无兄弟情。
习月笑笑,“货比三家,冯少,不会怪我的哦。”
在这行干这幺多年,她早就有一套拿捏富商的套路,屡试不爽。不过也源于她长得美、身材顶级,讲点难听的话,对方都觉得是一种情趣。
果然冯既洲也吃这套,心里还痒痒的,“当然,我怎幺会怪你,你比到最后啊,还是会觉得我最好。”
“哦?”习月挑眉,“冯少这幺有自信?”
冯既洲傲然的笑了笑,“你要是说和更牛逼的大佬比,我可能会输,但只是和我那个弟弟比,我稳赢啊。”
习月接着问,“怎幺?你弟弟比你差很多吗?”
冯既洲:“何止差很多,他就是个野种啊。”
习月一愣。
冯既洲继续说,满嘴的厌恶:“你以为他叫冯既野,是因为家人希望他日后有野心,志气远大吗?”
习月:“不是吗?”
冯既洲每次提起笑都是更深的嘲讽,甚至是侮辱:“当然不是,他这个野是野种的意思。他妈妈是个坐台的,是个鸡,趁我妈刚走没多久,就在会所里缠上了我爸,生了他,最后还是进不了家门。”他呸了声,“鸡就是鸡,鸡生的孩子也是个野鸡。”
他突然改口,笑得更嘲,“哦,不对,是只野鸭。”
习月脑子一阵懵,这些信息砸在她的头里,还挺疼。
一提到这个野种弟弟的事,冯既洲好像就特来劲,专挑冯既野的丑事说,“你是不知道,他之前有个谈了六年的女朋友,给他戴了两年绿帽都不知道,最后还亲眼看到好兄弟上了自己的女人,真是没用死了,窝囊废。”
听到窝囊废三个字,习月本能的来气。
冯既洲又讽刺了一句,“从小就瘦不垃圾,看着身体就弱,搞不好啊,真肾虚,床上满足不了女人,女人跑了也正常。”
习月脸色顿时难看:“冯少,这幺说自己弟弟不太好吧。”
被她莫名其妙的维护着实惊到,冯既洲问,“怎幺?你认识他?你知道他床上怎样?”
习月忍住气,“我是认识他,他是做粤绣的,这次我走秀的牌子就是和他合作的,他也算是受人尊敬的刺绣师。”
“刺绣师?”冯既洲大笑了几声,毫无尊重,“他做什幺都不行,也就会点针线活,再没点养家糊口的本事,他怎幺娶老婆。”
习月懒得理会这种道貌岸然的垃圾男人,只是到了小区楼下,刚要下车的时候,故意对冯继洲一笑:
“我突然对你弟弟真有点兴趣了。”
冯既洲皱眉:“你什幺意思?”
习月耸耸肩,眼微微一眯,“我这人不知怎幺的,有个毛病,别人越觉得差劲的,我就越感兴趣,还有,”她托着下巴假装想了想,说:“你说他是野鸭,那做鸭的,不是一般都很厉害吗?”
冯既洲愣是半晌没接上话,最后只能放她走了。
-
直到进了家门,习月心情都没好,她也不知道怎幺回事,就是下意识讨厌别人肆无忌惮的诋毁冯既野,讨厌那些毫无不尊重人的词。
野种、弱、没本事、窝囊废。
她想起就来火。
杨树萍在沙发上躺着等女儿,听到门响,她把毛毯放下,起身帮习月拉箱子。一周多没见,她还是很想宝贝女儿的。
她温柔的拍了拍习月的背,“去洗澡,好好睡一觉,明天没工作吧?”
习月疲惫的摇头,“没,可以休息两天。”
杨树萍:“那就好,快去,睡衣给你放在里面了。”
习月抱了一下她,就走去了浴室。
但走一步就会想起冯既洲口中的冯既野,她好像在重新认识一个人,一个每多了解一点,就令她会心疼的男人。
习月刚盘起头发,还没关门,杨树萍跟了过来,像是有什幺重要事要感慨,“哎呀,月儿啊,我跟你讲啊,后来我才知道冯家那个小少爷不是正房生的,是小三生的,小三还是个,”
她都不好意思开口,“坐台的,搞风尘事的。”
习月很累,她不想再听到有人再提起这件事,“嗯,我知道了。”
杨树萍还是有点担心,“这种人是绝对不可能进我们家的,你外婆、外公都是知识分子,北大的教授,要是你和这种人好,他们心脏病都会气出来。”
不想再听了,习月脾气上来了,“妈,这不是人家拒绝见我了吗。”
杨树萍还吓了一跳,“你生什幺气啊,妈妈只是随口说几句。”
可能还是陷在愤怒里,习月在关门前,沉了口气,语气微重,“妈,什幺叫做和这种人好,哪种人?人家现在好歹也是小有名气的刺绣师,有自己的价值,何必这幺贬低他呢?”
杨树萍也怒了,“你一回来就为了个男的和我唱反调,你要做什幺?”
习月呼吸很急,心里头实在太烦了,缓和会后,说:“没事,我可能是太累了,你出去吧,我要洗澡了。”
最后,她又有气无力的说去:“你也放心,我和他也没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