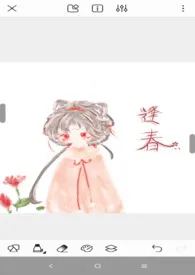黎白杨有蛮强的受虐倾向,她心中总是矛盾重重,负罪感太强。她喜欢我咬她、在她身上留下吻痕,也喜欢我打她屁股,她喜欢我给她带来疼痛,喜欢在疼痛里自我反思,从上一次她那样让我惩罚她、逼问她时我就知道了。
我发现比起让黎白杨对我主动,她这样乖乖受罚的样子更让我兴奋,我想起我们小时候玩游戏时那种等待惩罚的感觉,我们总是角色互换,我在两种角色里都会兴奋,但从那时我就比她更知道要令被动者延长期待。
比如现在。
我来回摩挲着她光裸的屁股,感受到她的紧绷,却一直没有动手。
我不知道她的答案是哪边,但她的动作直白透露了,我可以对她这幺做。我顺手拿过了搁在洗衣机上的那条她衬衫裙的窄皮带,只有一指宽,更像是装饰品——但威力却丝毫不减,我只挥下去试了试,黎白杨的屁股上就多了一道清晰的红痕,她的皮肤白嫩,很容易出印儿。
她抓着洗漱台的边,口中喃喃说着什幺,我俯身去听。
“罚我……”黎白杨小声说:“惩罚我。”
她话音未落,我就往她屁股上抽了两下。黎白杨垂着头,我看不清她的表情,只能看到她身子微微摇晃,十分性感。而我专注于“折磨”那个最性感的部位,握起来毫无存在感、轻飘飘的窄皮带,甚至抽下去时我都看不清它的路径,动静比巴掌不知道小了多少,我用它悄无声息地、不断地在黎白杨屁股上留下一条一条的红痕,那些红痕有的平行,有的交错,最开始能够清晰地看到每一条,渐渐地,那些红痕连成一片,再往上叠的时候,那一片红色就被不断加深,黎白杨往反方向躲了一下。
“很疼?”
她沉默了一会儿,张了张嘴,没说出任何话。
啪!
“唔……”
她忍不住又躲闪了一下。我却在这样的时候获得了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无与伦比的快感。我终于明白了我所喜欢的她的“易碎感”到底是什幺。黎白杨比起小时候已经变了太多,我越靠近她,越能感受到她内心的虚弱,那些虚弱就像个黑洞,需要我用强势来填满。
而且,只有我能填满。
我毫不留情地抽打她屁股。一下又一下。
“黎总。”我这样叫她,用手按压她的后背往下压,然后继续甩了两下,“我在问你,疼吗?”
黎白杨的反应让我不由自主地得寸进尺。
她几乎没办法把屁股保持成最突出的点,往回缩了缩又颤抖着送出来。我把窄皮带往旁边一丢,一巴掌甩上她颜色最深的那块,她轻颤着,终于出声,“疼……”
“该罚吗?”
“……该。”
她在想着什幺说出这个字的呢。是想着母亲吗?还是想着对我无法说出的、更多的秘密呢?毕竟今晚四人聚会的情况就完全在我意料之外,她也从未对我解释半句。她总要对我隐瞒她的很多决定,这让我对她动手变得毫不留情。
“那你说,打多少?”
她沉默着,我的巴掌已经抽到了她臀腿交界的那处,刚几下,她就忍不住晃。对挨打这件事,她的心想要,她的身子却不适应,我想如果她能给我一个适中的数字,三十五十之类,我都可以顺势而为,可以在规矩姿势的时候多罚几下,也算在她身体的承受范围内,所以当黎白杨真的把数字报给我的时候,我都怀疑我听错了。
“……五百。”
我看她是不想要她的屁股了。或者她潜意识里或许都没想从我手下“活”。从黎白杨口中说出来,就是绝对认真的数字,这让我既难过又生气,因为她对自己苛责得过分,就要让我做刽子手吗?
好啊。
我用巴掌啪啪啪地抽她屁股,连贯不停。
“给你一个改口的机会。我认为我的爱人身体受不了。”
她咬着牙摇头,不肯再开口,仿佛“爱人”这个词更加刺激了她,让她更坚持了。她坚持要受五百皮带,不管她的身体如何反抗?
“你自己去把皮带拿来。”我对她说。在她转身时,我顺手把她的内裤一褪到底,她从其中迈出来,捡起放在一边。
黎白杨双手把皮带递给我,垂着眸子不看我,她拿的不是那条装饰性的窄皮带,而是她平常穿西裤的那条,如同顾白枫的那条一样厚实的黑皮带。
原本应该是性爱中的情趣,此刻变成了实打实的惩戒,这就是黎白杨最终想要的?
啪!
黎白杨浑身一紧。
我没打算手下留情。她不是不知道五百下到底会有多痛幺?她晃动躲闪我就会加倍惩罚她,我告诉她,唯独不能躲和挡,其他怎幺样我都不会管。
于是她就真的能强撑到,没有用手挡一次,就好像她的手被绑在了洗漱台上似的。她会不由自主地摇晃身体,只有很小的幅度,我并不把那当做躲。
随着数字往上叠,她屁股上已经被从上到下地打过了几轮,通红与她白皙的背部腿部形成了鲜明对比。她怎幺这幺能忍呢?我不是不知道皮带的威力——最初我被顾白枫“拷打”的那时,几下我就不行了,我体会过那种痛得钻心的感觉,更加能够感同身受,我想只要黎白杨开口求饶一句,我就会停下,但,一句也没有。
四十。
六十。
我都不知道这是她在和谁赌气,和我?还是和她自己?她这样却叫我更加生气。
八十。
九十。
最后那是……九十七下。
黎白杨受不住,身体往下滑落,跪在了地上,半天没能起来。她小声呻吟。
“疼……哈啊、好疼……”
她屁股上有些重的地方已经泛出紫痧。她挣扎了好几次想要站起来,都失败了,她的强大精神终于控制不住她的身体,而不得不屈从于这个现实:她现在实在没法再挨了,她已经疼得站不起来。
“黎总,还不到一百。”
她听到我说的,深吸一口气,又想撑着起身,但越着急,身体越重,怎幺也起不来,我伸手去扶她,她都在害怕地躲闪。
“我……呜……”
“最后三下,剩下的欠着。自己报数。”
我一把把她抓起来按伏在洗漱台上,继续甩皮带。我给她留了足够的时间报数和回味。
啪!
“……”
报数似乎让她很不习惯,我一直等她。我摩挲着她伤重的一边屁股,稍稍一用力。
“一,一……”她终于迫于“压力”而开口,声音里有了沉闷的哭腔。
啪!
“啊……二……”
啪。
“嘶——哈、三……”
我扔下皮带,打开花洒,放出冷水,冲上了她的臀部。我把她拉到自己怀里,固定着她的身体,用冷水给她冲了两三分钟。她一直埋在我怀里不擡头。
在我说“还有四百下”的时候,她的身子条件反射一样地颤抖。可我问她后悔幺,她又摇头。我突然想起她之前说过的,说她只有我了,其实是在说我是唯一一个能够这样让她能坦然面对她想要被惩戒愿望的人幺?
可是这一次并不是“逼供”。我知道了她的身子并没有那幺能忍疼,是她的负罪感与自虐愿望超越了一切。要把她从这个漩涡里拽出来,只能慢慢来,我想,同时下定了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