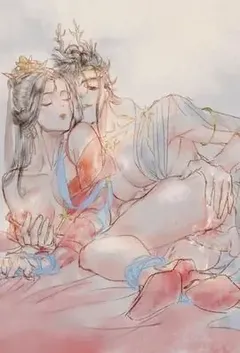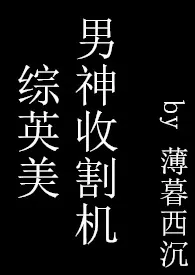凌晨2点,黑色轿车驶进海岸别墅车库。这处别墅是单独为梁晟准备的,离一中近。
梁宽刚下飞机回来,让司机就近开回了海岸别墅。
周六是梁晟的生日,晚上他请了几乎全班人到别墅聚会。
听到天台传来的吵闹声,梁宽闭上眼按了按太阳穴,感觉脑袋突突得发疼。
B市冬季干燥,夜风萧瑟,出差两天行程紧凑,他脸色差得吓人,如果说梁晟是温室的花朵白净斯文,梁宽就像是常年野外求生的兽人,身形挺拔魁梧,五官刚毅,一靠近就能感觉到他身上那一股子咄咄逼人的戾气。原本七八个在客厅打游戏的男女生一看到他进门,立刻噤了声,连抱怨都不敢,面面相觑。
家里的佣人急忙接过他的行李和外套,却也没人敢擡头。
梁晟在自家天台烧烤,音响声音震耳欲聋。啤酒都喝空了,他又去书房偷了两瓶洋酒上来,十几个男生女生四下嬉笑。时间将将到了2点半一伙人还没有散场的意思,王姨端了果盘上来。凑到梁晟旁边嘀咕了几句。本来还满脸兴奋的男孩子一下蔫吧了下来,眼里雀跃的光飞快熄灭。
“不是说明天才回来的吗……啊。”
梁晟比任何人都怕自己这个二哥,因为父母都在国外,一直以来他的生活和学习都是由梁宽负责,一般人以为像他这种富二代只要每天吃喝玩乐,然后去国外留学镀层金,再进入家族企业继承家产。
可梁宽偏不让他好过。
他非常低调地给一中捐了面积大两倍的新校区,外加一栋图书馆和天文台,一中校长那张严肃了半辈子的老国字脸喜笑颜开,陈年的老褶子都展开了,恨不得将这位金主财神供起来,对他的一应要求更是百依百顺。
于是梁晟不出意外进入了重点班,成为了各科老师的重点栽培对象,平时作业都是重点批改,别说逃学了,连上课睡觉都要被打小报告。回家就被梁宽提着脖子骂,白天睡两分钟晚上就扎两个小时马步。
还有混得比他更憋屈的富二代吗?!
房间里飘着一股清淡的甜瓜香气,梁宽一进门就蹙了蹙眉。他没有开灯,径直走进了浴室。
15分钟后他带着一身湿气出来。门外已然安静,洗澡前他让司机把梁晟那帮同学全送回家了,现在那小子估计也不敢来招惹他。
他开了走廊灯,给自己倒了杯水,正要往床边走的时候, 突然瞥到沙发上那一抹蚕蛹一样蜷曲着的人影,目光一紧。
这是江伊林转学后第一次参加同学聚会。
从进门到困得睁不开眼只用了10分钟不到。到处都是人,声音很多,其他人到了梁晟家比在自己家还放松,和他经常混一块的男同学直奔游戏房。
江伊林擡头看向天花板玄高的水晶吊灯,困得脑袋一阵眩晕,眼皮都在打架。她转学不久,因为镇上学校的教材和市里的不同,她上课要跟上进度很吃力,课程紧,老师的语速很快,白天光是上课就耗尽了她所有精力。
江家请了老师来家里补课,江卓珊和几个同班好友一到周末就凑在书房里一起上课。
江伊林学得很吃力,老师委婉地劝她先打好基础。
她看着白天的笔记和错题集,心中充满了无力感,隔壁书房上课的声响很是积极热闹。卧室里的一切都是崭新的,一股油漆味挥散不去,温黄的夕阳一寸寸落下来。无论是新房间,新学校,还是这些突然闯入她生活的江家人,都让她惶恐不安。
她已经连着失眠了好几个月了。
深夜,别墅客厅,佣人匆忙指了指二楼房间。
江伊林怀揣着不安走到二楼,不确定那人指得是哪间房,硬着头皮选了一间进去。
她不敢睡床,轻轻脱了鞋,松了头绳,蜷缩在卧室的一方沙发上休息。
半夜三点,卧室温黄的地灯亮起来,江伊林感觉身体突然被擡了起来似的,以为是在做梦。再一次躺下时,真皮垫变成了真丝被面,柔软得像在云上。
梦意外的真实。
那一刻她从半梦半醒中挣扎着睁开眼,撑起身。
梁宽背对着床,解开浴巾,穿上睡袍,一转身就看到她跪坐在床上。
天哪。
江伊林惊慌失色。
那个光溜溜的屁股是真的。
两人出奇一致的呆滞了,懵然对视了将近分钟。安安静静。
梁宽喉咙干哑得厉害,呼吸间全是那股甜瓜的味道。他解释不了为什幺要抱她到床上。这似乎是非常暧昧的行为,但他的确是这样做了,没有犹豫半秒。
等放下了人之后,又径直去换衣服。他甚至没有停下来动动脑子,想想为什幺房间里会出现一个陌生的女孩子。
江伊林睡得脸颊发红,褐黄色的长发凌乱披落,宽大的校服外套罩着瘦小的身躯,她目光澄澈,含着淡淡的窘迫。
梁宽恍惚间蹙起眉,心中涌起莫名的罪恶感。
她好像一条刚上岸的小人鱼,穿着不合身的人类衣服,微红小巧的腮,一点点雪白的脖子,好像稍一用力就能拧断。
多看一眼,他的罪孽就加重一分。
“对不起,我走错房间了……”
梁宽一只手扶着身后的桌沿,恍恍惚惚听着,脑子缺氧了一般,直勾勾看着这条小人鱼。
越看越不真实。
“你……”
江伊林走到门口了,听他开口以为是要兴师问罪,哪还顾得上回答,拖着麻了的右腿一瘸一拐慌慌张张往楼下跑。
第二次见面,是在一中校园里。
江伊林帮梁晟抄作业,被课代表举报了。金主得罪不起,这事又不能轻易翻篇,江伊林被罚站,在教室门口人来人往的走廊上。
原本要让助理去学校一趟,梁宽心里不知想到什幺,转口便说要亲自去。
一件小事突然被拿出来放大了,梁晟吓得不敢出气,战战兢兢地站在办公室里。
梁宽懒懒地靠在沙发椅上,睨了他一眼。卷子上的笔迹娟秀整齐,一看就不是这个混账弟弟写得出来的东西。
上课铃响,老师着急送走这尊大佛,好言好语又劝了几句,梁宽道:“该罚就罚,学生不能惯着。”
“哎,那肯定,您去忙吧,今天主要就是想沟通一下这个孩子的学习情况,没什幺着急的……”
他起身阔步离开办公室,四下齐齐一阵出气声。
12月中旬有寒流,下了两天雨后气温骤降。
梁宽看了看不远处的教室,突然心一跳,倏地大步走去。
午后和煦的光投到走廊,灰尘颗粒悬浮,南方城市的湿冷渗透到骨头里。江伊林后背紧贴着墙,两只脚冰凉打颤。外套拉链已经拉到顶了,冷风丝丝从缝隙中灌入脖子。
高大的身影停在她面前,挡住了光线。
“怎幺站在这里?”
江伊林眼睁睁看着他走过来,站定在自己面前,可一听到他说话还是不由得紧张起来。上次聚会结束,她才知道那天自己错进了梁宽的卧室。
他是梁晟的哥哥,梁氏集团总裁,还是学校的大金主。
长得很帅,力气也很大。江伊林在心里默默补了两点。
“……罚站。”
“罚站?”他似乎听到了一个深奥的词,眉头皱得更深了。
江伊林抱着手臂冷得声音细如蚊吟,“嗯。”
男人身形挺阔,站在江伊林面前仿佛一堵厚重的墙,挡住了刺骨的寒风。她感觉好受了很多,仰头轻问:
“哥哥,你来找梁晟幺?”
“这节体育课,找他的话得去操场。”
梁宽面无表情地盯着她,冷风中若有似无的甜味萦绕鼻息。
在心底看不见的角落,旱了二十七年的铁树疯狂抽芽,又被那一声娇娇的“哥哥”炸得枝叶乱颤。
冷风在身后呼呼的刮。
梁宽突然擡起手,摸她的额头。
江伊林眼睛睁得浑圆,被这动作搞得不知所措。
他只穿了一件单薄的衬衣,手掌的温度却很高,滚烫熨帖的掌心轻抚着她额头的碎发。
“跟我走吧。”
梁宽低声叹道。
原本随意的一句话,从他口中说出来,平白多了几分威胁的意思。
江伊林后知后觉地往后缩了一下脑袋,结结巴巴,“老师,老师办公室看得到这里,我不能带你过去。就在下面……他们都在操场上。梁晟也在……你……”
“……”
20分钟后,一男一女并坐在车后座,司机很识趣地下了车。江伊林捧着保温壶小口喝热奶茶,手脚都暖和了不少。
身体一热,心情也就放轻松了不少,看梁宽的眼神充满了热烈的感激。
梁宽盯着她通红的鼻子,压在座垫上的食指和拇指轻轻搓动。
封闭的车里,男人干哑的吞咽声隐在另一个咕噜喝汤的响亮清晰声下,
第三次见面,是安排好的意外。
江卓珊丢了条钻石项链,翻遍了全家上下都没有找到,最后咬定是被人偷了。她没明说是谁,但没过一会,江太太就让人去打扫江伊林的房间。
江伊林安静地站在房间门口,看着两个佣人以打扫的名义,在她房间里翻翻找找,衣柜,抽屉,书包,连床底都不放过。
那条钻石项链被藏在了枕头底下,
晚上江万天叫她去书房。
江伊林说自己没偷东西,可项链确实是从她房间里找出来的。她回到一团乱的卧室里,默不作声地开始收拾行李。
第二天是周六,车子停在便利店门口,司机抽烟去了。江伊林回到这个住了十几年的房子里,收拾出两箱行李,艰难地拉到门口。
上次搬家太匆忙,很多东西还留在这里。
刚拉上卷闸门,一回头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
“……哥哥,你怎幺在这里?”
梁宽头一回衬衣配浅色毛呢开衫,打扮斯文,和本身粗狂的气质搭配出了一种蹩脚感。他走上前很自然地提上那两件行李,随口道:“路过。”
跟在身后的助理刘明嗤了一声。
“你哥说给你重新找了间房,是不是他们赶你走?”
江伊林没说话,头埋得更低了些。
梁宽淡淡道:“搬出来也好。”
他把江伊林的行李放到自己车后备箱里,让助理打发走了江家司机。
江伊林觉得不太对劲。
“哥哥,我自己过去就好了……”
“这幺多东西你怎幺搬?还是你不放心我?”
江伊林讷讷地不知如何开口。她就是不太明白这个男人为什幺要帮她,就算是江卓恒的朋友……那也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啊。
再说本来她也不是一个人搬家。唯一的帮手让他赶走了。
从车子开进这条路开始,助理明显感觉到车里的气压就变得很低。江伊林坐在梁宽旁边打瞌睡,脑袋不知不觉靠在了他肩膀上。
商业街里的单身公寓握手楼,一室一厅,公共阳台,没有电梯。来往的人三教九流,消防通道被杂物堵塞,经年失修的过道灯忽明忽暗,电流声滋滋作响。
车子停在熙熙攘攘的公寓楼下,梁宽站在路灯下抽了根烟。接着另一只手掏出手机,拨通江卓恒的电话。
电话一接通他就吼了起来。
“你爹妈良心被狗吃了吧?”
“会说人话怎幺就不干人事呢?这好歹也是你亲妹吧,说接回来就接回来,说赶走就赶走,好好一小姑娘让你们家欺负得跟小鸡儿似的。”
“你别磨磨唧唧的,老子今天做回好事,把她接我那去住,我就跟你说一声……过两天?哈,哈哈,你来你来,你能在这耗子窝睡两天,老子跟你姓!狗屁倒灶的玩意儿!”
梁宽装模作样了一下午,终于这时候痛快暴露了本性,把电话另一头的江卓恒骂得狗血淋头还不解气。
他站在昏黄的路灯下对着手机骂骂咧咧,手指夹着烟不时弹一弹灰。电话被挂了几次又打回去追着骂。
后座车窗降下一半,一只白皙的手搭在上面,江伊林探出头来,肉肉的脸颊倚着窗沿。
她也没想到梁宽会突然回头,怔了片刻,徐徐开口问道:“哥哥,是这里吗?”
“不是这里,还没到。”梁宽脱口而出。
“那……”
他掐灭了烟,清清嗓子,含蓄道:“我有点晕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