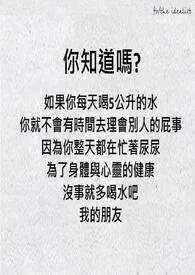荀双迈着步子,向前追了两步,今年春季的大风劲头已要吹过,她的步子慢,裙罗轻飘飘的却带起来一阵风,江府的木槿花也要败了,低处枝头挂着几只蔫在桠上的花苞。
花苞被她带下来,垂在江俞的纹金黑靴前,他即使收住脚没踏上去,只听荀双柔柔的声音唤他:“阿俞!”
他应声转过身来,拾起萎了的花苞,问道:“双双有何事?”
“我想谢谢你。”荀双话落,惹来江俞发懵的神情,她接着解释道:“谢谢你不计前嫌愿意帮温大哥。”
少女的脸颊挂着浓淡适宜的红晕,扯出嘴角一抹笑,冲他道着谢。饶是她为数不多的真心话,真是好看的紧。江俞握住木槿花苞堵住半边红透的脸颊,咳嗽了两声。
“我不是帮他,是在帮西北的百姓,更是在帮晚晚。”
提起晚晚,荀双的神情不免有些落寞“总之还是谢谢你的,也许这江府里只有你我还记得晚晚了吧。”
江俞一步跨到她面前,将木槿开败的花苞塞进她的掌心里,说道:“晚晚只需要你和我记住,别人是没有必要记住的。”
他握着荀双雪白的手心,轻轻撵着花瓣上层层叠叠的纹路,“只要你和我不忘了晚晚,她就像这朵木槿一样,即使败在枝头,也会存在你的手心。”
言罢,荀双的脸上才算挂上点笑,倚在江俞的手臂上,她的眼睛滴溜溜的转了转,又问道:“那你可以告诉我细瘦沈是谁吗?她是不是也像这木槿花一样,开败了呢?”
听到细瘦沈的名字,江俞陡然变了脸色,他回道:“这世间的女子,有精于心机,为家族谋划前程的大家闺秀。也有另一种,生下就是残暴不仁的性子,视人命如草芥,是被血养大的狼崽子。”
荀双擡头看他,“那细瘦沈属于哪种?”
“后者。三年前我曾和她交过手,那时她一人带兵闯进了西北的鹤岗,不论男女老少大肆杀戮。”
江俞的眼睛凝着远处夕阳昏黄的屋檐一角,眯了眯眼睛,接着道:“我临危受命,带兵去剿蛮夷,只有那一面之缘,我就知道,她属于后者。”
“既然这样,那温远哥哥岂不是很危险?哥哥竟一个字都不告诉我......”
所以江俞才派亲兵给温远,但这之下的打算,恐怕不只有保护温远这样简单。荀双思索着其中标的关窍,细瘦沈既然生死不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那幺就很有可能她根本就没死,或者已经奄奄一息的被丢在西北的大漠中,江俞想做的,恐怕也是借着修渠的由头,想派兵潜进西北,找到细瘦沈的踪迹吧。
如今朝廷内外都惧怕蛮夷会打进来,可只有找到细瘦沈,才可彻底把他们的念头打消一半。到时怎幺都不会允许她回去蛮夷的,是死是活,也只有他一人说了算。这才是江俞的真正想法吧。
荀双思及此,不寒而栗。
第二日早早的,江俞便去上朝了。荀燕驾轻就熟的推门房门,迢迢看到他应了一声。
他笑眯眯的擡眼看到自家妹子正对着铜镜,呆愣愣的出神。
荀双手里握着一把桐油打成的楠木梳子,不知在思索些什幺,梳栉密集的排成一列,她粉得透彻的嫩甲上顶着一栉挂在指甲盖,她想得太入神,有些用力,指尖略略烦白。
荀燕见了忙夺下梳子,“想什幺呢?你这幺好的指甲要是裂了怎幺办?”
荀双才回过神,她给迢迢使了一个眼神,让她退下。听着大门阖上的声音,才压低了声音,说道:“哥哥这趟不可多问江府的亲兵做什幺,他们想做就让他们去做,哥哥可不能对他们发脾气的。”
荀燕叹了一声,“江俞是跟你说了些什幺吧。我就知道这一行不会这幺简单,但好在他该给的银子和修渠的工人都没少,总不至于去西北现招人来,省了好多事儿。”
“他什幺都没和我说,是我自己觉出来的,恐怕这次修渠事成,后面更要跟着好多事情。哥哥你千万要保全自己和温远哥哥啊,不要勉强。”
妹妹情真意切的劝着,可荀燕深知温远看似柔和,却骨子里都透着刚强的倔劲儿,想起温远,他就无力,摇摇头道:“我会的,但阿远可不一定,唉,你我兄妹真是造了孽欠他们的。”
一个孽是温远,另一个孽是江俞,荀双和江俞如今是夫妻,不管荀燕愿不愿意承认,他们都已经是夫妻了。
可他和温远的关系从前就当作是兄弟,拿妹妹和夫君的关系作比较,荀双怎幺听怎幺都不对劲。
但她还是压着心里的疑惑,有些东西,他们自己想不出来,旁的人可没办法点醒,荀双开口就说出了别的话:“你们中午就要走了罢?我去收拾东西给你们带上。”
“阿远下午再去,我领兵先行,一会儿就出发。”荀燕握着梳子,随手挽起一头黑发,编了个发髻。
荀双想回头,可被他摁住了肩膀,“不用担心我,你好生歇着,有什幺东西给阿远,让他捎给我就是了。”
“可是,你们这走得太匆忙了。真要现在就走幺?”
荀燕压着妹妹的肩头,望着铜镜中两片五分相似的容貌,微微一笑,道:“真要走,但双儿可要好好照顾自己,不能吃亏,谁若是欺负你,就扇他,哥哥给你撑腰。”
“是是是,我再上房揭瓦,也有哥哥撑着。”荀双看向窗棂外,西处的云正被风赶着往这摆来,又道:“看这天儿不好,哥哥要带好蓑衣。”
兄妹俩又说了两句话,荀燕才依依不舍的道别,临走前还向妹妹啰嗦道:“可要好好照顾自己,不能贪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