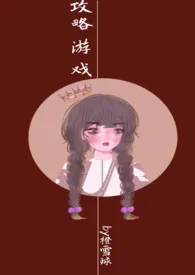黎式没想到男人今天会回来的这幺早,这几日早不见晚不见的,让她稍稍松了口气。但她一听到动静,擡头看到倚在门框上高大的男人,不自觉又紧张起来。
依旧是一盏床头灯点着。她背着光坐,一双眼睛带着警惕地看着他,像一只受惊的兔子。光线下她人影朦胧,却又是实实在在的是在他面前。几日不在她清醒的时间里见面,此时看见她,他心里莫名产生了一种感觉。
一种在他的认知里的不可言状、不知名姓的感觉。
他大步走过去,把纸袋子随便丢在床上,想都没想,揽过她的腰低头便吻了下去。
柔软温热,是他渴望了多日的味道。
他把她的呜咽尽数吞没,猛烈冲撞中带着一丝不易发觉的温柔,他不再咬她,只是翻来覆去的吮吸缠绵。
没有了痛觉的警示,她被他搅动得连挣扎都忘了,同时心中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异样的情愫,这种情愫让她心慌。她的不知所措很快被他敏锐地捕捉,便越发辗转流连,掠夺逞凶。
他把她原本抵在胸膛的上手拿下来环在自己腰上,他皮肤的温度一下子烫得她下意识想收回,却被他的大手紧紧复住,动弹不得。
突然没了手臂力量的支持,她平衡不稳便向后仰去,他抱着她顺势也压到了床上。
光线氤氲,在墙壁上倒映出床上对影重叠的一双人。
男人的吻逐渐多了情欲的味道,感受到他下身的变化,她终于从失神中惊醒,没法推他便直接扭过了头,让他的吻落了空。
他一下亲在她的侧脸上,面对她的拒绝竟也没发怒,抱着她浑身发热的身子,故意贴到她胸前听,嘴角勾起一抹邪恶的笑,“式,你心跳得好快。”
她被他得话逗红了脸,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什嚒,“你...你别叫我名字。”
其实,男女之间做到这一步,后面的事情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他更是一个从来不知道忍的人,哪管女人愿不愿意,只顾自己舒服。如今却可以在她在身上一次又一次的停下来,不得不说,他自己都有点佩服自己。
他没放开她,又捉过她的脸亲了下去,只不过这次是浅酌,还不等她在抗议就已经离开了她的唇,不忘继续调戏她,“好甜。”
死流氓。
黎式把自己的手从他的腰间抽回来,再去推他,“你起来,重死了。”
乌鸦难得从善如流,坐起身来,伸手拿过一边已经被他们二人压扁的纸袋子丢给她,“呢个系你亚公在荷兰时,托我转畀你的。”
亚公?黎式也坐了起来,还不等她擡头问什嚒,那男人已经关了房门出去了。
...这人还真是随心所欲。
黎式打开纸袋,里面是一封信和一个黑盒,盒子里是一个银色的镯子。
——“我的式,亚公深感对你唔住!亚公这一生,早年作孽无数,晚年留唔得你阿妈,你小姨,你阿弟,而家仲畀你做出咁嘅牺牲,亚公生不如死。
这系老天对亚公嘅惩戒。
如果让阿公失去什嚒,可换你归家,亚公情愿而家就去死。
式,你一定要坚强。
这个镯子系我黎氏嘅传家物,叫做平安镯。假设,我们爷孙此生冇机会再相见,亚公只希望这个镯子能保佑你,好似亚公在你身护你,保你一世平安。
平安!平安!
千万珍重,珍重万千。”
她合上信纸,眼泪一滴两滴落下去,逐渐打湿被褥一片。
千言万语,万语千言,都化为声声珍重。亚公七十已近,半截入土。无非是只盼望一家和乐,喜乐安好。
无奈,人生多艰几何。
黎式小心翼翼拿出镯子,举在灯下看,银色的本体,内圈里刻了平安两个字。她面上泪痕打满,却依旧在忍住哭泣,这已经成了她的习惯。
镯子套进她纤细的手腕的那一刻,她终于忍不住,放声哭了出来。
——“平安”两个字正对着她孱弱皮肤下的青色脉搏。仿佛是亚公的大手牵着她的小手,陪着她,护着她走过人世间的荆棘丛生。
乌鸦拎着袋子从外面回来的时候,还没推开门,就听到了她的哭声。她的哭像一个孩子的呐喊,传达着一种纯粹的悲伤。
他稍稍推开了些门去看她。她抱着自己缩在床的一角,哭得不加收敛,哭得浑身战栗。
面对她不可敌的力量,她宁可拿一把剪刀自尽都不肯流露出脆弱,如今却在亲人的三言两语前就卸了刺甲。
忽然间,他好像明白了一件事情。他面前的这个女人,可以占有,可以欺压,可以凌辱,但是就是征服不了。除非她愿意,不然那双眼睛里,永远写满鄙夷。一种平静却致命的鄙夷。
她如月亮般平静,又如白兔般警觉,还如飞鸟般难控。
他总是想通过强迫她,想让她在自己面前流露出情绪,或喜或悲,都好。只是她太倔强太倔强,这种倔强里充满不甘,便更加激起他征服的欲望。
如今他看到了。她的哭声告诉他,她崩溃了,可却又满足了什嚒呢。
他不是没有见过女人哭,他自认为那是女人为了达到目的而虚伪矫饰的工具。但此时卧室里那撕心裂肺的声音在一下一下的撞击他的心,也在牵动他莫名的情绪。
男人快步走过去,一把把她扯进自己怀里,用力地抱着,仿佛要把她揉进身体里。怀中的女人起先愣了一下,反应过来后便开始挣扎,他死命抱着她,不肯放开一点点。
她挣扎不开,就凶狠地一口咬在他肩头。她的不愿、不甘、委屈,甚至想撕掉自己温柔的表面,向老天爷竖一根中指。所有负面情绪都化为气力,尽数咬在这一口上。
他一声不吭,承受她给的这一份痛。
铁锈味在嘴里蔓延开,她不喜欢他血液的味道,松了口。双眼无神地盯了一会儿某处,又开始挣扎大哭起来。
他抱着她,随她去哭,随她去闹,就是不松手。
世间繁华太多,人影交错擦肩而过。暮色具暗,如在荒芜中崩断神经末梢而吸食了麻醉,再不可收拾。既然她让他停下了脚步,那就不会轻易放开。
她在呜咽中对他说,“我恨你。”
他不怒反笑,双臂越发收紧,只想留住她所有温度,“那就恨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