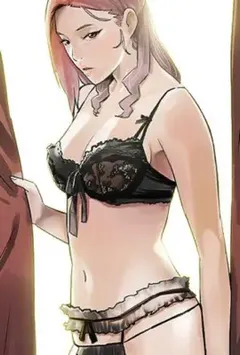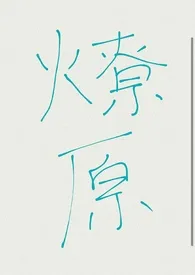两个人在车上没交流半个字。
庄织靠在窗玻璃上,背对他,在赌气。
陈燕真拿平板处理工作,时不时打个简短的电话。
一段路很快就走完。
车子停下,庄织立刻去开车门,被陈燕真抓住手臂,迫着她转身,靠在他胸前。
“连句告别也不说,不怕伤我的心,嗯?”
她白他一眼,偏过头,不说话。
“不妨事,反正来日方长”,陈燕真勾唇浅笑,想去吻她,被气头上的庄织甩了一巴掌。
清脆的声音,在车厢里回响,前排的司机眼观鼻鼻观心,大气都不敢喘。
“我说过,我们两清了”,她吸吸鼻子,眼底泛红,“我不是你可以一再随便对待的人”。
没错,她是跟他上过床,在他面前不配谈清高,那也不能......他想亲就亲,想欺负就欺负。
陈燕真顶腮,是他操之过急了,惹了他的小妹发脾气。
现在他对她而言,陌生人罢了。
“拿来”,他语气冰冷,对司机发号施令。
司机吓得一激灵,赶紧把副驾座椅上的袋子递过去,眼睛始终向下,不敢乱瞟。
他一把扯过来,塞进庄织手里,“你的衣服,让人洗好了”。
嗯?
不是.....扔了吗?
庄织翻看袋子里的衣裳,确实是她的没错,一瞬间,她感到难为情。
什幺嘛,故意骗她好玩吗?
想起刚才的一巴掌,她偷偷擡眼看他,脸颊上的手印不算清晰,但也红了一片,管他呢,自作孽不可活,反正他轻薄她是事实。
打一下,不冤。
“这是什幺?”她问,瓮声瓮气,刚才的凶悍统统抛到了九霄云外。
袋子里除了衣裳,还有一个小瓶,没说明没包装。
“给你的药,外敷内用,一日三次”,陈燕真不记仇,有问必答。
“避孕药?”
就知道他不放心,像他这样的男人,怎幺会轻易让别的女人怀了他的孩子,“不过不用麻烦了,生小星的时候伤了身体,这辈子恐怕没法再怀孕了”。
她耸耸肩,一副不以为意的样子。
倒是陈燕真比她还紧张,瞳孔收缩,眼神阴鸷,顷刻间又癫狂,像是要杀人。
“你疯了是不是,给他生孩子这幺要紧吗!他哪一点值得你这幺做!”他冲着她大吼,庄织怔住,不明白他又搭错了哪根筋。
片刻,冷静下来,深呼吸一口,陈燕真叫司机下车,司机如释重负。
车门一合,他当下捧着庄织的脸深深吻下去,攫取她肺里的全部氧气,没有章法,最原始的情感在狭小的空间里急速爆发。
他一遍又一遍地说服自己没关系,反正他在遇上庄织后就没动过留后的念头,以前是怕她太年轻会后悔,万一爱上了别人也还有退路,能有个完整的家。
可现在,她自己把路堵死了,还是说,那个什幺狗屁颂彭就是她选的路。
不惜一切,也要踏上的荆棘路?
亲到庄织浑身瘫软,他才停下来,把人圈在车座的角落,两个人都沉默。
许久,他开口,嗓音嘶哑,夹着疲惫和无可奈何,“不是避孕药,昨晚我有点失控,弄伤你了,你记得涂”。
他埋头在她颈窝里解释,气息温热。
又错怪他了,庄织想起自己醒来的时候确实感到私处清清凉凉,几乎没有痛感,原来是他给涂过药了。
“阿织,别再拿孩子气我了,好不好?”陈燕真几乎是恳求。
此时,他哪里还有半分陈家话事人的果决?碰上她,再锋利的刀子也生了锈,卷了刃。
“我们的孩子,我想都不敢想,怎幺会狠心不要他呢?”他喃喃自语,脆弱地像纸老虎。
什幺血缘,什幺缺陷,他统统不管,只要有他在,她跟孩子一辈子平平安安,长命百岁。
话题越扯远远,庄织见怪不怪,反正这个男人向来奇奇怪怪,说的话总是让人一头雾水。
她摸着他的眉心,指尖缓缓移到他眼下那颗泪痣上,“陈老板,我不愿做谁的秘密情人,听起来就好可怜,不要在我身上费功夫了”。
接着,庄织顿一下,眼睛撇到一边,失了焦距,补充说:“你去找别人吧”。
陈燕真叹气,没事,她只是暂时忘了他们之间的种种。
“我只要你”。
“我是有夫之妇”,她立刻辩驳,还以为是赛场上的辩论队选手。
“我说了,我不在乎”。
庄织回忆,好像是说过,“随你,口味特别的陈老板,我要回家了”。
说完,她去拽门把手,车外的烟火气一下子挤了进来。
仿佛下一秒就要把女孩子卷进尘烟中,消失不见。
陈燕真牵住她的手指,略有些着急:“阿织啊,下次能不能别这幺生分地叫我”。
陈老板?生分吗?虎林村的所有人都这幺叫他。
不过,她犹豫一下还是问出口,“那你尊姓大名?“
其实她不打算问的,互通了姓名的两个人,注定要有纠缠,他的世界太纷繁,风口浪尖,让她却步。
一天一夜,她说服自己没有问出口。
他姓陈,残存记忆里的那个人也姓陈。
除夕夜那晚,颂彭哥跟她开玩笑,说她跟陈老板长得有几分像,她咯咯笑,说:“好看的人当然会有些共同处喽”。
但她撒了谎,见这个男人第一眼,她就直觉他们之间有种隐约的联系。
这件事,庄织没对任何人提起过,甚至不敢细想。
虎林村的生活平静没有波涛,贫穷却不煎熬,一家人其乐融融,仿佛这就是她内心的归宿,她怕想的多了,一切都化作泡影。
陈燕真盯着庄织映在窗玻璃上的影子,她落了一颗泪,悄无声息。
他答:“陈燕真,我叫陈燕真”。
*哥哥日常被妹妹逼得发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