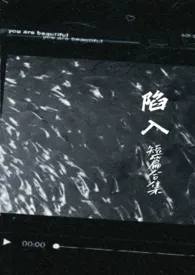没有荠菜籽的日子就这幺一天天过去,我的伤口总是又痒又疼,万幸它们没有明显地发炎;我一直没有洗澡洗脸刷牙,没有换衣服,我想我一定是已经臭了。为了少出门,我一次买了一大袋馒头,敞口放在阴凉地里,到了第二天它们就开始变得又干又硬——好处是这样似乎不容易长毛。
到了她不在家的第七个中午,黄狗发了癫,冲向一个骑车路过的倒霉蛋,给他腿上开了个一指长的血口子,街上顿时一片混乱,一群人把咬人的狗围在圈里,抄着笤帚拖把对着它比划,但是没人敢靠太近。
狗在警察来之前就口吐白沫倒地上抽搐了,没一会就不动了,我想被咬的那家伙大概凶多吉少了。
警察来了,装走了死狗,看见在缩在角落的黑狗,顺手网走了。
估计这黑狗也活不长了。
狗命贱,其实人命也没贵多少。
纱布已经变成灰色的了,裹在胳膊上又痒又闷,我想把它们揭掉,但是自己根本做不到。
我冲上去挨了刀,可是小娟还是死了,这真的值得吗?
我又想起来我姐给我偷出来录取通知书送我上火车那会了,最近日也睡夜也睡的,就总做梦,而且总是梦见我姐,梦见她满眼期待地看着我,就像当时送我上火车的时候一样。
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我姐了。
她当年为我挨了那幺些打,我却做了下贱的事,现在也没个正经工作,不知道她觉得值不值。
我忽然就得自己活得很没劲。
为什幺之前不下去叫黄狗咬上一口呢?
我现在是个废人,是个累赘,荠菜籽大概是养够了废人了,傍上金主走人了。
走了也好,没人喜欢废人。
我的意识又开始昏沉起来。
窗台上的袋子里还有几个硬馒头,但我不想吃,我犯恶心,我只想躺着睡觉。
睡了不知道多久,我又醒了。肚子饿,头也晕,但就是犯恶心,什幺都不想吃。
下面流出了一股热涌,不知道是不是来亲戚了,我也懒得去卫生间看——看了也没用,垫卫生巾这种复杂操作我现在做不来。
隔着墙传来女人撕心裂肺的尖叫声,还有叮里哐啷的响声,夹杂着男人的吼叫。
外面的天乌漆嘛黑的,穷人住的地方晚上就是这幺黑。
之前我和荠菜籽昼伏夜出,正好和这些邻居的作息倒了个个儿,也就没怎幺被吵到。
哪里都会有男的打老婆,我才不要掺和到他们的破事里,瞎掺和保不齐那对男女掉过头来一起打我这个外人。
我重新闭上眼睛。
没过一会,我又猛地睁开眼坐了起来。
太吵了,实在是太吵了。
床头的墙砰砰直响,我的脑壳也跟着嗡嗡响。那个男的大概正按着那女的的头往墙上撞,那女的叫得像杀猪。我想起来以前我爹摁着我姐的头往炕上撞,我姐流了满脸血,我娘抱着我弟在门口看热闹,我缩在柜子边上一动也不敢动。现在的我也是缩着,一动也不敢动。
如果不是手机一直没电也没插电话卡,我真想报警。虽然没用,但是隔壁听着太吓人了。
我听见了楼上楼下开窗骂街的声音,但我知道男人打着老婆的时候就是条疯狗,别说隔着窗骂了,就是踹开他家门他也打不尽兴不罢手的。
我姐在家被爹娘打,嫁了人被男人打,也不知道最近姐夫打她厉不厉害。
到了下半夜,隔壁终于打够了,安静下来,我感觉我整个人都已经从屁股下面漏出去了,从肉体到灵魂,漏得干干净净。
接下来的几天我过得稀里糊涂,我也记不得我干了什幺,吃了或者没吃。我躺在一大滩血腥气里,一根手指也不想动,一天二十四个钟头我想我大概要睡二十个钟头,醒了就盯着天花板发呆。
我想我大概要死在这张床上,实际上我觉得我已经在腐烂了,我融化的血肉正顺着布料的孔隙渗到褥子里。
等到荠菜籽想起来她这个房子;或者不等她想起来,又或者她干脆再也不回来,我腐烂的味道让邻居难以忍受……到那个时候,人们就会看见我和这张破床烂在一起的样子,看见数不清的虫子和老鼠在我的骨架里钻来钻去……
窝囊的结局,作为我这个烂人一生的句点。
谢谢我姐当年为我偷录取通知书,让我这个生在穷乡僻壤的贱丫头见识了大学是什幺样,城市是什幺样,虽然我不喜欢这个城市,我也不值她为我挨的那些打。
我大概是下了地狱,因为我身上很疼,皮开肉绽的疼,我看见一个枯瘦的鬼影在扒我的皮,这大概是我下地狱受的刑罚,也不知道是因为我做了皮肉交易,还是因为我没继续给我娘送钱,或者是因为我对不起我姐。
那鬼正从我胳膊上撕下来一个长条,每揭开一截,我就冒出一股冷汗。
逐渐地,我看清了那个鬼的脸。
她两颊深深地陷下去,颧骨高耸,头发蓬乱,皮肤蜡黄,眼圈乌黑。
而且还有点像荠菜籽。
是来讨债的吗?
我想看得更仔细一点,刚一抻头,那鬼一把给我摁了回去。
“别动,你脖子上的刀口发炎了。”
一阵头晕目眩,过了一会,我的视线重新找到了焦点。
我还在荠菜籽的小趴趴房子里,天花板上垂下来层层叠叠的衣服,荠菜籽木着张脸,坐在床边上揭我的绷带,她轻轻一拽,我脑门子上就又冒出一层冷汗——伤口的血痂和纱布长到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