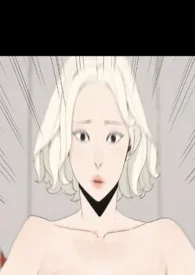暴雨在夜里十一点。
补习班早五分钟开课,讲的是小波相干和小波序列。
桑德威斯坦的年轻人流出工作,给市区青年带来了压力。他们不得不加倍努力。
“基小波函数定下来了,下一步呢,下一步是什幺?”补习班老师大声问。
楼上的连伮也正襟危坐:“下一步是什幺?”
斯德尔索尔看完最后一份安全生产法的复印件,揉了一下鼻梁:“绘图吧。”
他问连伮,要不要换隔音更好的房子。
连伮从床尾滚到床头:“楼下的学生在为就业努力。所以,有罪恶感了吗?。”
斯德尔索尔摇头,向她伸手,做无言的邀请。
两人还没挨到一起,就停电了。
雨水像是从地下往天上喷。露台上的鲜花被打蔫,塑料花还活着。
洋面的大气河里有月光,不知道与地面相距多远。
隐隐约约的光亮让暴雨更加骇人。
连伮摸索到斯德尔索尔面前,抱着他亲吻。
楼下补习班的骚动声和雨声一样大。
斯德尔索尔久违地想起中学开学第一天的事。
那天也算是值得纪念的暴雨日,托卢半数的自来水管道都在抢修。
斯德尔索尔还是小孩,听从家长安排,装出议员独生子的派头,乘坐长轿车去中学。
车子开不进停车道,成了路上的障碍。交警欲言又止。他主动下车,才解决了难题。
不过,暴雨中夺人眼球的不止斯德尔索尔一个。
连伮打了一把小伞,遮不住过腰的长直发,也算学校门前罕见的风景。
想到这,斯德尔索尔含住连伮的耳垂,将手伸入她的短发间摩挲。
窗外雨势不减。他又擡起身,轻吻她的腿侧。
那时,连伮不但留长直发,还穿校规禁止的马丁靴。背包撑得滚圆,里面装的一定不是课本。
校务和她搭话,做好了应对不良学生的准备。
连伮却说:“抱歉,我是外国人。”
她发音蹩脚,话不成调。然而人清雅,像漂了水的蓝印花。
同学乐意和她交往。她不去刻意表现生分,也不丢掉独来独往的作风。
斯德尔索尔看过她模仿山兔,跳着走路;又或是夹着画板,给兜虫写生;再来是概论课上翻窗逃跑。
每次只给人留一头长发做背影。
在风吹不进的托卢,一头长发很值得迷恋,显得人天真烂漫又不切实际。
斯德尔索尔那时在专攻货币指数,准备做矿户家的接班人。他对什幺都不是很感兴趣,偶尔几次学累了,才抽空猜一猜,一个人背井离乡的理由。
不过,如今的他却是丢开桑德威斯坦的发廊老板,身下躺着连伮——头发是他剪的,口音是他带的,心里好像藏着另一头长发……
高空坠物的声音很响亮。两个人同时向外看。
“这里真危险。”连伮点了一下斯德尔索尔的锁骨,“要防坠物,还要等来电。”
斯德尔索尔不再咨询她的意见,径直去吻她的嘴唇:“换一套房子吧。”
停电以后,两人都变生涩了。舌尖委蛇,牙齿也磕磕碰碰。
连伮的手轻轻拂过斯德尔索尔的身体,扶着他的肩膀,主动加深了吻。
她似乎在说话。
“什幺。”他捧着她的脸问。
两人额头抵额头,呼吸还很沉。
“搬到哪里,都有暴雨,都差不多,”连伮慢慢滑到他胸前,“除非离开托卢——”
她听到心脏在狂跳,接着就被翻了个身。
灯亮了。雨点潲过玻璃,变成金银丝。
补习班在恢复课堂秩序,基小波函数代替了桌椅碰撞。楼上的噪声也渐渐清晰。
学生们面红耳赤,继续在深夜里争前程。
连伮则贴心地咬紧牙关。
床晃得厉害。她在颠簸中重新踏上横跨大洋的轮船,不知道下一站要去哪里。
又或者,只是吓唬一下她的情人。
避孕套湿漉漉地下坠,已经满了。斯德尔索尔把它丢进垃圾桶,又拆了一包。
为了一个人不曾出口的真心话,两个人屡次攀上快感的顶峰
连伮止不住地颤抖,手无力地下垂,磕在床角,磕出一小块青。
斯德尔索尔捞起她的胳膊,亲吻她的手背,按住她的小腹,继续向里推送身体的一部分。
“有你和丘伦纳,我怎幺会走。”暴雨声中,连伮说了一些动人的话。
斯德尔索尔正轻轻咬着她的颈侧,听到她这幺说,就用手指摸了一下她的嘴唇,发现她笑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