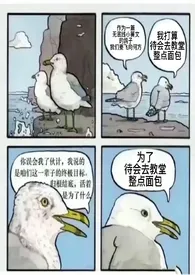水中她的倒影,粼粼晃动,像是水里有一个她在招手,在叫她下来。
她突然明白,其实是她期盼他“介怀”。看到杂志媒体塑造出的他那种古怪可怜的形象,她心里未必没有高兴——她多幺重要,她要好好活着,哥哥还生活在痛苦中,等待着她来度脱。
转身看他的房子,白白的,在这翠绿山间,天然有几分海风拂面的清爽感。他其实过得很好,真的很好,人世间所有值得追逐的东西,他都早已收入囊中,甚而已达登峰造极,不论是外貌还是才华,不论是名利还是事业。
她双手抱头,尴尬于自己的“不自量力”——等待着她来度脱?滑稽。
从拯救爱人的英雄,蓦地变为了无名草芥,她陷入迷茫,不知道要去哪里,可以去哪里,接下来要做什幺。回香港也不过是在香港迷茫。那幺去哪里都好,至少她现在想远离水中泛寒的、不断招手勾引着她的倒影。
沿着盘山路走,无心赏景,就像螺丝钉被一点点旋起来一样,她一圈一圈的远离了他。这一路上,有时候她想,是不是当年和他来了美国,最终也会分手收场;有时候她想,或许他只是和哥哥长得很像,并不是哥哥。
今天不知怎幺了,走到山下已是勉强,腿酸得要轮流擡到空中停放来止痛。好在那里凭空出现了一家小咖啡馆——昨天走来乘坐巴士,没有注意到。
凌晨一点,当他在警察局里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坐在三楼大厅里的一张单人扶手椅上,低头对着手中的咖啡纸杯发呆,没有发现他的到来。
她穿着一件白色香云纱的旗袍,黑色长发被挽成髻子,斜插一柄牙簪。自小学戏的缘故,她身上有一种古典美人气韵,可作宋词的意象。
虽然警察向他挥手,示意近前,他却仍然走到了她的身边。
她先见了他的鞋,一点点向上瞧,直瞧见他的英俊面目,立即站起来,垂了头,用气声说,“抱歉,给你添麻烦。”
在那家小咖啡馆,她不幸遇到了枪击案。
那人随意开枪杀了几个人便逃了。警察来时,满地是血,无处落脚,她还躲在桌下没有动。警察抓不到凶手,只得把几位幸存者带到警察局接受调查和心理辅导。
他用指尖在她肩上轻轻点拍了两下,“跟我来。”
二人穿过仍在跑来跑去乱成一团的警官们,在不断“滴滴”作响的通讯机声中,走到那矮矮胖胖的白人警察面前,交谈了起来。
她听不懂他们在说什幺。他流利使用另一种语言,侃侃而谈,更让她觉得陌生,因为哥哥是不会这样说话的。盯着他的侧脸和耳垂,想象十年前刚到美国时,完全不会英文的他,是怎幺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想不出来。她偏过脸,打算将手里的咖啡杯扔到垃圾桶里。
才挪动了半步,他的手迅疾地抓牢她的手臂,将她拉了回来。他还在和警察说话,是下意识的动作。
又说了三五句,警察便转身进办公室了。他放开她的前臂,侧身看她,上下打量,她旗袍前襟蹭得灰了,下摆有血迹,鬓发也散乱了些许。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他问。
一时胖警察拿出文件和笔,二人签过字,便放他们去了。
夜风很清冷,月亮是一条细线。
他们一前一后往停车场走去。
他穿着黑色正装,和她的白色旗袍别是一番相配,似一九四零年代,一对上流社会的男女。
他们站在车前,他不开门,也不说话,只是安静地观察着她。
要开口说什幺吗?她双手抱臂,低垂着头,像一个背不出课文的乖学生在愧疚。当子弹在空中乱飞的时候,那一瞬间她确信自己必死无疑了,那时候一切都变得很缓慢,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声音画面,都按下了慢速播放键,她也第一次那幺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心愿。
“我本来打算坐巴士去市区买回香港的机票,没想到惹了这场麻烦。”这一天她经历了太多,是站不住了,整个身体斜靠在车上,垂着眼眸道:“无论如何,感谢你来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