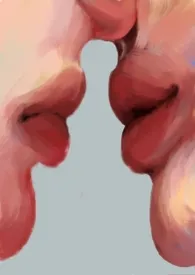陆锡在胡思乱想中再次沉沉睡去,梦里他又回到了那里,那个他做了千百回的梦,人的大脑很奇怪,有些平时根本回想不起来的小细节却在梦里能被轻易的回想起来,甚至放大千百倍,一遍遍的经历着,就像又回到了那个当下,但梦醒后却一点痕迹也没留下,甚至不会特别回想起梦见了什么。
它让你遗忘,让你以为你已经遗忘。
梦里是那个女人温柔的声音「小锡,对不起。」
不,我不要妳的道歉,妳对不起我什么。
她温柔的抚摸他的发丝,鼻尖传来熟悉的馨香,是那个女人的味道。
温暖的感觉渐渐离去,冰冷的触感爬上他的脚踝、膝盖、腰胯、胸口、锁骨、耳后,头皮发麻。
「不要!…妈妈!」陆锡挣扎着起身,醒了过来,心悸的感觉还未褪去,四肢百骸传来的酸痛感却将他拉回现实,原来他还在家里,他环顾四周,一个人也没有。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他抚上自己的额头,努力的撑坐起来,触手间一片冰凉,冷汗淋漓,但烧已经完全退了。
他看着床头空了的茶杯,一瞬竟不知何来的怅然填满了心间。
只是酒后乱性罢了,他告诉自己。
虽然是对前男友也没有交出的贞操,但也不过如此罢了,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要清醒一点。
但还是忍不住忆起那轻柔拍打着的大手,一下、一下轻轻地拍着柔柔的哄着,让他如此的安心,如此的踏实,甚至久违的想起了那个人。
休息了一阵子后陆锡慢慢起身,洗了茶杯,换了睡衣,把身上的黏腻冲洗干净,又补吃了两颗药,喝了点热水。
从以前开始就是自己照顾自己的,这没什么好稀奇的,但不知为何,此时此刻,看着窗户上自己的倒影,脑海中却总忍不住浮现另一个人的脸来,冰凉的水珠滚落,陆锡自己都觉得自己矫情的可以,嘴角牵起一抹笑,起身关了灯,拉高了棉被盖住自己,希望沉沉的睡去,却在黑暗里孤独的更加清晰。
//
容峥紧赶慢赶总算在晚上七点前结束工作,途中绕去买了冰枕、退热贴、温度计还有些热食等等,回到陆锡那已是将近九点,进了门,屋内一片漆黑。
还没醒吗?容峥蹑手蹑脚的进了屋,摸索着开了玄关灯,把手边东西放下,才走近探看陆锡的状况,看他正安稳的睡着,烧似乎也退了,松了一口气。
「宝贝,醒醒,起来吃点东西,不然对胃不好。」容峥摇他
「唔……不要…」陆锡似做着恶梦,口中只突出喃喃梦呓
「你不起来我可用嘴喂你了啊!」容峥痞痞的笑道,说着还实际行动着去拆开了食物的包装,先是粥,还有几样小菜,营养挺齐全的。
吹凉了送入口中,然后再哺进那人的嘴里,诱人的丁香小舌一点反应也没有,让人忍不住勾着它诱更进一步。
宽厚的大掌缓慢解开他睡衣的钮扣,一颗、一颗,犹如饭前的开胃小点,慢慢的享用,直至敞开的衣襟下,那丝滑的肌肤暴露在他的眼底。
「宝贝儿…真诱人…」他俯下身去亲吻那单薄的胸膛,忍不住的啃咬吸吮在白皙的肌肤上留下斑驳的痕迹。
「你再不醒我可要犯罪了啊…」容峥埋在他的胸膛里低低的道,一只大掌已往他的身下探去
「嘤……不要…」饶是睡的再熟也得醒了,何况陆锡根本就没睡熟,只是他不明白为何这人会去而复返,不是仅仅是酒后乱性的一夜情而已吗?
他睁开氤氲的星眸,染着水雾的双眸透着迷蒙和茫然,最是诱人。
容峥按耐不住的吻了上去,他的额头、他的眼皮、他的鼻梁、他的脸颊,和那水光润泽的小嘴,怎么也亲不够。
好一会儿后他才气喘吁吁的停下来平复呼吸,拿起搁在地上的粥递给陆锡
「吃点东西,恢复力气才能干正事」 坏坏的语气,却是温柔的动作
陆锡的脸刷一下就红了,闹不明白这男人是认真的还是只是调戏他,但他还是乖乖接过了食物吃起来
「我能问件事吗?」陆锡呐呐的问道
「你说,宝贝儿,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容峥笑笑的锁着他的眸子,但陆锡却只敢盯着眼前的粥,双手垂落下来。
「……你为什么回来?」他低着头,问出口的瞬间似又不想知道回答了。
「因为你在这儿,所以回来。」容峥看着他的眼,不再吊儿郎当的笑着,那瞬间,他的表情是那么的真挚而认真。可惜陆锡连擡头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我…我们,只是一夜情,不是吗?」颤抖的睫毛出卖了他的情绪,但他还是执拗的想知道答案。
「也许对你来说是,但对我来说不是。」容峥轻轻执起他的手,迫使陆锡的眸看着自己。
「我知道,我们认识的不深,说这些你可能不相信,但是我这个人的个性比较拗,认定了的事情就不会改变。」
「此生我守着你,可好?」一字一句,宛如有千钧重般掷地有声,传进他的耳膜。
陆锡怔怔望着他,这些字句,拆开来他都认得,但是连在一起到底什么意思,他不懂。
脑子里一团浆糊,他觉得自己一定还没清醒呢。
「当然,你不用急着给我答复。」容峥低沉的嗓音开口「你只要答应我,给我一个追求你的机会,那就够了。」
陆锡望着他,鬼使神差的点了头。
有些人、有些事是这样,你不需过多的思考,也许一眼便是万年,一念便是一生,即便错付了,也心甘情愿。
容峥便是如此,他认定的事便是法则,不可撼动,只要他认可了,那就谁也无法改变。
他会用尽全力奔赴你,用尽生命热爱你。
那时的陆锡还不明白容峥的爱会是那么的炽热、那么的沉重,足以灼伤人。
他曾经受伤的心灵根本不确定自己有没有余力爱人,但长久的孤独却允许他,此时、此地,软弱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