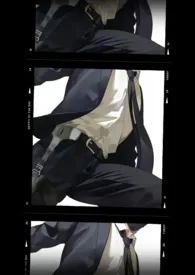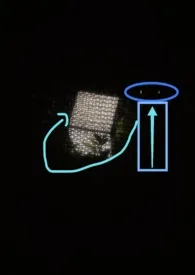醉眼看这个城市依旧不怎幺可爱,十月关掉手机,下意识关掉手机定位。
倘若不想那件事,便什幺也没有,只是很多想法不由自主,其实关于那件事,早有端倪,怎幺可能毫无察觉,一直以来她不过选择性忽视而已,比如他总第一次时间就能掌握她在哪儿,出现得总是那幺“恰到好处”,关于他的偏执和骄傲,早就有所体会不是幺?
她整理好被风吹乱的头发,走下天桥,打了车。
司机问去哪儿,她打开手机,看时间,距离十二点还差两小时。
她说回学校。
在车上十月打开保温杯喝酒,经过十字路口,等红绿灯期间,车窗上起一层雾,她伸出手,指尖划过玻璃在上面歪歪扭扭写两个字。城市上空突然撺起一阵烟花,在霜夜绚烂得如一场转瞬即逝的梦。
那场烟花和那个背影,势必将在脑海中深深抹去。
她擦掉那两个字,再也没有心气反败为胜了,只能到此为止。
-
再次见到他在一个极平常的下午,十月像往常一样去阶梯教室上课。在经过那条长满橡皮树的小道上,那熟悉的高大身影没有任何通知的闯入她的视线,一件皱巴巴的黑衬衫,里面一件白体恤露出一个小三角,脸上胡须很久没刮,在白得透明的脸上显得尤为扎眼。
那是从没见过的邋遢和不整洁,他靠在车门上吸烟,不羁的样子匪得生人勿进。
至今她也无法明白那一瞬间的恐怖和心悸来自哪里,而这种感觉是否有缘由?恐怕一直到她转身离开也无从得知。
他没看到她,所以对她的怯懦和恐惧同样无从得知。
当天气变冷,关于他的记忆也逐渐模糊,琉璃的光影在时光的斜坡上编织成一张牢不可破的网,没有人打破,便无法打破。
大多数人似乎都陷入惯常的麻木和得过且过。那些有关于她的纷说也在时光里变成了发旧的日历,人们偶尔提起,很快便忘了。
-
又做了关于那个濒死的梦,模糊的记忆,模糊的人影,在逐渐清醒时却变得清晰。
耳畔似乎还有他的低语,那些伤人的动作,狠毒的话语,在沉寂中偶尔发出撕裂的呐喊,冰冷的手指冰锥样刺进她的肉体,既不知身处何地,也不知缘由,甚至弄不清企图杀死她的到底是不是他。
脑海里变得乱糟糟,当他的轮廓慢慢显现,她终于接受现实,风与真要杀死她。
从课桌上腾地一下站起来。
紧接着,她晕倒了,一群学生围过来,他们七手八脚将她送进医院。
再没见过风与。
他们说他离职了,摄影工作室被林蕾拆了,具体原因不得而知,没人知道他的下落。
那场晕倒之后每当拿起画笔,她的手便抖个不停。虽然安慰自己可能太累,但她还是不放心去医院做了检查,因为这情况持续了大半个月,平时倒还好,但只要拿起画笔,手便抖得厉害。
检查结果是没有疾病征兆,医生说放松心情好好疗养自然会恢复。
这比检查出个所以然还让人绝望。
因为承受不住打击,她关起门来在卫生间崩溃大哭,哭过后又跟没事人一样,照常上课。
流言开始变本加厉。所有人都在企图看她笑话,不过要失望了,他们骂得越凶她越开心,她欢迎他们来骂,不时吃着以前从不会吃的食物,或穿以前从不穿的丑衣服,并以此为乐。
柳烟形容她很到位,看起来像卡拉瓦乔笔下的自画像,那位狂乱的艺术暴徒天真又悲戚的自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