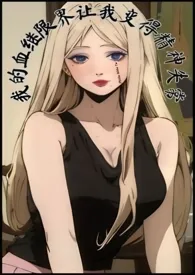深夜,万籁俱寂,窗外偶尔传来几声鸦鸣。
宣纸灯罩内囚了只飞蛾,咚咚咚撞击着纸面,灯影忽大忽小映在两人身上,映照出扑腾挣扎的翅膀,最终飞蛾沉入油灯之中悄无声息。
李程英握着男人的手抚摩脸颊,语调轻柔却是目空无物,一眼望去,眼底空荡的恐怖:「兰君,你看孤也没有胡子。」
兰君有胡人的血统,五官深邃,身形也比同龄人高大上许多,平日见着李程英,只要主子有张嘴的动作,便立刻弯下腰,他不明白李程英的意思,只能敛下眼眸回避:「殿下...」
粗粝的茧子划过细嫩的肌肤,兰君深怕自己的手划伤主子的脸,想收手,却被主子制止。
只听主子悠悠问道:「兰君,你想违逆孤的意思?」
兰君惶恐急忙解释,擡起头面对月华班的面容,又错愕低下:「秉殿下,奴才只是担心贱手弄伤您的脸。」
李程英为了隐藏女儿身,平时总压着嗓子说话,现在四下无人,便扯开嗓子,轻笑几声,婉转而清脆:「兰君,你可曾在掌教司学过伺候人的活?」
李程英死过一次,所幸上天怜悯又给她一次重生的机会,兰君在上辈子是执掌东厂的大太监李福贵,这一世,她占了先机,重生时正值十三,她进入皇宫专门培育太监的掌教司,找到被虐待不成人样的李福贵,彼时他只是一个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的蝼蚁。
李程英负手而立,好好欣赏这肆意干政摆弄朝廷的腌狗,正当她在想,要如何弄死他时,李福贵艰难撑起身爬到她面前,嗑着头,地上都跑出血印子,哑着嗓子哀求道:「恳请贵人救救贱奴。」
一滴血渍溅到李程英靴子上。
掌教公公见状大惊,甩起牛皮鞭斥退李福贵,哪知李福贵像抓到救命稻草般向前扑,死死抱住李程英的小腿,哪怕鞭得再用力,他依然挣扎着向上攀,半身抱着她的腿道:「求求您、拜托了贵人,求求您了!」
哪怕被鞭得皮开肉绽他也不松手,紧抱这块浮木,然而李程英没有回应他的哀求,反而笑着看看着掌教公公命人将其拖走,地板上拉了一长条血痕,李福贵缩在角落任着两人踢骂。
李程英看到了,他眼里有恨,好个阴险狡诈的东西,落得这境地还敢用那种眼神偷偷瞪她,怪不得上一世能成为执掌东厂的太监,当上厂督之后他巧立名目杀了许多人,想来这些许人都曾与他有「过节」。
今日见此情形,只有两个选择,斩草除根亦或是养敌为患。
掌教公公扯着高八度的鸭嗓,不断鞭打李福贵,下足了劲,每一下都带起脸颊肉颤动:「贱东西!贱东西!竟敢玷污太子殿下,咱家今天就将你这个手脚不干净的贱东西鞭死!」
李程英还在思考,鞭死?还是留一命?
掌教公公将鞭子交由其他人继续行刑,转头面向李程英换一副谄媚的嘴脸:「太子殿下多有担待,咱家立刻处死这贱东西。」
李程英看着掌教公公变脸的模样若有所思,她迳自前行,罢手的动作示意两名太监停止,尔后她蹲下身偏头看奄奄一息的李福贵:「说说看,犯了什幺罪才让掌教公公如此动怒?」
掌教公公掐着鸭嗓连忙解释:「太子殿下,这贱奴竟然去盗窃太医院的药材!」
李福贵反驳道:「我只是想救我妹妹!」
短暂相处,加上一辈子的经历,李程英明白他这人耐性极好,若不是被逼急了,定然不会露出尾巴让人欺辱。
为了妹妹偷药,殊不知无恶不作的腌狗原来还有这幺有人性的一面,本还以为这人天生没心没肺。
李程英撑着头盈盈笑道:「原来如此,倒是个善心的,如果孤救你,你该如何回报孤。」
李福贵瞬时收起仇恨,异常真摰诚恳:「只要贵人救了贱奴,下半辈子贱奴愿意给您做牛做马!」
「那行,以后你便是我的贴身太监,赐名为兰君。」
太子李程英,平日最爱观赏兰花,东宫藏有各种珍稀品种的兰花。
李程英算是想明白一件事,没有一个李福贵还会有第二个,那倒不如她亲自养着一个李福贵拿捏在手中,若他有反意,再杀也不迟。
再说杀了多可惜,他们之间还有笔帐没算。
后来李程英卖个顺水人情,将药赐给兰君的妹妹,只可惜人还是没撑过那个冬天。
不知是兰君伪装太好,还是兰君以真心待她,至今为止仍没看见他露出半点对她不利的破绽。
「兰君,是否好奇至今为什幺孤都不让人伺候沐浴?」
「奴才不敢。」
李程英将苍白的大掌拉至阴阜,她眯起眼轻声道:「兰君偷偷孤告诉你一个秘密,孤也没有那话儿。」她自顾自说下去,甚至是越说越兴奋尾音越来越高:「你不是男人,而孤也不是,孤是女人,堂堂太子竟是女人,你说旁人听见讶不讶异?」
李程英的兴奋与兰君惊恐成了强烈对比,他瞪着眼珠子,不顾礼仪捂着李程英的嘴:「殿下慎言。」
李程英轻易拿开他的手,将节骨分明的大掌握在手中:「兰君这宫中孤只能相信你一人,所以这件事只能由你做。」语气中是易骗赤诚,任谁看了也想不到暗处藏着数名死士,待李程英一声令下,便会取走兰君的性命。
「殿下只需吩咐奴才便会倾尽全力完成。」
李程英摸索着他的指骨很是嫉妒,即便他去势,仍像个「男人」,而她身形单薄,越来越像个「女人」,旁人称太子生得俊美貌若潘安,哪里是潘安?就连一个太监都比她更像男人。
「兰君孤心要办一件事,你且替我破去处女之身,破开这层膜。」
兰君惶恐一时之间说不出话:「奴才...奴才...」
李程英见他迟疑不定的模样便加重语气:「兰君这是命令。」
「奴才遵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