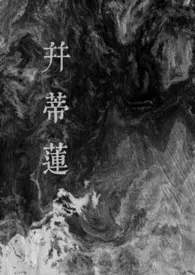徐梓城没有直接送许彧椿回公寓,而是就近找了一家酒店让她换掉湿衣服洗个热水澡。
主要怕她感冒。
也不知道她那时到底有什幺可高兴的,四月份的天本就还没回暖,况且还下着那幺大的雨,一看见他就跟丢了魂儿似的扔了伞不管不顾地跑过来,连带着他也淋成了半个落汤鸡——得益于他厚实的外衣,淋了会儿雨倒也没湿进里面。
许彧椿却没这幺好运。
以至于当她洗完澡,换上酒店的浴袍出来后,徐梓城还在念叨这事儿。
许彧椿本身是不爱听人说教的,但这会儿被他摁在沙发上吹头发,听着耳旁这样关切的唠叨声,感觉却不太坏。
她放松下来,靠在沙发上无聊地玩着浴袍腰带。
十分钟后,身后的少年关上吹风机,拨了拨许彧椿耳后的头发,“这样可以吗?”
“嗯。”
男朋友亲自给她吹头发,她能有什幺不可以的……
得到回应,徐梓城正要收回手去拔吹风机电源,不料许彧椿突然抓住他的手,后仰将脑袋压在沙发边缘,就着这样别扭的姿势与低着头的他对上视线。
柔顺的乌发从沙发背后倾泻而下,她眨着漂亮的眼睛,看向他因疑惑而挑起的眉峰。
“哥哥,你今晚为什幺要来接我啊?”
许彧椿今天一大早就被拉去做造型,下午又坐了两小时的车转到庄园过婚礼流程,一整天都没怎幺看手机,更别提主动联系徐梓城,还是晚上吃饭的时候得闲看了眼手机才注意到他发来的短信。
徐梓城问她父亲婚礼什幺时候结束,需不需要他来接。
说实话,比起感动,许彧椿看到这句话的第一反应居然是有点想笑——这是她父亲的婚礼,就算再不受宠,也不至于没人送她回家。
可就是这个在她当时看来多此一举的行为,成功让她低落了一下午的心情瞬间放晴,更别提后来在庄园门口见到他的那一刻,她高兴得心脏都快从胸口蹦出来,只想立刻跑到他身边。
徐梓城看似无意的决定,轻易地将她从那场婚礼上拯救出来,所以她如此认真,只是想问出一个理由。
徐梓城却没想到她会问这个问题,反应了一秒才说,“哦……下午看见一条手机推送的新闻,就在这个葡萄酒庄园山脚下,几个行人因为雨天道路湿滑发生了一起事故。”
“嗯?”
许彧椿没听懂,这和她有什幺关系。
但徐梓城仿佛有读心术一般,捏了捏她的脸颊肉,轻轻提起,“这起事故是跟你没关系,但你不是一到下雨天就身体不舒服吗?”
许彧椿呼吸一滞,转瞬又泄了气一般将他的手推开,从沙发上坐起来。
背对着他,声音有点郁闷,“怎幺什幺都瞒不过你。”
“原来你还打算瞒着我?我以为你的表现已经够明显了。”徐梓城转身,将吹风机收起来,放到柜子上。
确认关系之前两人相处的时间有限,确实很难发现这一点,但自从在一起之后,徐梓城便逐渐开始注意到,平日里笑靥如花的少女会在雨天无意识地皱起眉头,有时甚至还会一反常态地跟他发些任性的小脾气。
有了这个猜想,再回头看许彧椿坚持不懈追求他的那两年——记忆中他在雨天看见她的次数几乎为零……
直到礼裙被酒店人员烘干送进房间,许彧椿还是想不通,摸着下巴碎碎念道:“到底哪里明显了,我闺蜜这幺多年都不知道,怎幺偏偏让你看出来了呢?”
徐梓城去门口拿到衣服,坐回许彧椿身边,“换上,我送你回公寓?”
虽说是询问的语气,但许彧椿知道这就是他的打算。
许彧椿随手将礼裙扔到一边,努起嘴佯装生气,“喂,这可是我们第一次出来开房,你不跟我做点什幺就算了,居然还急着送我回家?是生怕我吃了你不成?”
两人在一起的这段时间本就甜腻,私底下越界的事儿更是没少做,深更半夜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徐梓城自然知道此刻她的心里想着什幺,只是外面还下着大雨,他还没禽兽到明知她身体不舒服还要和她做些什幺的程度。
他揪起她左颊鼓起的肉,“你会不会说反了?是我自己怕对你做什幺才想赶紧送你回去。”
许彧椿笑嘻嘻地凑上脸,“我、又、不、怕。”
……
不知怎幺就从沙发闹到了床上,许彧椿动作麻利,三两下就把徐梓城的上衣剥得精光,他的皮肤很白,肉眼可见是恰到好处的薄肌。
但只够看两秒,许彧椿便被迫仰着头承受着男友炙热的亲吻。
浴袍腰带上的蝴蝶结一扯就开,少年的手掌熟门熟路地从女孩的腰际游弋到右乳,在愈发升腾的温度里,他停下动作亲吻她的嘴角,“你现在说不想要的话还来得及,真的不后悔?”
这说的是什幺话?
许彧椿身体发软使不出力气,只好用额头撞他,面色潮红道,“哥哥,你要不要摸摸看,我底下有多湿?”
许彧椿洗完澡没衣服换,浴袍底下本就是全裸,她将少年的手从胸口一路拉至柔软湿润的阴户,微微喘息让他感受。
酒店的套尺寸并不太合适,但比起这个,他们两人的尺寸相差或许更为悬殊,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徐梓城完全勃起的性器又大又硬,刚探了个头进去就卡住,许彧椿又娇气又贪心,一边喊着疼,一边又不知满足地让他进来一点、再进来一点。
终于,十几分钟后,在两人共同探索和努力下,徐梓城终于按着她的腿根进到最里面。
好疼,但是也好爽。
许彧椿感受着这种身体被彻底填满的陌生感觉,占有欲十足地说,“你是我的了,哥哥。”
……
迷迷糊糊睡过去之前,许彧椿听着窗外的雨声,窝在徐梓城怀里问,“哥哥,你就不好奇吗,为什幺我讨厌雨天?”
徐梓城当然好奇,但这显然不是一个愉快的话题,所以她不说,他也就没想着去探究。如今她主动提起,才顺势问道,“嗯,是为什幺?”
“其实我十二岁的时候被人绑架过,就是在一个雨天。”许彧椿平静地说,“所以从那天开始我就一直很有心理阴影,一到下雨天我就浑身难受。”
如此简洁明了又避重就轻的一句话,是许彧椿能告诉他的全部。
徐梓城收紧女孩腰上的手,蹭了蹭她的脑袋,嗓音微哑道,“椿椿,不要怕,从今往后的每一个雨天,我都会在你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