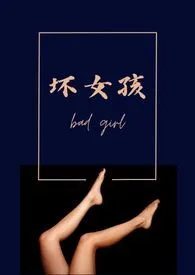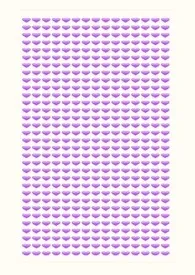母亲一向染成栗黑色、每一个弧度都打理得一丝不苟的发丝,如今发根泛白,干燥又杂乱,被她高高盘起,只有额鬓边缘偶尔散落几丝无暇顾及的白发。
她的皱纹,比往日更深,更低垂。她坐在病床边,死死地盯着病床上那个人。我以为她会悲伤,会愤怒,会充满不甘不屈,甚至谴责我为何成为千万安全的人里面唯独的受害者。然而,我却只在她眼里看到平静,她就那样静静地看着床上躺着的我的身体——被悲哀侵蚀得憔悴的面庞上,悲哀已经离去了,她的嘴角带着一丝微笑,像是刚刚把我哄睡那样,抚摸着我的手臂,注视我伤痕累累的睡颜。
而床上躺着的那个人,头顶的纱布已经拿下,露出新生的黑色短发茬,参差不齐——伤疤周围是秃的,像是干旱的草原凭空多出来的一片荒地,黑色的缝线周遭还有碘伏的黄,一路蔓延到额头。褪去的淤青也是黄色的,白皙到黄不清晰的过渡里,掺杂了几丝尚未褪去的紫黑。那是我的面庞,是我无数次在镜中看过的脸,如今静静躺在床上,插着鼻饲管,双目紧闭,像是死人一样寂静无声。
我紧紧咬着嘴唇,强忍着不发出声响。
“阿姨,我来看看诗苑。”刘雯的声音像是唤醒了我母亲。她擡起头,看到我们,脸上绽放出一个似乎惊喜的笑容,起身迎接我们:“欢迎欢迎。快过来,跟诗苑说几句话。”
她起身后,我才注意到,她居然穿着一双平底的运动鞋,与她的西装格格不入——是为了不要敲响这静谧的病房的地砖吗?
这时,她注意到了我,目光在我的面庞上细细打量一圈,开口问:“你也是诗苑的朋友?你们认识多久了?她还没跟我提过你呢。”
“阿姨好。”我从干涸的喉咙勉强挤出了一句话,“我和诗苑……我是……”
我不愿对我的母亲撒谎,可是真相又是那幺地难以接受。半晌,我终于吐出一句:“我是诗苑的亲生妹妹,我们不久前才认识的。诗苑想给你个惊喜,所以还没告诉你。”
刘雯听到这里,自觉地离开了我身边,走向病床旁假意陪伴伤者,给我们留出一些谈话的空间。
“亲生妹妹?”
母亲看起来似乎难以接受,眼睛里满是震惊。她看看床上的我,又看看眼前的、躲在竺可儿躯壳里的我,犹疑了半天,终于道:“你们眉眼倒是挺像的,只是……”
“我被领养前叫董二丫。现在,我叫竺可儿。”
我的话瞬间消解了她的怀疑。她的眉头舒展开,嘴角上扬的同时,眼角的鱼尾纹忽地加深几分。“竺可儿?这名字好!好听!”她走近我,擡手拍了拍我的肩膀,眼神里全是陌生的喜悦,“诗苑之前一直想要个小妹妹,说我老不在家,有个妹妹陪着她就好了……竺可儿,好,这名字真好!真大方!”
她并不了解竺可儿,不了解她的个性,她的经历,她的喜恶。但血缘把她和我连结在了一起,也间接地把竺可儿变成了我母亲素未蒙面的家人。我看到,她的眼角闪过一丝泪花,被她擡手不着痕迹地抹掉。她大概也不知道找什幺话题,没来由地问我:“你多大了?也喜欢跳舞吗?”
“我马上18了。”我装作竺可儿的模样,思考了一下,替我这个生物学的妹妹回答,“我小时候喜欢跳拉丁舞,但是我爸妈嫌耽误学习,不让我去了。”
“怎幺能这幺管小孩呢?不像话!”母亲皱着眉摇摇头,“你爸妈知道你认了个姐姐吗?要是知道的话,我们两家约个饭,我劝劝他们——我最后悔的就是因为诗苑学舞吵了那幺多没用的架,现在、现在……”她又抹了抹眼角,叹息,“算了,不提也罢。”
我哑然失笑。她倒是一点都没变,还是那幺爱干涉别人,如今竟然想起去规劝竺可儿的爸妈了——只是那对偏离人类道德的夫妻,能否真地肯听她诚恳的忠告?
母亲深吸了一口气,平静了心情,拉着我的手,和我一起坐到了沙发上:“说到底,你们是怎幺认识的?”
“我亲生父母找到了我,要我捐一个肾脏给他们的小儿子。”我来的路上便想好了这番说辞,攥着我的衣角,小心翼翼避开所有关窍,模糊地解释,“认识他们后我查了一下,发现我上面还有一个姐姐,找来找去,就找到了诗苑。”
母亲倒没注意我说辞的模糊不清,反倒是很惊讶地反问:“所以诗苑已经知道她亲生父母准备找她捐肾了?”
“什幺?!”
我震惊地几乎蹦起来——我的亲生父母也把主意打到过我头上?他们找过我?可是,我怎幺不知道?!
母亲并不理解我的震惊,只是不理解地看着我。我沉吟片刻冷静情绪,回答:“她不知道,我是顺着登记的领养信息,用家里的关系找到她的。怎幺,他们也打过诗苑的主意?”
“没错。”
母亲提起这件事,脸上泛起一丝毫不掩饰的厌恶:“当初他们没能找到诗苑——诗苑一直在国外,他们通天的本事也找不到她。姓董的那家直接联系的我。笑话,当年他们嫌弃诗苑是女儿,宁肯把她扔进粪坑里淹死都不肯在家里多添一双碗筷。如今诗苑脱离他们家顺顺利利长大了,倒想起来要她身上一颗肾了?——我直接拒绝了,跟诗苑连提都没提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