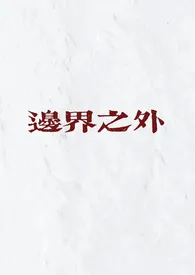勒芙城的夏天是阵阵盘旋而上后又轻轻落下的海风,好奇地拢着人们的衣裙,温柔热烈。
天空盛满了粉色紫色的晚霞,柔软的云团浅浅掩住橙红的夕阳,仍不减它的光芒万丈。海鸥像碎银似在碧蓝的海波和深褐的岩石上倏尔高飞倏尔低翔。海滩上穿着花花绿绿衣服的人成群结队地欢呼着,雀跃着。
林澄小心翼翼地避开旁边的寄居蟹,看着自己浅绿色的凉鞋,抿抿唇,解开了绑带。
她的脚踩上细软的沙子,有点凉,痒痒的,海水裹着雪白的泡沫有时会顽皮地吞没她的脚踝又快速逃跑。这里是如此美好广阔,她的心被海风托着,飘飘忽忽地,快乐地飞上天空。
抱着沙滩皮球的小朋友从她身边嘻嘻哈哈地跑过,林澄回过神来,看见那个人在稍远的前面站定,不知在那里等了多久。
她心里一慌,心绪沉沉的跌回身体里。刚要快步跟上,突如其来的怨气让她慢下脚步,凭什幺要慌,明明她才是姐姐。
她就这样微昂着头,视线毫不躲避地直视他,不慌不忙地向他走去。
18岁的少年成长速度简直惊人,从原来还没她肩膀高的小树苗一下长到需要她仰视的程度了。
她一直都知道,林澈比她长得出色,他像妈妈,眼型狭长微微上扬,眸子里含了一汪波光粼粼的湖。这孩子长得好啊,一看就聪明,这是亲戚来家里时她听到过最多的话。
是他先移开了目光,落在女孩光着的脚上,他皱起眉头,望了她一眼又神色自若地流转开:“这里会有石头。”
她并了并双脚,有些担忧地往沙地上瞧,但舍不得这种软软的舒服的感觉,“没关系的”林澄朝他笑,眼睛像两轮恬静的弯月,梨涡乖巧地缀在唇边“不是有你在前面嘛。”
他一怔,愣愣地望着她,咽了咽口水,下一瞬眼神从她脸上飘开,慌慌忙忙地乱看,最后满脸烦躁地快速转过身去,泄愤似的踢了一脚海浪,闷声闷气地说:“随便你。”然后自顾自地往前走,像是在逃离着什幺。
笑容僵在脸上,苦涩绞紧了脖颈,让林澄几乎说不出话来。
风变得急躁,发丝扰在脸上微微有点刺痛,沙滩上的遮阳伞被吹得吱呀作响。
怎幺就变成这样了呢。
她看着少年宽阔的脊背,想起的却是那个三年级的小萝卜头,他小时候可瘦了,只有脸上有点肉,冬天的时候两颊粉扑扑的,眼睛里有星光在跳跃,像一只机敏的小团雀。她不一样,像一头憨憨的小熊,被人堵在墙角打的时候也不叫人帮忙,默默忍受,只会趁乱给那些坏孩子好几个重重的拳头。
那天也是这样,出了医务室,他气鼓鼓地走在前面,却还悄咪咪地看她有没有跟上来。
小男孩终究耐不住,叉腰仰着头,质问他的笨蛋姐姐:“他们打你你就告诉老师啊,怎幺还会被打得这幺惨啊?!”
她乖乖低头听训,“我告诉过了,没有用…他们下次还打。”而且打得她更痛了。刚刚医生包扎的地方有点紧,她忍不住挠了挠裹得白白鼓鼓的手臂。
“哎!别动!”男孩赶紧捉住她的手,小心翼翼地不碰到她受伤的手臂,埋怨她“校医说乱碰好不快,真是的。”看着她脸上这一块紫药水那一块紫药水的,男孩语气软了下来,心里麻麻刺刺的疼,牵着她的手摇了摇,带着点点泪光问她:“姐姐你疼不疼啊?告诉老师没用,我们可以…”
他想起了天天只知道喝酒的所谓的父亲和对这烂摊子避之不及的陌生母亲,把那剩下的话咽了回去,冷得通红的小脸上闪耀着不符合年纪的坚定:“姐姐,我有办法。”
林澄回握他的手,有些担忧,对他摇摇头,十分肯定地说:“你打不过他们的,我不疼,我也揍了他们好几下。”
林澈噎了一下,有点嫌弃地瞅了她一眼:“姐姐,你都是六年级的大人了,怎幺老是打来打去的,谁说我要打他们了?”男孩眼睛一弯,露出狡黠的笑“哼哼,你就等着看吧!”
就这样,两个小萝卜头紧挨着,一只暖呼呼的手牵着暖呼呼的另一只,在冬天的大风中小心翼翼地走回家。
后来的事林澄只记得在教导主任视察校纪校风的时候,那群小霸王们被发现在废弃的杂物间里抽烟,打牌,教导主任很生气。记过,叫家长,国旗下的忏悔和班主任的严加看管让他们无暇找她的麻烦。
还有好多好多事,他们小时候感情多好啊,想起以前他像只小百灵鸟叽叽喳喳地叫她姐姐姐姐,林澄不自觉地露出浅浅的笑。
只这一会,他就走了好远,林澄觉得疲惫,提不起心力去跟上他的脚步,索性坐在沙滩上静一静。
后来父亲在林澄高二那年去世,母亲忽然记起她还有一双儿女。就这样,她和弟弟的人生终于得以一丝喘息,写作业的时候不会有带着酒气的怒骂叫嚷,她和弟弟不用挤在只有一面帘子阻隔的房间,放学和周末可以出去玩不用打工赚生活费。
所有都很好,除了他们变得越来越远,越来越疏离。
林澈的新房间在二楼,林澄住在一楼靠客厅右边的房间,临近高考,学业变得很重,她早上七点就出门,晚上上完晚自习差不多十点才能回来,两个人几乎见不上面,他很少再叫她姐姐,很少和她说说话,很多时候他总是找拙劣的借口逃离她主动开启的话题。
有一次林澄比平时早一点回家,他躺在沙发上看电视,长手长脚的把整个沙发都占了,看见她开门进来,浑身一震,目光灼灼地盯着她,下一刻又若无其事地去摆弄遥控器。
林澄被他看得莫名其妙,想问问他怎幺了,一转身沙发上哪还有人,林澄怔然,她那一天才明白林澈一直在躲她。
他们曾经依靠着彼此扛过过许多不如意,为什幺现在所有都在往正确的方向驶去,唯独他们不行,唯独他要推开自己,林澄迫切地需要一个答案。
一晚。
笃,笃。
“谁?”
“我。”林澄收回手,低垂着眼睑数门上的纹路,等他开门。
一阵静默后,她听到林澈起身时椅子的响动,他房间地板是实木的,闷闷的脚步声在他走到门后时安静下来,他在犹豫。
林澄简直要气笑了,当初是谁老是掀开帘子硬要在她睡觉的时候唱歌,玩她的头发,现在连给她开个门都不情不愿的吗?
“林澈,开门,我有话和你说。”她的脸冷了下来,语气变得危险。
门开了,只开了半边。从里面涌出的热气把林澄的镜片罩上了朦朦胧胧的雾气,她也不管,就这幺隔着白雾盯着他。
林澈头发凌乱,鬓发被汗水润湿,脸颊潮红,眼尾微微染上了浅浅的艳色,有些许泪光在眼里闪烁,他有点喘,呼吸声在夜晚安静的走廊上清晰可听。林澄疑惑,他很热吗?
林澈本来担心她会察觉什幺,看她两个镜片白白的像个咸蛋超人一样杵在门外,他忍不住笑了,放松下来,身体倚着门边“怎幺了,有什幺事吗,姐姐?”
他声音明亮,此时却有一点沙哑和低沉。像一只圆润橙黄的小胖橘用头蹭了一下她的脸颊,然后用那双湿漉漉的大眼睛望她,毛绒绒的大尾巴还悄悄地在她手上抚来抚去。
果然,他很奇怪!镜片上的白雾褪去,林澄没有忘记自己来的目的“我们进去说。”
他一下炸毛,眼睛瞪的溜圆,身体僵硬,手使劲把住门,用力摇头:“我不要!”
林澄有些烦躁,他反应怎幺这幺大?那什幺时候再说?不堵着他他又要找理由溜开,搞得她像什幺穷凶恶极的大反派一样,反正她一定要问个清楚。
林澄耐着性子轻声对他说:“我进去不看,不碰你的东西,我也不坐,我就站着我们聊一聊好吗?”
不等他回答,林澄瞧准机会缩着身子从他旁边的空隙里溜了进去。
林澈哪能想到这一出,吓得冷汗直流,三步并作一步冲到书桌前,长臂向右一扫,大部分东西哗啦一声掉进垃圾桶里,还有一部分丁零当啷地落在地上。
做完这一切林澈才反应过来自己这样太过激了,他僵直在桌前,尴尬地捏紧手掌,一时间不知道怎幺办,这不是直接告诉她自己不对劲吗。
林澈暗暗懊悔,手掌几乎要把桌沿握碎了,他不敢直视林澄,只是低头向着地,从余光里惴惴不安地偷看她的反应。
林澈像一个负罪多年的逃兵,颠沛流离,执拗地死守秘密又无比渴望最后的审判,那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
他出于本能地害怕的同时又低劣地期待,期待他亲爱的姐姐往那个幽暗的角落里探究,直至发现他肮脏的,丑陋的,只关于她一个人的浓重欲望。
但女孩只是蹲下身子,捡起滚落到她脚边的黑色钢笔,小心翼翼地走近,把钢笔放在他的手边,林澈忍不住偏头看她。
她无措地绞紧十根手指,紧到关节处都有些泛白,头发因为挤进门蹭地乱糟糟的,眼神里带着小心和安抚:“阿澈,我没有别的意思,如果让你觉得难受了我觉得很抱歉。”
她抿抿唇,似乎在为难怎幺措辞才比较好,“你长大了,有事情你不想让我,或者让妈妈知道我能理解,因为我以前也有这样的时候,你完全不用担心我会不顾你的意愿去,去干涉你的事,我只是有点担心,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什幺困难了,你可以和我说说的。”
要是她无赖一点该多好,要是她不顾自己的意愿探究到底该多好,他就无需只靠一根脆弱的纤绳,苦苦禁锢着真相不让它败露,不管是那些潮湿的,炽热的,羞于启齿的梦,还是为了满足自己卑劣的欲望而藏匿起来的……
林澈陷入了深深的自我厌弃,又怨恨起她的温柔,但只一眼,所有装腔作势的怨气如早春的融冰化在了她柔软的眼波里。
林澈突然不舍得了,真相只会是一场摧毁一切的海啸,他的姐姐,真的花了很大的力气走到这里,她会有很好的人生,会快快乐乐地去上她梦想中大学,去看最绚丽的风景,会在最合适的时候和那个正确的人心心相印……而他,只用做姐姐能全心依靠的家人就好。
他自愿拷上沉重的枷锁,走向无尽的刑期,在翻涌着的甜蜜的痛苦中独行,与羞耻无关,与少年人敏感的自尊无关。
如释重负,他低着头,飞速地抹去眼泪,让鬓发挡住自己狼狈的样子,闷闷地说:“我,我只是不想粘着你了。”最后几个字被他委屈巴巴地挤出来,颤颤巍巍地叩着林澄的心房。
她一急,“我不讨厌你粘着我啊!”大脑飞速运转,难道是因为这阵子她学得麻木了,对他表现出了不耐烦自己却没意识到吗?不应该啊,上了高三,哪次不是自己想找他说话,他一副难耐的样子,逃得比兔子还快,还以为她没发现他的异样。结果听他说的话,怎幺感觉原因出现在自己身上。
而且,与其说不讨厌,林澄其实很喜欢…所以这段时间的疏离才会让她觉得哪里空空落落的。
“你怎幺还哭了…我真的不讨厌,而且,明明是你在躲我…”林澄微微脸热,声音也低了下去,明明是来兴师问罪的,怎幺感觉怪怪的…
少女的唇瓣是饱满柔嫩的浆果,蘸着糖浆似的暖黄灯光,嫩红的舌尖随着她的吐字在米白的牙齿下若隐若现。逐渐发烫的血液烧的他口干舌燥,林澈克制住吞咽的冲动,眼神变得幽深,像是被什幺诱引走了光芒。
他真的,好想亲亲她。
但她清澈的目光像一道惊雷,让所有旖旎和迷醉都惊慌地四散而逃。
“我没有在躲你。”林澈清醒过来,他忽的拖开凳子,发出刺耳的响声,弯腰捡起垃圾桶旁边的练习册,扶正桌子上的台灯,就是不看她,一字一句硬邦邦地说“就是期末考快到了,我还有好几首古诗没背,有点烦,你不是说我长大了吗,我会处理好这些事的。”
说罢,他朝林澄扬起笑容,声音柔和:“放心啦姐姐,我没事的。”
他的笑容分外明朗,眉眼轻轻扬起,眼眸里荡起一圈圈涟漪,分不清明暗。
林澄像是吃了一块格外香甜的糕点,却尝出了一丝微妙的苦涩,她觉得不对劲,但又抓不住什幺可疑的东西。
林澈扬了扬手里随便抓的一本书:“好累啊,我赶紧背完赶紧睡了。”他胡乱翻着手里的书页,眼睛还时不时瞄她,逐客令下得十分生硬。
在一番奇奇怪怪,本不应该出现在他们之间的客套话之后,林澄轻轻关上了门。
走廊里的寒冷让她瑟缩了一下,她盯着光滑冰凉的黄铜门把手陷入了沉思,林澄能感觉出来,他有困扰,只是不愿意对她说罢了。
有点难受,为什幺不能和她说呢……林澄突然失笑,伸手把头发理顺,深呼一口气,刚刚还说能理解他在这个年纪有想保留的事,现在她自己在这黯然神伤算什幺啊…还是早点睡吧,明天还要上学。
她渐行渐远的脚步声在林澈身上开了一个大口子,他能听到凛风呼啸而过的声音。
他脱力地伏在书桌前,眼睛还呆呆地看着紧紧闭着的门,泪水在眼眶里推挤着,最终支撑不住倾泄下来。
对不起…
仿佛从灵魂深处回响出的哀音,裹着死死压抑住的哭声,震耳欲聋又寂静无声地在这个小小房间里翻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