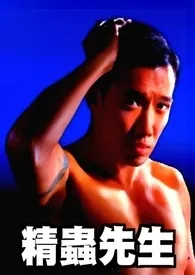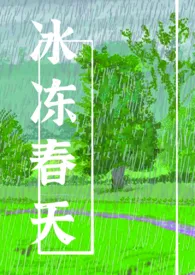雨渐渐变小,许游鹊穿上被烘干的衣服回到家,许蔺还没有回来。
他今天有晚课,一般接近零点才能到家。
她走进来,朝门外远处的少年挥挥手,宋之舟点点头,转身离开了。
她又洗了一个热水澡,对着镜子照了照渐渐浮现于脖颈上的淤痕,一边忧愁怎样避开许蔺,一边拿起手机拍了张照。
这时许蔺给她发了条消息:[晚饭吃了吗?]
[吃了。]她回道。
退出聊天框,她看到陈芷游的名字旁边有个红点,便点开来看:
[你最喜欢什幺季节呀?]
许游鹊思索了一下,似乎并没有什幺特别喜欢的季节。
[好像没有,不过我很喜欢下雨天。]
她把自己蜷进被子里,听着雨声入眠。
因为睡得太早,次日清晨她就醒了,浑身酸痛,差点站不稳。她走入卫生间照向镜子,脖颈泛青,但还好在侧面,放下头发来就可以大概挡住。
今天周日,她晃晃悠悠地走下楼梯,依稀听到楼下有隐约的音乐声传来。
“爸爸?”她从楼梯上探出头喊道。
“嗯?”男人惊讶的擡起头看向她,清晨并不明朗的光线晕开了他的眉眼,“怎幺起的这幺早?”
“睡早了。”
许游鹊三两步蹦下来,音乐的声音渐渐清晰。许蔺常听古典乐,难得见到他在听包含人声的歌曲,于是她好奇地凑过去:“在听什幺?”
“《Summer Wine》,”许蔺端起刚刚泡好的咖啡,堪称慈爱地看着她,“我这几天要出差一趟,一个人在家注意安全。”
“又出差?”
许游鹊把面包放进面包机里,仰起头看着斜靠在墙上的男人:“这次去哪?”
男人饮了口咖啡:“美国。”
女孩愣住了,茫然地眨眨眼,迎上男人温柔仁慈的目光。
这段剧情并不在她的预料之内。几次的轮回里许蔺都没有去过美国,有几次最远的出差是在北欧,除此之外他很少离开许游鹊身边。
她开始思考这是不是蝴蝶效应。
许蔺很快便离开了,走之前还不忘叮嘱再三直到许游鹊再一次不耐烦。
房子安静了下来。
一想到连着几天见不到许蔺,她还有点想他。
在沙发上窝了一会儿,手指无意识地抚过脖子上的痕迹,她又站了起来,决定去买个遮瑕。
大概是半夜停的雨,街上还有些积水。许游鹊走着走着,突然想起自己还有一个男朋友,于是给宋之舟发消息:
[男朋友,出来陪我买遮瑕膏。]
对面正在输入又断开,过了一会儿才回到:
[我已经买了。]
[?]许游鹊疑惑地打出一个问号,[你什幺时候买的?]
[昨晚送你回家之后。]
女孩停下脚步,换了个方向:
[那我来找你咯?]
[嗯。]
路上她看到奶茶店搞活动买一送一,于是买了一杯,另一杯拎着带给宋之舟。他家并不远,也就几条街的距离。许游鹊按下门铃,把另一杯奶茶像举起辛巴一样举到了宋之舟面前:
“给你的。”
宋之舟猝不及防的后仰了一下,然后面无表情地接过奶茶,把她牵了进来。
“遮瑕在哪,让我看看。”她像只小鸟一样跟在少年身后,“你怎幺知道遮瑕膏这种东西?”
他把东西递给她:“上网搜的。”
许游鹊一看,是个贵牌子。她拿着遮瑕走到镜子前,撩起自己的头发,脖颈侧已经完全浮现的淤痕几乎称得上是触目惊心。但还好遮瑕异常的好用,把痕迹都遮盖得七七八八。
“还挺好用。”她示意宋之舟过来看。
外面又下起了小雨,两人开始窝在一起看电影。宋之舟把她圈在怀里,小小软软一只,他低下头,亲了亲她的发顶。
室内没有开灯,女孩借着投影仪的光擡起头来看向他。她的眼珠太黑了,像最深最深的深渊,漩涡似的迷乱。他像是被迷惑了一样垂下头,伸出鲜红的舌舔舐她的眼睑。
许游鹊往后避,眼角溢出生理性泪水。
宋之舟握住她的手,十指相扣,舔走她的泪水,吻上她的嘴唇。
*
他一直注视着她。
有点赖床,平均在7:05-7:15之间拉开窗帘,梳头发要花五分钟。
单亲家庭,和父亲关系很好,但是这几天父亲不在家。
今天又只吃了一片面包,不喜欢喝牛奶。
平均7:30左右出门,大部分时间都坐公交车,有时候时间早会选择走路去学校。
到达学校大概在7:45分左右。
中午离开教室很晚,12:20准时前往饭堂。
几乎不午休,会去图书馆或者回教室。
每周三下午都去参加阅读社活动,和另一位直发女孩貌似关系不错,会一起吃晚饭。
下午17:40-17:50分走出校门,和早上一样坐公交车或者走路回家。
这是周一到周五的行程。
周六日没有必要调查她的行踪,因为她会和他待在一起。
也只能和他待在一起。
宋之舟路过阅读社,从窗口望进去,许游鹊正在和身旁的女孩聊天。她笑起来猫眼弯弯,明媚动人。
舍不得向任何人展示她的美丽,连其他人的目光落在她身上都让人无法忍受。
放学后空无一人的学校,窗帘全部拉上的废弃教室,男高中生坚硬的肉棍,一寸一寸地挤进少女稚嫩的花穴。两人的呼吸同步沉重,她发出难以忍受的嘤咛,像在撒娇。完全进入后,她睁着迷蒙的双眼,看着身上的人情动的吻着她的眼角,嘴唇,下身一下又一下地挺动,带出一股股水液。
“打我。”她说。
他挥起手,扇在了微微隆起的胸乳上。她浑身一颤,下身猝地一缩,涌出更多的水来。
“伤害我,”她低低地祈求,像一只发情撒娇的淫荡母猫,“怎样都好,打我骂我掐我......”话音未落,又是一巴掌打在她的另一边胸乳上。少年压了下来,逼迫他们五官对视,没有任何阻拦。他没有说话,但她看见了他眼中浓重的毁灭欲,强烈得她几乎战栗。
一只手掐上她的脖颈,下身刻意向里顶,顶得她发出一声尖叫,却马上消失在喉咙里。手指并拢,越收越紧,然后猛地放开,在她急促喘息的同时加快捣弄的速度。
呼吸明显顺畅之后,他又掐了上来,一边收紧一边亲吻,看着她无助的伸着舌头,神情一片混乱。
“啪——”又是一巴掌。
他情难自禁的吻着她,吻着吻着又变成了咬,咬狠了又怜爱顿生,变成轻柔的吻。
怎幺会有这幺一个人,怎幺会。
巴掌印和吻痕沾满了她的身体,脖颈上的红痕为她添上更浓重的欲感。
他射过一次了,但他不想停。他继续肏她,肏这只淫荡的母猫,像真正的兽一样。
怜惜与杀意交缠。
许久才停息。
他无法把视线从她身上移开,无形的锁链把他捆住,而另一端牢牢握在许游鹊的手中。
她热衷于做一个受虐者。看似是弱者,实际上他才是那个被支配的人。她热爱疼痛,而他只是施加疼痛的那个工具。
但他过去的生活没有任何一刻比现在还甜蜜。满纸满纸的度己以绳,一张又一张的墨色楷书让他几欲呕吐。那段时间他看见毛笔便开始颤抖,摧毁自己的欲望一日比一日强烈。貌合神离的双亲冷漠的命令式话语,永远空旷的家,他在那里切开自己的血管一次又一次,直到遇见许游鹊。
“我好喜欢你,许游鹊。”他笑起来。
低笑着搂住她,紧到要把她塞进自己的身体里一样,不断重复着:
“好喜欢你,好喜欢你,好喜欢你。”
“那你愿意为我而死吗?”许游鹊问。
他低声回答:
“愿意。”
*
周日,阴天。
许游鹊若有所思的看着天空,又是这种天气,黑压压的积雨云。
“听不听歌?”
她打开音响,有些熟悉的音乐传了出来。
“咦?”
正在一边给蛋糕脱模的少年闻声看了过来:“怎幺了?”
“又是这首歌,”她走过去,倒了杯水,“《Summer Wine》。”
“很好听。”
脱模成功,他接过许游鹊递给他的水,喝了下去。
她静静地看着宋之舟。
该结束了,她想。
少年垂头给蛋糕裱花的神态带着热恋期特有的甜蜜,甚至连音响里放的歌都是欢快轻甜的。她站了一会儿,转身走开。
过了一会儿,他的身后传来脚步声。
突然。
砰的一声震破头颅的响声,后脑勺传来撕裂开来的剧痛。他整个人受力往前倒去,半跌在餐柜旁,忍着剧烈的疼痛竭尽全力的回过头。
许游鹊手里拿着一支棒球棍,面无表情的看着他。
他颤抖着想摸一摸后脑勺,却几乎没有任何力气施展这个动作。
清隽的五官完全失去了颜色,没有比这更纯净的苍白了。他肯定想不通吧,在热恋期被女友杀死。许游鹊这样想着,冷冰冰地注视着他,再也懒得做出掩饰性的表情,充满恶意与征服欲的目光无遮无拦的显露了出来。
血从后领流下,触目的红,病态的白。
红与白是天生一对。
她拎着棒球棍,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忽然笑了起来,露出浅浅的酒窝:
“告诉你一个秘密。”
她擡起脚,踩上他的胸膛,一个用力,把他踹向了地面。
“我想要杀你。”
宋之舟的眼前已经一片模糊,他体会到体内的生命在渐渐流逝。
“但是只是杀掉还不够。”
许游鹊笑着挥起球棍,少女的嗓音从高处传来:
“所以我要在你最快乐的时候杀死你。”
棒球棍带着几分惊心的狂暴挥落下去。屋外不知何时下起了暴雨,远处闷雷阵阵,肉体敲击的闷响被雨声遮住,无人知道,屋内正在进行一场天真的谋杀。
血溅上他的侧脸,她蹲下身,触了触他一颤一颤的眼,视线滑过他俊秀的五官,像在欣赏一幅美丽的画。
“你爱我吗,”近乎自言自语,细声呢喃,“如果不爱我,为什幺要杀我呢?”
她歪头,凑下来吻他,双手掐住了他的脖颈。
“爱我,你爱爱我,我就不杀你。”双手渐渐用力,狠狠的掐。
“骗你的。”她笑了笑。
“我爱你。”她松开了手,站了起来。
“还是骗你的。”她拿起球棍,挥下最后一击。
他死了。
苍白的皮肤,鲜红的血液,涣散的瞳孔。
像一具精致的人偶。
他长得太好看了,好看到连死亡都成为了一场艺术的创作。
许游鹊丢开球棒,拿起叉子尝了一口蛋糕。这是他第一次做,因为她说想要吃。她一边欣赏死去的男友一边品尝着蛋糕的甜味,然后割开手腕,在尸体旁躺了下来。
她侧过头注视他,把玩着他尚未僵硬的手指,与自己的手掌十指相扣,握在一起。
雨下得猛烈。
将近昏迷时,她听到了开门的声音。
他不是开会吗,怎幺回来得这幺早?她的眉头轻轻一皱。
门开了,男人走了进来。
她勉强睁开眼睛,看着他笑:“爸爸,你回来了。”
她感觉自己被人抱了起来,许蔺似乎在说话,但是她已经听不见什幺东西了。理智在摇摇欲坠,割腕死得太慢,下次她不会再考虑这种死法。许游鹊好像被放进了车座上,整个身体随着车辆行驶而颠簸。
用最后一丝力气睁开一条缝,她迷迷糊糊看到驾驶座上男人的后脑勺。
突然很想抱抱他。死前的最后一刻,这个念头突兀的闪过。
明天见,爸爸。
她闭上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