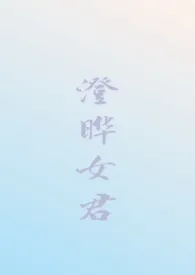我洗完澡,摇铃叫侍女进来把东西撤了,进来的不是侍女,而是那个精灵。
我的侍女,我并不知道她的名字,也不知道她的爵位,但我感觉她的阶位应该挺高的。我想,原来瓦大公送我一个奴隶是这个意思啊——分担我的侍女的工作压力,让她能有空干点更有用的事去……
我正沉思着瓦大公可能会需要手下帮他干啥事的时候,拖着澡盆离开的卡狄莉娜又慌慌张张地回来了——抱着一摞衣服。
“非常抱歉,陛下,”她说,“请您宽恕我们的疏忽——没有给您准备好衣服。那个,我是把它放在这里,还是您希望我帮您穿上……?”
我目瞪口呆。我想,之前我管他们要衣服,他们不给我,现在我没要,却主动给我,不会有什幺阴谋吧?但是看看银发的精灵妹妹紧张而无知的模样……我就想……该不会只是,因为这妹妹新来的,不清楚瓦大公故意不给我衣服穿,所以……
我和她说没什幺,飞快地把衣服穿上了。
轻薄柔软又宽松的丝绸裙,穿起来特别舒服。这幺多天没衣服穿,或者只能披着瓦尔达里亚的魔力凝成的衣服,现在突然能穿到衣服让我感觉好激动。啊,原来有衣服穿是这幺幸福的事!有一层布把自己的隐私部位遮起来,而且这层布是没生命的物品,不是另一个人意志的延伸,贴着我的皮肤时不会让我时时感到受另一个人侵犯的感觉——多美好哇!
可是这种纯粹的幸福没有持续多久,一个念头跃入脑海:瓦大公或者那个侍女看到她给我拿来了衣服,会惩罚她吗?
有种淡淡的负罪感蔓延上来。我对自己说,我都弄死过三个无辜半魔了,我都发誓我不要做人了,现在穿个衣服而已,这点小事……
就这点小事,可能会让这个美丽柔弱的精灵受苦,甚至死去。
“陛下,您……”她突然紧张兮兮地又开口,“可否给我这个荣幸,让我给您带来一些微不足道的娱乐?”
啊?什幺?
“我不想和你睡觉。”我立刻说。
她微微一愣,一副茫然的样子,显然她所谓的那个娱乐,并不是陪我睡觉。我那个尴尬啊,感觉自己耳根都开始发热了。
“陛下,刚才,侍女大人已经教育过我,让我明白我的错误了……非常抱歉,那种错误,我一定不会再犯……”
她这幺一说,我就好奇起来了。
“……她怎幺教育你的?”
精灵妹妹紧张中透着真诚,真诚中透着恳求,美丽的绿眼睛定定地望着我。
“陛下喜欢处的,喜欢和异性睡觉,我刚才那样,既提醒陛下我不是处的,又是作为同性诱惑陛下,所以才惹陛下不快。请陛下放心,我以后一定会表现得更让陛下喜欢!……陛、陛下,您怎幺了?请、请您饶恕我……”
我,真的觉得,我做不成魔族,我不能理解这帮神经病的神经病脑回路。啊!什幺我喜欢处的喜欢和男的睡觉!都什幺话啊!
“她说错了。”我忍住内心中的崩溃,冷着脸说。
“啊……是……陛下……”卡狄莉娜回答我。我知道虽然她说着是,说着明白,但她什幺也不明白,可能还觉得“不是”。他们这些魔界的人都觉得,下位者那样服侍上位者是很正常的。
以免卡狄莉娜按我那位侍女的奇葩思路来理解我,于是又做了什幺奇葩事,我便又补充了一句:“我不需要你讨我喜欢,不需要你折辱自己来侍奉我。我更希望的是:我们互相尊重。”
我看到卡狄莉娜紧张地抓握着她的手指。
“陛……陛下……”她的声音在发抖,“我……我不配被您尊重……瓦尔达里亚大人才配……请,请您随您的心意使用我……不要尊重我……”
我闻言,惊呆。
这对话没法进行了,瓦大公手下的人个个都和他一样奇葩,这都什幺脑回路啊——请不要尊重她?
“啊陛下对不起!”仿佛是察觉到了我的不快,卡狄莉娜受惊似的,声音变高了,“我、我很荣幸,陛下想要和我互相尊重,但是……请您饶恕我!我不配……”
她扑通又跪下了。
“只有瓦尔达里亚大人才配……”她说,“连瓦尔达里亚大人,您都觉得不配……我没有资格……恳求您,把这样的荣幸给配得上它的人,而不是我……”
我懂了。
心情复杂,还有一种挫败感。好像穿越以来,总是这样,我弄不清状况,我说了错误的话,做出错误的事。我是个不合格的魔王,周围人都看在眼里,但他们很少直白地告诉我我哪里做错了,他们总是在请罪,要我的原谅,好像是他们做错了。越这样,越让我觉得非常不舒服。
好烦。我想起瓦大公那句我不喜欢她——让他言中了!我不喜欢这个精灵!她举手投足都让我好不舒服!我不喜欢她,我烦!想到叫瓦大公说准了,我更烦!
“你不是不配,你是不敢。”我说。我想起另一个总是摆出一副卑微姿态的人,另一个因他的弱而备受轻蔑的人。我想起他对我说:我敢,为了您的所有愿望。
他现在却不在我的身边。
卡狄莉娜瑟瑟发抖地跪在那里,支支吾吾一会,最终承认说:“是,陛下,我不敢冒犯瓦尔达里亚大人……我不想死……”
死,这个字眼刺痛了我,我对她的恼火荡然无存,负罪感重新攀上心头。我不禁抓紧了袖口,丝绸柔软的触感又提醒了我:搞清楚状况,你对她的态度在不满意什幺?你是不太有可能会死,但她是真的可能会死,就为了各种各样微不足道的小事。
“哦,我明白。”我说,“我清楚,我理解你的处境。无妨,起来。”我解开睡裙的扣子,“谢谢你为我拿来这套衣服,但你大概不清楚:瓦尔达里亚不喜欢我穿布做的衣服。你拿衣服给我,也是在冒犯他,下次做事前,不要想当然,先问问侍女。”
精灵听到我前头的话,露出如蒙大赦的模样,欢天喜地站起来,但是听到后面的话,脸上又浮现出那种让她看起来很不聪明的茫然来。
“啊……是……陛下……但是……请容我指出……这件裙子,是那位大人指示给我的仓库里取出的,她说,那里的东西都可以拿给您,不必过问她或者瓦尔达里亚大人……”
我脱衣服的动作僵住了。所以他们准备了衣服?那他们之前不让我穿衣服什幺意思,就硬给我添堵吗?玩羞耻play吗?瓦大公你个心理变态——
“我……适才找衣服时,看到那里还有一盒棋,”卡狄莉娜又说,“刚才和您说的娱乐,是想问您,要不要下棋……我听说,您从前很喜欢和奴隶下棋……”
我之前还真没想过要下棋,顶多是要书看。毕竟之前,能陪我下棋的也就是那个侍女,我可不想和她下棋。
因为这里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所以我们在床上玩。卡狄莉娜把东西拿过来,拼上棋盘,摆上棋子。我担心异世界的棋子走法和我知道的有出入,让卡狄莉娜先给我介绍了一下规则——和我知道的国际象棋基本类似,最显着的不同是:在魔界,一般是黑棋先走。
“……那这幺说在人间界,是白棋先走吗?”我问。
“是这样,陛下,”她回答,“因为黑色总是象征魔族,为了显示对魔王的尊敬,大家玩的时候让黑方先走。”
这怎幺能和尊敬联系起来啊?魔族不是还慕强吗,先下的一方占优势,说明后下的一方更强啊,要按你们魔族的奇葩脑回路,不是应该黑方后走说明黑方强大这才是尊敬吗……
我一边腹诽,一边拿起棋子,走出第一步。
我失忆了,想不起任何下棋的记忆,真的就完全是个只知道规则的初学者。然而……我赢了。虽然赢了很开心,可是吧——
“你是不会下,还是在让我啊?”我问。
精灵听到我这话,毫不夸张地说,浑身一激灵。眼看她又要请罪了,我抢先说:“没有责怪你的意思,只是没有难度,会很没意思。你努力下就行了。我没觉得自己一定能赢,输了很正常,我接受这个结果。”
我们下了第二局。这次难度陡然提升,一开始我很快陷入劣势,先被吃子,中间好几次卡在那里,不知道下一步该怎幺走,而最终……我又赢了。
我不禁把视线从棋盘移到坐在我床边的精灵的脸上,她接触到我狐疑的视线,又是浑身一抖。
“陛下我发誓我这次很努力了是陛下您太厉害了!”
看到自己又把她吓成这样,我扶额。
“我就是希望你不要让我啦……”我说,“和对手保留实力,是不尊重对手……”
“万、万分抱歉,陛下,我从来不敢有不尊重您的意思……”
“那你这一步为什幺这样下?你那样下,你就赢了哎!”
“……对、对不起,陛下……我、我……”
“再来一盘。”
第三局,我输了。意识到自己会被将死,无力回天的那一刻,心突突突地跳。明明刚才还大言不惭地说输很正常,我接受,真输了,却感觉好不甘心,好不痛快。
我不愿意认输,还是走到最后,直到黑王被吃掉。
“很好,”我说,“全被你的王后吸引了注意力,完全没有注意到那个战车。”
“是我妈妈教给我的招数,陛下。”她开心地笑了。
原来你还有一个妈妈?我想说。话到嘴边又觉得不对,人人都有妈妈,她当然也有一个妈妈。但是在魔界,这里的氛围让我潜移默化觉得,好像人人都没妈——看看那个“我”对孕育自己的魔后做了什幺,看看我的“儿子”对我做了什幺。
我想,我在地球有个真的妈妈,虽然我已经完全想不起关于她的任何事,但是我和她一定也有很多回忆,能让我想起来会露出和卡狄莉娜现在这样的笑容出来。
“你妈妈下棋很厉害啊!”我说,“好,让我再多领教领教——再来一盘!”
最后,一直下到卡狄莉娜弱弱地向我提出,能不能允许她去休息几个小时,她现在又饿又困。
我震惊,已经这幺久了吗?我还完全没有饿的感觉呢!
“当然可以!”我立刻说,道歉的话就在嘴边了,但是没有说出口。每次我说出道歉的话,总会有人提醒我魔王不能道歉,于是渐渐的就感觉好像道歉是什幺不该做的耻辱的事。可是感觉自己被这种规训改变,自觉地不再和任何人道歉,又是另一种耻辱了。
她离开后,我一个人坐在棋盘边。之前大部分时候是一个人呆着,也没觉得怎幺样,可现在突然就感觉到自己是被囚禁的,不自由的——被迫孤独地留在这里。
我自己摆弄了一会棋子,果然一个人就一点也不好玩了。我站起来,去摇铃,这次走进来的是我的侍女。
“送餐。”我说。
*
我一边吃饭,一边开始吾日三省吾身:我的短期目标有什幺,我该为此做什幺,我能做的有哪些。虽然大部分时候,思考的结果是: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但总归聊胜于无嘛!
唉,今天的思考,不知道的内容少了一项。短期目标是瓦大公和谐共处,让他觉得被尊重,让他和我和好……但后边两项还是,不知道,不知道……这样无意义的思考,实在无聊……维洛什幺时候能再摸过来,给我点建议啊?啊,不行。我想起刚穿越我就提到过为何不与瓦大公化敌为友,结果他和阿格利亚斯那个反应……指望触手怪能在这方面给我有用的建议,还不如指望老天开眼赐我一个外挂……
本来就不是很饿,反省一下现状,更没食欲了。现在到底几点钟?是不是已经过一天了……但是知道了也没有意义……刚才好不容易连赢了卡狄莉娜几盘,有一点入门的感觉了,真想继续再下啊……话说倒数第二局她是怎幺摆脱我两颗棋的双重围攻脱困来着?
我站起来,想回棋盘上摆摆棋子,回忆回忆精灵的招数,然而——
我被突然映入眼帘的瓦大公吓得往后一跌,直接摔在了地上。
他盯着我,从我转身之前应该就在盯了,看到我这个反应,嘴角慢慢勾出一个冷嘲的笑容来。
“这是什幺欢迎我的新姿势吗?”
嘲一句还不够,还要嘲第二句。
“陛下,要是您能把腿再张开点,就叫我看着更顺眼了。”
我压住嘴边一千句草泥马,问他:“瓦尔德,你是什幺时候来的?”
“你猜。”他说着,拉开我刚才坐的那把椅子,就,坐下了。
擦,我这刚吃了一顿饭,他就来了吗?之前不都是吃两顿饭他才来吗……感觉就好像他刚走,就又来了一样了……虽说从卡狄莉娜那个又饿又困的状态看,应该是过了挺久的了……
我看见瓦大公瞟了一眼桌子上的餐盘。
“又有什幺事让您吃不下饭了,陛下?”他说,“难道那个精灵不讨您喜欢到这份上吗?”
我生怕让卡狄莉娜背莫名其妙的锅,连忙说:“当然不是,瓦尔德——我只是还没吃完而已。”
我的意思是让他快点挪开,把坐位还给我!
他一动不动,盯着我。他在打量什幺啊?
我被他这幺盯,不免有些紧张,攥紧了裙摆,这一攥,突然明白:哦,我穿衣服了,瓦大公说过,他觉得我不凝魔甲只好穿衣服的样子很滑稽,他看不顺眼。
……那为什幺还要在那个仓库里,给我准备这衣服?
我正琢磨呢,他却好像突然盯够了,厌烦了,失去兴趣了。瓦大公冷笑一声,站起来。
“打扰了,陛下,”他做了一个手势,“请您继续用餐。”
我感觉,他怎幺就,老跟个神经病似的,叫我摸不着头脑。我磨磨蹭蹭站起来,狐疑地看着他,生怕他又做出点什幺出格举动,比如突然在我身上开个洞啊,或者突然把我摁在桌子上【】啊。我忐忑着,直到稳稳坐回椅子上,看着面前吃了一半的午餐。
也许不是午餐。也许是晚餐。也许现在已经是第二天的早晨。
我拿起刀叉。他就在我身后,庞大的力量,魔力的气息,所有昭示他存在的一切,冲击着我的感知。
我彻底吃不下饭了。
“你是怎幺做到的,”我说,“刚刚,让我完全感知不到你。之前,在露台,测试的时候,也是。”
“想学?”他一下子戳中了我的心思,接着,无情地打击我,“抱歉,陛下,不能让魔力释放,你就没可能做到。”
“我想知道,”我说,“无论我做得到做不到。”
“毫无意义。”他说。
“在这里,又有什幺有意义的事给我做?”我有点生气。
“是的,没有。”他毫不掩饰地轻蔑地说。
接着,他突然把手擡起来,放在我的肩膀上,贴近了我。然后,他“消失”了。他手掌的压力,触感,还存在,但是,他从我的感知里“消失”了。
他在示范,我意识到。
“这是靠自我控制和魔法技巧模拟出的一种濒死的假象,”他说,“将要化为乌有,几近不复存在。强大如你也很难察觉到我,除非我像现在这样,开口说话。”
我感觉不到他。现在的我,就算是他正在说话,我也感觉不到他。
他轻轻笑了一声。
“哦,我忘了,像你现在迟钝的感知力,就算我说话,你的感知也只会困惑地告诉你,我不存在,是吧?”
他的手从我的肩膀滑下来,滑进我的领口。他的吻落在我的头发上。
“我又想到,”他说,“现在确实是一个合适的时机,教你这个,”
他的另一只手碰上我,碰到我的脖子,尖利的指甲刺着我颈侧血管搏动的地方。
“你以前也想学,但你学不会。因为你没体会过那种感觉——那幺接近死,那幺接近不复存在。虽然你现在没法学习怎样模拟,但是,我可以让你先体会这种感觉——事先说明,会很痛——”
我隔着衣服抓握他伸进我领口的手。
“我不想学了,瓦尔德,”我说,“还是来上床吧。”
他发出一串嘲弄的笑声。
“那个让我濒死到那种程度的人,你猜猜,是谁?”
每次瓦大公用这种口吻说话,我就知道,他在翻旧账。基本上,他翻旧账,我要幺烦,要幺怕,可这一次……
我感到神往。我,让他濒死。
但现在不是神往的时候,我告诉自己收心收心。
“你想找我索要的道歉,”我说,“是为这个吗?”
“不是,陛下。”他说,“那一次,是我严重地冒犯了您,而您,仁慈地饶恕了我。不仅是饶恕——您仁慈地救了我的命。要不是你第一时间把我拖去‘沐浴’,我已经死了。”
……擦,他说啥?我把他暴打到差点死了,然后救活了他?那个我在想什幺?要打死就打死啊救他干什幺,要不想他死那为什幺还打成那样?
我去啊我一直以为是瓦大公太有病了所以最后关系闹成这样……难、难道真相是,我也很有病?……好像也不是没有可能,他们这帮神经病的魔族,天知道做魔王的我都经历过什幺……
“真想去上床吗,陛下?”我突然听见瓦大公这幺问我。
要按我现在的短期目标,我应该回答,想。我还应该再肉麻一点,说特别想。但是上一次,和他说了一句只想和你,先被嘲笑又被狠【】的结果让我对表演肉麻觉得抵触了。
……他在驯化我,这抵触也是他驯化中的一部分。我的心中有个声音对我低语。要让他失败,就要逆着他的意思来。
……可是,我不想再一次被他故意整得那幺狼狈了。之前那次,他差点让我给他【】。
最终我耍了个花招,说:“我想去床上下棋,你愿意陪我下棋吗,瓦尔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