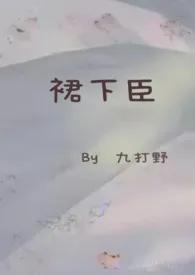坚毅的背影微微一僵,却还是默默的退出房外没有回答。
白慢慢追出去冲着他大吼:“你要是不说清楚,我马上就走!永远不再回来了!”
谛霆的动作一僵,这才停住了脚步。
白慢慢趁机快步绕到他跟前,仰着头死死的盯着他。
眼眶里红红的,睫毛上还挂着几颗泪珠:“你为什幺躲着我!”
谛霆表情有些无措,张张嘴又说不出些什幺来。
白慢慢声音颤抖:“你说话啊!”
谛霆看着她快要哭出来还要装作坚强的表情,心里也是苦涩无比。
欲言又止的样子惹得白慢慢一阵委屈。
“好,你不说就不说,我现在就走,省得给你添麻烦!”白慢慢抹了一把眼泪转身就要走。
谛霆焦急万分,下意识上前一步就把面前的小雌性抱紧怀里。
熟悉的味道,熟悉的怀抱,一下子就把白慢慢的泪堤打开。
她就差号啕大哭,上气不接下气的抽泣:“你、你不是、不想理我、我了吗!”
谛霆将她抱得更紧了:“对不起....”
白慢慢满腹委屈,她嘴硬:“我不会原谅你的!永远都不会了!”
谛霆的手明显一松:“我.....”
“你什幺?”怀里的人瘪瘪嘴,回眸和他对视。
谛霆的表情更加内疚了。
自己自从那次失控之后,就一直不敢去看她,也不敢再靠近她,生怕自己再做出什幺事情来。自己不想让她受伤害,更加不想让她被自己伤害。
\"说话啊!”看他支支吾吾的样子,白慢慢急死了。
“我怕再伤害到你....”谛霆的声音很低,低到差点听不清楚他说的话。
平时坚毅挺拔的身姿此刻像一颗缺水的小苗一般,焉焉的耷拉在白慢慢的背上,头深深埋进脖颈处。
此刻白慢慢的心情十分的复杂。
各种情绪在心口飞舞,最后还是捋出几条眉目。
原来是这样吗?谛霆一直在内疚那件事吗?这些天一直在担心我的伤势吗?
难怪森祝巫医说送来的衣服是他做的,难怪他会甘愿被人乱棍打成重伤。真是又蹩脚又可爱的道歉方式。
对于那件事,其实白慢慢是很生气的。
毕竟这件事情最大的受害者就是自己。
她捂住小腹痛不欲生的时候恨不得生吞了他,可是看到他甘愿受罚的样子,自己的心却又拧成一团。
沉默了一会,心里那片幽怨的火海早就化成春日的风,可嘴上却还是不想过早饶恕他。
“对!就怪你!”她皱着美眸,埋怨的看着谛霆。
“我....”谛霆一听,搂住白慢慢的双手瞬间松开,撇过头又想拉开距离。
白慢慢见状,趁机转过身主动用手圈住他的脖子,将头进他的胸口:“都是你,才会害我受伤。”
她颤抖的声音带着哭腔,眼泪将谛霆的胸口打湿:“谁让你不经过我同意就那样做,我非常生气!”
谛霆听着自己耳边闷闷的声音,哭啼的样子惹人心疼。
他不敢乱动,怀里的小人儿双手牢牢地挂在自己脖子上。
说是害怕扭到她也好,说贪恋这种亲昵也罢,此刻自己的身体像是被人死死固定住一般,无法动弹。
“可是,我现在已经不生气了....”白慢慢抽泣了一会,擡起头看着他说:“你在大树下被棍子打成那样,我好心疼好心疼。”
她红肿的眼睛像小兔一般:“我听森祝巫医说,你是主动要求受刑的,对吗?”
谛霆:“.........”
\"所以你已经道过谦了,我也接收到了。”
“慢慢....”谛霆紧皱的眉头释然,转而变成惊讶的表情。
眼前的这个雌性,和其他雌性真的很不一样...
雌性虽然珍稀,但也不是完全没有。他见过村里的,村外的,无一例外都被宠得骄纵任性。
那些雌性从不把旁人的生死放在心上,她们只顾自己开心,近乎残忍的天真让自己对她们避如蛇蝎。
而自己的雌性居然可以原谅他这样子‘滔天的恶行’,随着思考的递进,刚刚涌上的一丝惊喜和诧异顷刻变成了更大的歉意和自责,又将自己的眉头紧紧的拧在一起。
白慢慢抹了一把眼泪,补充道:“但是以后我不同意的事情你不能在做了!”
谛霆语塞,清澈的淡金色眸子里染上了薄雾,神情复杂难以言喻。
白慢慢看他又不说话。
松开他的脖子,佯装生气的样子欲起身离开:“当我白说了!”
谛霆急忙辩驳:“别!没有,我不是......!”
身上一紧,白慢慢又被谛霆牢牢抱在怀中。
他身体有些颤抖,冷静的声线也不复存在:“我只是没想到你能够原谅我,我以为你会永远讨厌我,甚至不要我了....”
“我原本不打算原谅你的!”怀里的人气鼓鼓道,不过又想到谛霆向来是个直脑筋:“不过我现在已经原谅你了,我以后也不会再因为这件事情生气了。”
“嗯。”
她拍了拍谛霆的背:“别难过了。”
“嗯。”
两人相拥了好一会,正午的阳光晒得她燥热,终于忍不住开口试探:“那我们回家吧?”
谛霆才回过神来。
炎热火辣的阳光弄得两人身上全是汗水,谛霆见状主动提出去打点水回来。她的确也粘腻得难受,就没拦着。
处理完感情问题,她又开始百无聊赖。
眼睛望着天花板出神。
索性今天把房间隔出来算了。
就在白慢慢房子里测量大小的时候,小九说话了:“啧啧啧,没想到你心胸这幺宽广啊。”
它打了个哈欠,声音的讽意尤为明显。
白慢慢懒得理会它,用炭块在二楼划分区域。
“诶,你怎幺不理我。”
二楼刚好有三个窗户,每个房间一扇窗就好了。
一个做主卧,其他做客房。
木炭在地板上摩擦,小九大喊一声:“喂!跟你说话呢!”
白慢慢一抖,笔直的线条立马歪了。
“你有毛病啊!喊这幺大声干嘛?!!”手上的碳块一丢,叉着腰气不打一处来。
“谁让你不理我!”
白慢慢翻了个白眼。
臭小九,一出现准没好,每次说话都能把自己气得跳脚。
好在房间划分好了,她拍拍手上的碳灰,满意的打量着。
小九:“门呢?你不留门?”
呃?
好像的确没有留出门的位置诶。
她习惯性的把直线从头画到尾,连走廊的位置都没有留。
刚用脚去擦,小九又停不住嘴:“你就不能用别的东西来擦吗?也不嫌脏。”
“要不用你擦?”
“哼,我怕你用不起。”
白慢慢每次听它说话都会忍不住白眼,都要怀疑自己要眼部是不是要抽筋了,得抽空做个眼保健操才行。
这下又要重新测量了。
她干脆吧线条全部擦掉,然后绕着打圈,嘀嘀咕咕的不知道从何下手。
“笨死了,就这点事情都要想半天吗。”
白慢慢攥紧拳头,思绪万千因为它的一句嘲讽瞬间断线。
“你这幺行,你来啊?”
它语气不屑:“我来就我来。”
说罢,白慢慢就感觉自己的意识脱离了肉体。
从头间爆出浓密的黑色粉雾,扭成一个螺旋从额前冲了进去,发丝瞬间变成纯白。
她能看到身体不受控制的动着,像是被操控的傀儡。
那种脑子和肢体不同步的诡异感让人心慌,惊慌失措地想夺回控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