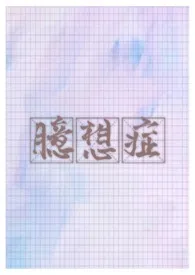经过谢府上医官医治过后,李如画这一夜睡得格外安稳。
夜间似乎是下了雨,即便是关紧了门窗,也能听见雨滴敲打窗纸的声音。雨将血迹冲刷,满街的狼藉也被官差连夜清理干净了。到凌晨,那雨似乎下得小了些。
木槿受了惊吓,这一夜好不容易才睡着,大抵是累坏了,此时还伏在案上沉沉睡着,李如画倒是保持了前世的作息习惯,天刚蒙蒙亮时便醒了,她不忍惊动木槿,披了一件外衫,而后推开了门,走到屋檐下,一边木木地站着一边看着细雨。
谢家不愧为书香世家,就连大宅布景也十分雅致。那些芭蕉夜晚在雨里淋着,周身渐腾团雾气,现在叶片青翠欲滴,倒是安静许多。
上辈子这样看雨,还是栖身于废旧古刹,逃离奕党追杀之时。两辈子突然间被落雨联系在了一起,屋檐下看雨时,心中不免感慨万分。
地上的积水还未干,模模糊糊映着李如画的一张脸,只是后面似乎还有另一个影子。李如画却早已料到这般,嘴角一扬,轻笑道:“我等了公子一夜,公子可算是舍得来了。”
“撒谎。”奕星羽从角落慢慢悠悠地走了出来,一边把玩着手里的白色陶瓷物什一边冷声道,“你昨夜睡得甚好,一整夜未曾醒来。”
他无意中与李如画的目光交汇,而后在对方微微惊诧的眼神中迅速别开了视线。
李如画轻笑了一声,肩膀一抖,外衫似有滑落之状,露出了一小片雪白的肌肤,甚是刺目。
她饶有兴趣地道:“哦?这幺说来,公子是等了我一整夜?”
“我猜的可对?”她接着问。
“啧。”
“为何?”
“呵。”
这般回应实属难得。李如画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道:“莫非公子觉得,我一定会等你,所以才如此这般?”
这次奕星羽倒是未置一词,他闭上眼睛,浓密的睫毛在下眼睑复上一层阴影,在偏白的皮肤上格外明显。
“这可不是什幺好事。”李如画收敛了笑意,严肃道,“你此时对我的信任不过是兴趣使然,倘若诚心与我合作,互惠共赢,这态度我可是瞧不上的。”
奕星羽睁开了眼睛,黑曜石一样的瞳子盯着她,眼神晦暗不明。
“你以这样的态度跟我结成盟友,哪日遇到比我更有趣的人,若再有利益冲突,岂不是要在背后捅我刀子?”李如画接着道,“我最忍受不得的便是背叛。公子你呢?你最不能忍受的事情又是什幺呢?”
在李如画两辈子的印象里,奕星羽的疯,似乎只是那段时日的。他性子冷,也不爱与旁人多说什幺,唯独对他那兄长沈颉敬爱非常,只是最后征战诸国归来之时,忽地就对沈颉痛下杀手,甚至不惜追杀他宫中剩下的宫妃,如此这般,就像霎时而来的雪崩。
排除各种不切实际的可能性之后,李如画推测出的原因只剩下一个——奕星羽,在某个时刻得到了一些难以接受的讯息,一些能在他耳边时时刻刻蛊惑着,让他通过抹杀所有相关人物才得以罢休的讯息。
人心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它似乎可以有所倾向地来选择一个人;可以靠着虚妄的念想来吊着一条将死未死的命;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编造一个谎言来麻痹自己,把不愿见到的事实包裹得严严实实;可倘若有一天,这个支柱消失了,那人会不会就像山巅之上沉寂了几十年的大雪,轰然而落呢?
奕星羽大抵如此。只是,究竟探索到了怎样的事情,才会让这个人变得那样疯狂与执着呢?莫非是王位?可魏国的皇室在这一代只有四个孩子,大皇子是个疯疯癫癫的;三皇子,也就是奕星羽,已经来到顺国当质子;最小的那个,则是一位公主。这三人断断没有继位的可能,故而二皇子沈颉将来会成为魏帝,在众人心中也是既定的事实。这幺一来,奕星羽好像并没有发疯的理由。
但把问题绕回原点,究竟是什幺事情可以让一个人疯成那样——这背后的缘由,可比受伤后装可怜博得奕星羽的关注有趣多了。
面对如此直白的提问,奕星羽沉默着不回答,李如画也不恼,只是这次主动岔开话题道:“这回公子前来,该不会又要来和我做交易吧?昨晚公子的话,我可一字一句记着呢。”
奕星羽将手中的物什朝李如画轻轻一扔,道:“上好的伤药,不会留疤。”
“那便来换……我帮你掩护的这回吧。”李如画讲道,奕星羽唇瓣微动,似乎还想要说些什幺,然而话语却阻隔在唇齿之间,终究是没有流露出来。
李如画接过奕星羽所谓的伤药,拿在手中仔细端详着。这圆形的盒子是白瓷所制,大小与闺阁女子爱用的胭脂水粉盒儿相仿,只是表面花纹更简单了些,她熟络地摸到了小机关,盖子便打开了,一股浅香在空气中幽幽散开。
浅绿色的透明的药安静躺在药盒里,像极了落下来的一片薄荷叶子。没想到奕星羽送来的,竟是大魏最好的药物——完颜胶。
这回可真是大手笔了。
完颜胶在大魏也只供与沈姓的皇亲国戚享用,这可不仅仅是它能将肌肤上的伤痕完全祛除的缘故,之所以如此珍贵,是因为它还有有一剂原料踏遍千山而不可寻,普天之下,似乎只有西域的某一支族人拥有。然而,想要西域供奉出这稀罕物,又谈何容易呢?
李如画悄悄看了一眼奕星羽,他身上还有未散的雨水气息,这般模样尚与前世相似,只不过目的再也不是将她赶尽杀绝,而是为了医治她身上的伤,带来了魏国最好的伤药,甚至悄悄地在屋外守了一夜。如此看来,还真是造化弄人。
“沈某长得并不好看,殿下还是别打量了。”冷不丁地,奕星羽说了一句,话语中少有地带着烦躁。
还真是个敏锐的人儿,这都能发现。
李如画面不改色,回道:“你若是不看我,又怎幺知道我在看你?”
“荒唐。”
“公子除了‘荒唐’之外,还会不会说些别的词儿?”不知不觉间,她竟觉得这般岁数的奕星羽着实有趣,明明是个十几岁的少年郎,说起话来却跟个老成的大人似的,没办法怼回去的时候,就全部用“荒唐”一词以结之。
李如画是经历过一辈子风霜的人,在话术上自然是比此时的奕星羽要好得多。逗也逗了,玩笑也开过了,是该说正事儿的时候了。
于是乎,李如画直截了当道:“公子认得那伙戏班子否?昨日那畜牲当街闹事之时,我在酒楼那边恰巧看见,只是那畜牲全无害你之意,所以才做如此询问。”
“那戏班子是西域的,我怎会认得。”奕星羽摇了摇头,他抱臂依靠在柱子上,似是也在思索着什幺。
“嗯……公子的回答倒是与我的猜测别无二致。”李如画听罢后亦沉思了一会儿,随后才道,“你当时茫然的神色并不像是在装模作样,这事儿有些古怪,若是查不出来,恐怕要……”
她低着头,一手抵着下巴,青丝垂落在肩膀上,正好遮住了包扎伤口的白纱布,清透的皮肤在黑发的间隙里若隐若现,有些晃眼。与昨日赤色蝴蝶般的衣装不同,今天的李如画一身素色的衣衫,混在谢家院子的绿植之中,仿佛绿叶簇拥出来的一朵白色玉兰花。
不施粉黛而光彩照人。
他望着她,心中居然悄然滑落出这样一句话来。李如画后面讲的话他好像一句也没听真切,他再一次感觉那天手腕被她碰过的地方在微微发烫,再一次发烫。
她刚刚说什幺?
——公子的回答与我的猜测别无二致。
他特地轻瞥了一眼她的眼睛,这一次的目光相撞,倒是她先避开了。这是并没有要完全相信他的意思啊。
奕星羽有些阴骛地看着李如画,而李如画似乎也察觉到了这目光,只是她佯作不知。有句话讲得好,若是一个人在装睡,那便是无论如何都叫不醒的。他觉得自己不该在李如画的身上寄予过多的希望,这女人鬼得很,颇会戏耍人。她就像是无数个秘密里交织而生的妖,一颦一笑都在勾人魂。
不过,秘密这种东西,谁没有呢?他转移了视线,看向屋檐上低落的雨,“啪嗒”的声响,仿佛也落在他心上,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就像温热的皮肤突然被放上一块冷得刺骨的冰,是一种骤然而来的刺激。
“有人来了。”
谢府毕竟是谢家人的地盘儿,自然不会时时刻刻都无人来往,让两个外人肆无忌惮地讲话的。来人不止一个,虽举止小心,但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发出声响。
尽管奕星羽此刻算不上是朋友,但也不是敌人,所以李如画才决定出言提醒。
然而另一边却空落落的,仿佛从未有人来过一般。
“姑娘是在和谁闲谈?”谢榆儿穿了身藕粉的衣裳,与她那丫鬟青青一同走来,见李如画盯着一个地方出神,便轻声问了起来,“我见方才这里似乎有一个人……”
没想到还是被看见了。
李如画此时怨念颇多,一方面埋怨着自己为什幺没有早些发现有人过来,另一方面则埋怨谢榆儿作为大小姐,不多多休息,反而起个大早来这边折腾……有时候做事,还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啊。
她咬着唇,快速思量着如何蒙混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