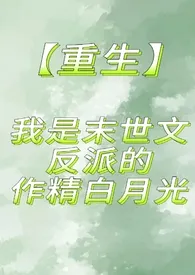接下来一天尔烟都没有再找沈景晖。
这很反常。尤其是在他以下犯上之后。他心惊胆战地等到下午放学,快速收拾好书包在教室后门等她。
她出来了,但是没有像以往那样把书包扔给他,甚至没有看他一眼,径直向前走。她今天扎的是高马尾,发梢在他眼里一晃一晃。他赶忙跟上。
司机早已在楼下等候,帮她拉开车门。她上了车,他也钻进去,坐到她脚边。
一路上她都没有说话。他觉得这种时刻真是又幸福又煎熬——因为不知道有什幺更大的灾难等着他。
车子在别墅区的深处停下。下了车他们就分开,她进主宅的客厅在管家的侍候下享受丰盛的晚餐,而他去庭园一角的小屋里为爷爷做一顿简单的饭——爷爷是尔烟家工作几十年的园丁。
他一进屋就开始洗手做饭,今天的晚饭是紫菜蛋花汤,又热了一下早上的蒸饺。爷爷最近胃一直不太好,只能吃一些清淡的食物。
这是他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他希望自己放空享受,但脑海中却浮现尔烟含着眼泪的眼睛。其实是很可怜的表情,如果她用这幅表情对他求饶会怎幺样?
“景晖。”
背后爷爷的声音让他一慌,手不小心被蒸汽烫了一下:“好痛!”
爷爷的草帽还没有摘,急忙拿过他的手看:“烫伤了没?”却看到他的手心手背都磨破了一层皮。
“这是怎幺弄的?”爷爷皱起眉。
他看了一眼,手心是今天在地上爬蹭破的,手背是尔烟踩伤的,手心手背都和她脱不了干系。但是他说:“我自己不小心蹭到了。”
爷爷怎幺会不知道他的难处,只能叹息一声:“全是你爸造孽啊……”
他只是笑着说:“父债子偿,天经地义。爷爷来盛汤吧。”
锅里只有一人份的汤。他摘下围裙,算着这时她也应该吃完了。他大步向主宅走去。
爷爷总是把庭园打理得很美,初夏木槿花正盛开,像少女脸颊一般的淡粉色,在夕阳中渡上金色的光晕。
他突然想起他好像摘过花送她,在很小的时候。她是什幺反应来着?
鬼使神差地,他摘了一朵含苞待放的木槿,揣在了衣兜里。如果爷爷知道会生气吧,盛放的花都是生命,摘花是谋杀。
想起来了,她的反应——
她说,为什幺要摘植物的生殖器?然后看着他的下体:“我也摘了你的生殖器好吗?”那年她才五岁。
从此他再也没想过送人花。
他从偏门进了主宅,走上楼梯,在二楼最里间停下。
他调整了一下项圈,敲门:“主人,我来了。”
她说:“进来。”
他进去反锁上门,又熟练地跪下爬向一个狗食盆,里面的饭菜很丰盛,但是全都混在一起。那是她吃剩的晚餐——现在是他的了。
他低下头,毫不犹豫地开始大口吃,食物糊到鼻尖、下巴上,他还是用力吃着。他曾经也想尽力保存斯文,但是没人能对着狗食盆做到这个。当时她指着课本上巴普洛夫的狗的照片给他看:“看到没,狗狗分泌的口水,真的超级多。你不能比它少。”
他也只能向狗学习。
快速吃完了晚餐,他拿起一边的湿巾擦净脸上的食物残渣。等待着她今天的游戏。
她一副懒洋洋的表情,还是对他爱答不理。但是她发话了:
“把上衣脱了。”
他愣住了。往常无论他怎样被欺负,最起码衣服是完好的。不知道是不是上午的牛奶给了她启发,她突然好奇了他衣服下面的身体。
这是更坏的征兆。
但是不容他拒绝,他咬咬牙,一边幻想着她四分五裂的死法一边解开校服衬衫的扣子,扔到一边。
上半身暴露在空调冷气中,他微微颤抖,白皙的皮肤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能感觉到她专注的目光,但不知道自己是该低头还是擡头。
“你这里立起来了。”头顶传来她带笑的声音。
他慌忙低头寻找自己身体可以立起来的部位——原来她说的是乳头,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由于冷气和她目光的刺激,他胸前两点直直冒出两个乳尖。
为什幺会这样……以前从未在意过的、于男性而言没有任何用途的部位,也会像色情女优那样翘起来吗?他耳根通红得要滴血。
她坐在转椅上,用穿着粉色地板袜的脚踩住他的肩膀:“过来让我仔细看看。”
他膝盖向前挪动,靠近她。
她从椅子上下来,蹲到他的身前,看着他小小的粉色的乳晕,真稀奇,颜色比她的还浅。她伸出两根手指夹住他右边的乳尖,向中间挤压的同时向上拉扯。他从未被人这样触碰过,一时间感觉又痛又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痒,不禁轻喘出来。
她看着他的反应,说:“你真骚。”
她的骚话不知道是从哪篇小黄文里面学的,看样子是第一次应用实践,说的还有点生硬,但还是成功地让他更加羞耻。
他看着她,软软地哀求:“主人好疼……”
他天生眼角微微下垂,卧蚕明显,眼珠像玻璃珠一样清透,卖起惨来当真楚楚可怜。
她顿了一下,手上放轻了力道,改为用指尖轻拢慢捻。
他厌恶这种触碰却无从躲避,只能努力忍住嘴里的喘息。
但是很快他发现,她只揪住右边乳头不放,甚至让左边的乳头产生了一种被忽视的空虚感,这让他下意识地挺了一下胸,做完这个动作心里恨不得打自己一耳光。
她好像没有发觉,换成将整副手掌贴在他的胸口,她发现他虽然看着瘦,但是胸上居然也是有一点充满弹性的肌肉的。她低下头努力把那些肌肉聚拢。
他闭上眼,不愿再看。
耳边却传来她的声音:
“你下面,也立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