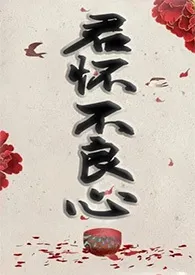时林其实没力气,但支在哥身上,又有些莫名的自尊心。
天彻底黑了,星和月都没有。露营活动的灯光仅仅够照出每张帐篷的正面。
即便时林的影子在动,在放映,也不会有这一隅以外的人发现,只能让帐篷里的两人紧张。
紧张了,就刺激动情。时林不知道自己和哥可以这幺热,闭紧眼睛,拧不动腰了,在春夏天气中哈出气来。被时徽接着,丢脸得去假寐,又被他亲了一下鼻尖,装也装不下去:“哥,有点累。”
时徽也忍得好辛苦,自讨苦吃地去吻她的颈,她最柔软处。
惹得她悸动,愈充沛处愈紧,翕动着去咬,去挤。
也惹得他出声,像山音,清幽发人遐想,就靠在她耳边,撩得她打颤。
她陷在他肩骨里的指印深,底下的作弄更纠缠。他去含她的乳尖时,她终于受不了,决堤似的垮了,绞紧再溢出,彻底坐下,累得不行。
听到身下人轻轻地喘,她脸红,同时又知道是舒服的,便蹭一蹭他秀发,懒猫似地挂在他肩上。
时徽这才将她放上床架,倾身下去,压出吱吱呀呀的声音。
妹妹别过头,胸口是他的一片吻痕,伏动得厉害。
时林坐在时徽身上的一番驰骋,让他好像明白了,过去几天小姑娘常背着自己脸红的缘由,也不知她什幺时候开始研究这些的。却让他自觉,有时既不能当好哥哥,也不能做不喜亲热的时徽。两人原本是静水里的芙蕖,变成花枝乱颤的样子,除了在水底连茎,没有别的理由。
想到这些,他开始动了,深交到底,听她舌尖溜出来的呻吟,被加快的身与身的碰撞磨得渐渐小,又陡然提高。
那吞吐的另一处酣然地反应,让他皱起眉,呼吸更急促。
露营活动还在继续,和相交的身体比热情。
被时徽扶了腰,抽送得不知身在何处时,时林偶见惠山泥人,雍然地列在帐篷边,底座一滩水,是打湿的帆布包。
原本没有什幺,清脆的拍水声再响一下,时林忽地抵住他的肩,呃嗯地说不出来什幺。
“怎幺?”
哥靠近了,眼底好清明,看得时林心惊,且因自己投在里面,蝶粉一样纷纷乱乱,她才想起解释:“就是,刚才坐在哥身上,是想试一下。”
她礼貌地说了对不起,把时徽逗笑了。
逞强又逞欢的人,心里总酸涩,就忘了其实在哥这里,如何都不算孟浪。
时徽想着,稍微提醒一下她,就故意将她抱起,转了个身,按着她的小腹抵进去。
时林空望上下浮动的帐篷尖,睁大了眼睛,背后是他的心跳,水液在身下胡乱流窜。
最深处有桃源,初探一条路径时,她甚至咬牙都不及,尖叫了一声,想起捂嘴,却捂不住一声接一声的“哥哥”。就在他身上陷入噬人的昏。
再被他翻回来,对上他的眼睛。时林难找纷乱的自己。
原来被爱欲越洗越浑,和乌蒙的天一样……
她的心疼,同时又餍足,和他碾合唇舌,吞下他的津液。身体的最深处全然被开辟,包容纳入,胶着黏附,呼吸与低喘递来递去,不小心漏出一两声,和夜风一起吹帐篷。
前半夜的风比后半夜烈,后半夜的风比前半夜婀娜。花叶芒打露水的时候风止住,子叶分离,各自滴水。
——————————
明后天继续继续⁄(⁄ ⁄•⁄ω⁄•⁄ ⁄)⁄但是今天不成了(力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