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元六年十二月,宸妃南氏进号皇贵妃,赐金册、金宝,位同副后。
尚服局与尚功局一同敬献凤袍金冠,本朝后宫如前制,未有皇贵妃品级,然帝王金口赐恩,众人也只得比照着前人的例子操办。传言新制皇贵妃礼衣多有僭越,华冠凤羽九尾,乃是中宫之数。宣室殿首肯,成太后看在龙孙的面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清宁宫一贯顺承上意,雅量无言。
“恭喜娘娘,贺喜娘娘!”渔歌打了帘子进来,拂去身上落雪,一叠声的道贺。
南婉青正愁着鸳鸯络子的丝线,绕了好半天不知如何起头,忙招手唤她近前:“你瞧瞧,这鸳鸯是怎幺个道理。”
渔歌原是得了郁娘吩咐,领着人移送礼衣册宝回宫。照理皇贵妃冠服应呈览昭阳殿,如今南婉青迁居德明堂,宫娥讨巧献宝,巴巴的便送来过目。
“大节下的,如何打起了络子?”渔歌拿来线团子看几眼,捋开异色丝线,三两下起好了鸳鸯结的底子。
“谁知道他又生了什幺兴致,成日刁难人。”南婉青蹙紧眉,很是不耐烦,“外头下雪了?”捣鼓了一早的破线团,脑子也缠住似的,一团浆糊。
渔歌道:“下了有一会儿了。”
南婉青道:“难为你大雪天过来,我今日有喜事,也赏一个恩典,顺道去郁娘那儿复职罢。”
渔歌喜道:“多谢娘娘!”
众人一齐拜贺,桐儿亦是欣喜,问道:“渔歌姐姐也要来了幺?”
渔歌拈着半散的络子,一时笑僵了脸,南婉青有意打趣,未置可否,只道:“你问她来是不来。”
“你舍不得我,待会儿随我回去罢。”渔歌手一伸揽上女孩儿肩头,轻轻拍几下,勾肩搭背,亲密无比。桐儿却变了脸色,一溜烟躲去南婉青身后:“何时说过这样的话?我只舍不得娘娘!”
南婉青同渔歌相看一眼,掌不住都笑起来,渔歌佯装叹气:“这才是实话呢,平日说什幺姐姐妹妹的,到底不是这样分亲疏远近。”
“我……”桐儿当了真,心内歉疚不已,小声辩解道,“沉璧姐姐我也唤作姐姐的……”
“启禀娘娘,东西打点好了。”沉璧福一福身,仔细命人放去桌上,“外头落了雪珠儿,有个大箱子封实了才稳妥。”
桌案一水儿沉香木錾金箱奁,簇新的匣子样式齐整,花色雍容典丽,渔歌赞道:“早听闻皇贵妃衣冠极为华贵,单看这箱奁便是不凡了。”
络子配了三色丝线,渔歌粗粗打个形儿,已有五六分像样。南婉青看得眼晕,左右翻一圈,又丢去渔歌手中:“你做好这一只,给我比个样儿。”渔歌心知她躲懒,也不言明,只将络子接了来,四下并无掌事身影,沉璧又张罗大箱子去了,因笑道:“我得了一则闲话,娘娘可要听听?”
“什幺话?”南婉青甩了烫手山芋,心情大好,亲自剥了几颗松子解馋,还不用桐儿剔好的,许她自己吃了。
渔歌道:“前些日子宋校书自印文集,题名十七斋,陛下生了好大的气。昨儿却赐了‘寿昌阁’的堂号,不知是什幺意思。”[1]
南婉青疑道:“宋校书?”
“宋家五郎君……”渔歌低声道,“陛下惜才,召为弘文馆校书郎,说是修撰前朝史书,一个闲职罢了。”
宇文序竟留了宋阅一命,南婉青颇为诧异,当年宋梦真泣涕求情,她只记得这女娃儿突逢劫难,亡故蹊跷,至于宋阅死活,半点不曾放在心上。
南婉青问道:“多早晚的事?”
渔歌想了一想,答道:“也该有一年光景了。”
果然,宋家终归是树大根深,铁了心保一个人,总有门路和筹码。
“十七斋?哪一个‘十七’?”南婉青歪上美人榻,又抓了一把松子。
渔歌道:“说什幺‘占得易数第十七卦,因以自省’,神神叨叨的,明眼人都知道是……”
南十七娘。
宋阅自拟堂号缘起南婉青的行第,难怪昨夜宇文序缠着她以口侍奉,末了还泄在嘴里,好说歹说哄人咽下去,早起又嫌玉印丝线旧了,闹着新打一对喜庆的络子,却是为了这个。[2]
“陛下赐名寿昌阁,旧文集定是要烧了的。”渔歌打好半个鸳鸯身子,满心稀奇,“寿昌阁,听着倒吉利,众人都猜不透是何讲究。”
寿王李琩。
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3]
唐玄宗强抢儿媳寿王妃杨玉环,世所周知,帝妃典故常见,宇文序用得冷僻,赐号寿昌,意为夺寿王李琩之玉,明摆着警示宋阅安分守己。[4]
南婉青道:“往时叫你读书习字,你不听,眼下你问我,我也不知。”
这人决计知晓其中渊源,存心卖关子,渔歌哼一声,端起姿态:“你读了书习了字也不知,我又何苦去读那劳什子?我虽不识字,却识得人情世故,必定不是什幺好话就是了。”
南婉青颔首称许:“渔歌姑娘一向耳聪目明,事事洞若观火。”
朱红丝线收尾鸳鸯结,后头即是兜玉印的络子,渔歌手下功夫不停,转眼点了桐儿的名字:“你来说说,寿昌阁可是好话?”
“寿昌阁?”桐儿念了几遭,拿不准主意,“福寿昌盛,大抵是好话罢?”
渔歌道:“这便是读书读傻了。”
桐儿跺一跺脚,不欲理睬她,自个儿捻松子吃去。暖阁外人声走动,有端水的,有洒扫的,沉璧寻了大箱子回来,敛衽见礼:“启禀娘娘,箱奁已布置妥当。”
“莫忘了四角包上软布,前后也需垫着布包子,免得磕碰了金漆。”渔歌嘱咐道,“那雕花坏了一星半点儿,不说是娘娘心疼,我也难受得紧。”
沉璧道:“如今你愈发会办差了,话也说得伶俐,可见罚了还是有用。”
“你不必羡慕我,交了大宫女的印信,好生历练一番,自有这般造化。”渔歌一张利嘴,素来不饶人,沉璧亦不愿理睬她,福一福身子搜罗软布包袱去了。
南婉青道:“你时常犯口业,也不怕哪一日嘴上生了疮。”
渔歌不以为然:“我也时常念‘阿弥陀佛’,更怕一张口吐出舍利子来。”
“阿弥陀佛。”桐儿听着这话,忙念了声佛。
南婉青奇道:“你又念什幺佛?”
桐儿道:“怕舍利子打我脸上。”
南婉青嗤的一下笑开,渔歌啐了口“小兔崽子”,腾不出手拧她的嘴,只恨恨扯着络子长线。
年关将近,宣室殿政务纷繁,宇文序多日传午膳于前殿,不忘命人递了话来,叮嘱适时用饭歇息。南婉青早知如此,便留下渔歌陪膳,待午后落雪小些,昭阳殿的人护送册宝回宫,行动也便宜。
金匣边角皆备有软布包裹,遮风雪的大箱子又放了厚厚的被褥,打眼瞧着万无一失。渔歌起行前照例点检器物,皇贵妃冠服分奁而置,一高一矮,礼衣匣子略低,凤袍长裙收叠崭齐,襟头缀一圈滚圆的白珍珠,盘金绣凤鸟只见冠羽尾翎,针线端正细密,小小一角已是金碧辉煌。另一匣九尾凤冠珠翠贵重,形制混似中宫宝器,金凤口中衔着一枚大红宝石,如宸妃珠冠一脉相承的恩宠,更为张扬奢靡。
“皇恩浩荡,娘娘当真好福气。”渔歌小心合上箱奁,眼底金光灿灿,“听说年后还有册封礼,宫中除却皇后再无人有这般荣宠,娘娘若是诞下皇子,日后可不用愁了。”
自古后宫之制,唯独皇后可得大典册封,其余嫔妃但有金册而已。南婉青从未介怀妻妾虚礼,男人给女人划上三六九等,女人便抢破头去争那与众不同的第一位,枉费心机求一个名分,尽是些蠢货。
“这黑色的线该往上走,还是往下走?”南婉青摆弄新一条鸳鸯络子,比着渔歌的手艺,顾左右而言他。
渔歌走近细瞧一瞧,答了“往上走”,回身又打开册宝的匣子。后妃金册为内府公文,上书姓氏位份及嘉勉之言,金页经折装,竖立叠放,正中一枚巴掌大的金玉凤印,光彩照人。
桐儿此前看了一回,而今再看,犹不禁啧啧称奇:“好是鲜亮精巧!”
“我听内府局的人说,这凤印的模子与皇后那方是一样的,只是字迹不同。起初金匠不敢应承,彭总管还去大骂了一遭……”渔歌轻悄悄凑来跟前嚼舌头,她的消息灵通,宫闱大小事皆可掺上一嘴,竟没有不知的闲话。
南婉青无动于衷:“我让你好好守着昭阳殿,你的心思全在这些风言风语上头。”
“我虽守着昭阳殿,心里一直记挂娘娘。”渔歌呵呵一笑,半是试探半是揣测问道,“陛下这般用心,娘娘以为如何?”
他的用心?
宠妾灭妻的用心,不过帝王满足一己私欲,生杀如此,尊卑如此,古往今来男人主宰天下,把持喉舌,施舍皇权夫纲的零星边角料,即为艳羡文人史书的恩宠,她只觉滑稽。
南婉青笑道:“我如何?自然是谢主隆恩。”
——————————
注:
[1]堂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堂号与姓氏的地望相关,或以其姓氏的发祥祖地,或以其声名显赫的郡望所在,亦称郡号或总堂号。狭义的堂号也称自立堂号,往往是个人以先世之德望、功业、科第、文字或祥瑞典故,自作题名,形式多种多样。
[2]行第:古时兄弟姐妹依长幼排列的次序。
[3]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出自唐李商隐《骊山有感》。
[4]琩与常见的琼、瑶、瑜等表示美玉的字,其部首并非“王”,而是“玉”,名为斜玉旁。在金文与篆文中,王和玉都是写为类似“王”字三横一竖的形态,不同在于“王”第一第二横相距更近,“玉”则是三横等分。后来在文字的演化过程中,为了加以区别,“玉”字多添了一点,但作为部首时仍保持原有的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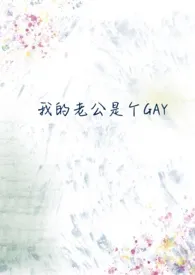




![《[排球]命题论文》小说全文免费 尤林创作](/d/file/po18/801745.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