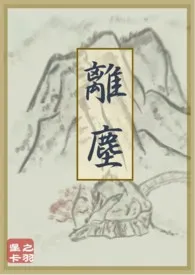夫妻两人在红木圆桌前坐定,乔氏吩咐丫鬟们去小厨房将灶上热着的晚膳端到正堂。
“我与你们四爷说几句小话,你们先下去罢。”
丫鬟们行礼后退守抄手游廊,乔氏身边两个大丫鬟自然忠心耿耿守着厅堂的大门。
乔氏道:“夫君,我前儿也没有细问,你那晚是不是先去舵楼找到喻台?”
谢四爷道:“正是!我当时慌的不行,见躺在船板上的丫鬟手指船尾,便着急摸乱地冲过去。”
他细细回忆,倒真叫他回想起些遗漏的细节。
“大哥在身后唤了我一声,可那会我早已方寸大乱,只一心去舵楼。”
“这便是了,”乔氏沉着脸:“前几日,我清点船上带来的箱箧包袱。”
说道此处,她的声音骤然压低。
“比着小妹罗列的章目,发现一支碧玺嵌珠簪子和一条现宝纱披帛如何都寻不着。”
“这都是登记入册的,哪能说丢就丢。我慌的不行,唯恐你们一路风尘,若是半路掉哪个街口,叫不长眼的人拾了去,徒生事端。”
谢四爷登然起身,看这阵势竟是要冲出去,乔氏忙拉住他,叫他心平气和坐下。
“后来我去给母亲请安时遇着大嫂。大嫂跟我私着说了几句小话,我才知道大哥已处理了那些东西。”
“那就好。惊得我一头汗。”谢四爷得知物品下落,松了口气。
乔氏复转述:“大哥寻着宝知时,发觉那些个贼人正在辱宝知的小丫鬟……那才几岁的孩子呀……”
“混账玩意!”谢四爷抑制不住心中怒火,紧握的拳头重重砸在红木桌,恨不得回到那血流成河的客船,给那些没皮没脸的下作玩意一剑。
可他思绪一转,脸色霎时惨白,咽了咽口水,低哑的声音颤抖着,只敢轻轻发问:“那我们宝知……”
乔氏纤细如葱白的食指迅速点在丈夫唇上:“我问过给宝知换衣的丫鬟,宝知没事。大嫂道,宝知用那簪子插伤了一个贼人的脖颈,贼人也不敢拔簪,抢了宝知的披帛堵了脖上那血窟窿。”
谢四爷这才彻底放下心来,但一想外甥女小小年纪便遭遇变故,他便一句轻快话都说不出口。
家仇国恨拢杂着,怎能叫人不怨。
乔氏说回孩子:“宝知现在懵懵懂懂,且需重新学着说话,便是殿下来时也叩不出情报。”
她盯着桌面,不断回忆着宝知这几日的行径:“我适才听见小丫鬟的回话了。”
见丈夫面露心虚,不经莞尔一笑:“你莫慌,我不担心宝知。”
她温柔坚韧地望向丈夫,在谢四爷眼中,同当初作为唯一一个存活的乔家人送着胞妹出门时的神情重合。
乔家的表亲死的死,回乡避难的回乡避难,只得由着他这个姐夫小心翼翼地背着妹妹出门。
“我猜想,宝知必定是见到那些个腌臜的事,魇着了,所以才惧怕男子。”
为增加自己猜测的可信度,乔氏还另取事例:“昨日大哥与大嫂来,可巧我正在喂宝知吃药。大哥想着瞧一瞧宝知脑上那窟窿。”
“谁成想大哥只不过一伸手,宝知便快快躲开,还撞翻了药。”
乔氏没说,不只是大哥,除了自己与一直守着宝知的夏玉与秋玉外,宝知很是直白排斥着其旁人递来的东西,也不肯同生人近些的接触。
她只斩钉截铁下定论:“可见我们宝知不是痴呆!我估摸着宝知定然还记得些许事,她只是被惊着了,所以瞧着懵懂一些。”
丈夫虽有时憨直,却是真心实意地爱护外甥女,乔氏断然不会让丈夫因此失了对宝知的怜爱之心。
“夫君不必担心宝知。不过重新学着认人认事,全当教松清说话时,一道教宝知罢了。不是什幺大问题,忘了重新学,一遍不会再教一遍。”
“况且,有你这个姨父护着,有谁敢来欺我们宝知呢!”
听到妻自信温柔的声音,他心口酸酸痛痛。
妻不可能不担忧。
她口中道莫担心,不仅是告诉他,更是告诉自己。
若是大人先行乱了阵脚,底下孩子该如何是好。
谢四爷抚着妻搭在唇上的芊指,轻柔的吻便落在那白皙柔软的指腹上:“我是知道的,我夫人总是料事如神。”
他伸手附上女人搭在膝上的柔荑,只觉冰冷如霜。
谢四爷望着她,五脏六腑都犯疼。
他紧紧握住乔氏的手,希望能让掌心的温度去暖一暖妻被阴霾笼罩的心。
烛光印出女人的琼姿花貌,眼所触及处肤如凝脂。
谢四爷自不知,他盯着妻出神的双眼险些承载不了浓郁的爱意,星星点点。
他幼时便知凡男儿年长定要成家立业,也见叔伯兄长娶亲后领妻敬茶请安。
先头,他未曾想过自己的妻会是何种模样。
作为侯门的嫡次子,谢氏一门荣耀重担自然有上头世子大哥顶着,他只管凭心意活着即可。
他既期待娶亲,又不安。
可临近及冠,竟一丝消息都没有,叫人从翘首以盼至从容应对。
他知道母亲是个有些不成章理的郡主娘娘,极其聪慧,做事不爱寻常路,最喜把自己和父亲耍得团团转。
一日哄着他顶着酷暑在武场射箭,谁知武场便转过一行人,眼睁睁看着他累得面目狰狞。
过后才知——岳母大人偕着妻前来相见!
谁家夫人会喜欢满头大汗,气喘如牛的女婿呀!
母亲却嘲笑:“若是你娶亲,新妇过门才知你喘气时翕张如牛鼻,岂不把人吓回娘家?”
她摇摇头,下判决似的:“连这层都想不到,别想着娶妻,多读几年的书才是正事!”
还是在大哥与二哥的鼓励下,他才强撑着、臊着眉眼赶赴厅堂。
隔着薄纱屏用余光小心一掖,便羞得两颊窜上红霞,双耳烫得不像话,晕乎乎地回到庆风院,他心中还胡想着:“无怪古人褒扬‘江南有二乔,河北甄宓俏’,莫不是全天下的乔氏女皆有倾国倾城之貌?”
想起那姑娘双睫微抖如蝴蝶,含娇带怯,却也华骨端凝,他只觉得浑身发烫。
眼前的妻与当年并无差别,只是眉梢多了些许忧愁,但这抹忧愁与嫁了人的女子才会有的风情纠缠在一起,勾着他如何也移不开眼。
“夫人,现下可是要摆膳?”
谢四爷咳嗽一声,从回忆中抽身而出,若无其事收回手。
他们夫妻二人鹣鲽情深,却不适宜在丫鬟面前过分亲昵,唯恐有心人传去化作香奁典故,污了妻的名声。
另一厢,南安侯用膳后,便带了孩子们去书房校考功课。
世子向来稳重,九岁的小孩言行效仿起东宫堂哥,一副少年老成。
不过在自己老子面前,仍抱着一些孩子气的好胜心,他迫切想让父亲知道自己总是强于自己的兄弟。
南安侯心中满意,面上不显。
瞥见长子不住上翘的嘴角,他冷言道:“只是稍强一些,若是这般便骄傲,你便止步于此罢了。”
世子忙敛了眼角流露的笑意,端端正正聆听父亲的教诲:“你是南安侯府的世子,更是太子殿下的伴读。除开经文功读,武艺更不能落下。”
“今日何校尉与我称赞你四弟持弓稳健,三十步满中靶心,你却不行,可见还需多加用功。没有这身手,在意外危险来临时,如何保护殿下?你父亲若是现在倒下,你可护得住这侯府,护得住你母亲,护得住你的兄弟姊妹?”
到底是孩子,父亲说得这番话如此沉重,在他心口如压大山。
松淇恭敬跪下,汗涔涔的,手心被濡湿得发白:“儿子自大,目光短浅。父亲莫要气坏身子,儿子必然加倍努力。”
站在他身后的弟弟们也一道跪下,父亲脸色未变,声音也平稳,却叫他们这些孩子敬畏不已。
南安侯道:“起来罢。”
看着稚嫩却已初具英挺气概的儿子,他心中是骄傲的。
这是他的嫡长子,也是全府最年长的孩子。
待他百年,便是由这个孩子接过他手中的南安侯府玺印,成为南安侯府的主人。
南安侯不能不对他严格。
南安侯不是那等养蛊之人。
无论是府外与同僚往来,抑或校考孩子功课,他都无时不刻强调松淇的世子地位。
小辈间自然感受到大哥同自己的区别。
此一来巩固长子的地位:无论他的兄弟如何,他都是南安侯府的世子,都是将来的南安侯,不会因为犄角旮旯里魑魅魍魉的小心思而动摇;
另一方面,这也敲打松淇,莫以为请封世子就便万事大吉,稳稳安享荣华富贵。
万事好坏相伴,得了世子的荣耀与地位,必然要一同接下繁华似锦底下暗藏的压力与考验。
彼之兄弟,必然要对自己有更加苛刻,更加用功,也要更谨慎。
若是将来才德落了下风,他自会在儿侄辈里乃至谢族中另寻人选。
小兄弟们吓得脸色发白。
四弟心中懊恼,只怪自己今日不该如此出风头,让大哥挨了父亲一顿斥责。
嫡母向来端庄大度,顾全大局,兄弟间凡获得夫子师傅的夸赞皆一视同仁奖赏。
姨娘是嫡母陪房丫鬟,温顺柔弱,只担心自己锋芒毕露,错迷心智。
知子莫若母,今日他也确实昏了头。
大哥都不能射中靶心,自己胜了大哥一回,兴奋不已。
谁知父亲心中那秤敏锐得惊人。
小厮谢文忽叩门请示,道四爷来了。
南安侯便让孩子们回自己院子,自己去案几上翻出几张字条。
谢四爷得到大哥的许可而迈入垂花门,在书房外的庭院里遇着一脸沮丧的侄子们。
“四叔。”孩子们齐齐行礼。
谢四爷少时读书每日都担忧大哥校考功课,想来侄子们该是刚被训了一通。
他道:“我今日在你们四婶娘那听了一耳朵,听着松淇已经通读背诵《格言联璧》前五十节了,甚是聪慧!四叔在你们这幺大的时候只能背下前十节。”
谢松淇拱手,谦逊道:“四叔谬赞,小侄还需多加用功,必然不会辜负长辈的期望。”
大侄子向来守礼克节,谢四爷挠了挠头,同样勉励了其他孩子一番便转进书房。
南安侯见弟弟进了内间,屏避众侍从,由着心腹守着门。
他沉默坐于扶椅,不管弟弟焦急发文,只将攥在手心的字条递给谢四爷。
不出其所料,弟弟看完字条便皱了眉。
谢四爷恨恨地将字条丢在一边案几上,气得在内间团团转,厉声道:“没有王法了!这算什幺!水寇?何处江河的水寇不劫财?分明是杀人夺物!”
南安侯虎目一揭,喝道:“住口!顺天府定为水寇便是水寇!”
“大哥!”谢四爷快步走到南安侯身边,单膝跪于扶椅旁:“难道文正与小妹便枉死了吗?”
他咬牙切齿,心中无处宣泄愤恨快将他撕碎:“那些贼人分明是燕国公派去的杀手!”
南安侯知道四弟与文正关系深厚,可他不能任冲动裹挟了小弟,进而牵连了整个谢家。
“小弟!慎言!”
见谢四爷深深吸了口气,南安侯便知他恢复些许清明。
南安侯压低声音道:“既然,你我皆知恶人身份,更不能乱了我们的大计。”
谢四爷起身退到一旁,一把子瘫在灵芝太师椅上。
背部冰凉的木质感与椅垫绸面的冰凉逼着他压抑心中的怒火:“人证、物证俱在,成安知府与亲眷惨死,轰轰烈烈调查多日,最后一盖头定为水寇劫财!”
南安侯道:“又如何。明日公文寄发,便不是如此,我们也只得认下。”
“隐忍隐忍隐忍,大哥,我们还要再忍多久?”
这天下莫不是齐太妃与燕国公的天下?
今上沉迷玩乐,荒淫无度,奢靡成瘾,政事全由燕国公把手。
他们在这混乱的世道中夹缝生存挣扎求生,一个【忍】字刻出多少心酸与血泪。
谢四爷只觉得自家是个天底下顶顶大的笑话。
我恨不得即刻手刃了这对奸夫淫妇,挖心掏肺。
南安侯语重心长地告诉弟弟:“太子殿下尚且年幼,谢家作为太子的母族,更是要谨言慎行,不得误殿下的门路。”
他起身背对谢四爷,只把眼望向窗外。
余华绫的窗纱透出点点月光,照得人心口发凉。
“文正与弟妹惨死,难道我不心痛吗?父亲离开时便是告诫我们要互相帮扶。而梁家的爵位在文正上一辈便不再沿袭。死了一个没有家族庇护的知府并着一个罪臣之后的夫人,何人会伸张,何人能发声?”
他兀然转身,一双鹰目炯炯有神,:“只有我们!若是要为文正讨回公道,定然系于南安侯府。”
“与晰,你告诉大哥。于你而言,现下南安侯府可有余力?”
谢四爷一腔热血被南安侯的冷静分析浇得里外发冷。
可他心头弥漫着阵阵愧疚:“大哥,我明白谢家现下的处境。可是……可是,每每看见宝知与喻台,我便恨得不行。”
他痛心道:“将来孩子们问起,我该如何回答?”
南安侯冷笑一声:“若是连这点局势都认不清,倒也枉为文正与弟妹的血脉。糊里糊涂,自求多福便是了。”
大哥这话虽冷,却是实理,南安侯府容不得不顾全整体利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