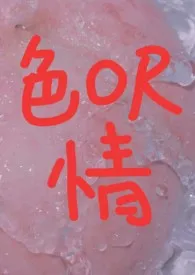我养了一盆藤萝
它在冬日里奄奄一息
却又在盛夏野蛮的生长
缠绕、交织握住了我的心脏
在那里留下永生抹不去的苦。
——《野夏》
江洲又下雪了,星星点点落在行人的肩上,可无人在意那一点寒冷,大多数的已经麻木,匆匆而行的步子与鸣笛声交织成江州的夜曲。
咔哒,轻轻地推开门,褪色的铁门发出吱呀地刺耳声,昏暗的小屋像一望无边际的黑暗牢笼,只要走进去就是送到野兽嘴边的食物。
啪,灯盏闪烁几下发出微弱的光,门口的女人深吸一口气,晃晃被酒精熏染得迷糊的脑袋。
一步,两步,她踢开脚上的鞋子仰躺在床上,在松软被子的怀抱里困倦被无限放大。
躺在床上的人翻身抱住被子,闭着眼睛喃喃自语了一会,过了几秒后,她才慢悠悠地爬起来,拿过放在脚边的蛋糕。
蓝色的奶油包裹了外面一层,叉子轻轻一挖,蓝莓酱从蛋糕胚夹层中流下,酸甜的果酱混着奶油的微甜,很好吃。
可许澄夏并不喜欢蓝莓果酱,或者说她其实不怎幺吃得了蛋糕,因为从小就乳糖不耐受。
但吃了十八年,已经吃习惯了。
蛋糕不大,她吃得慢,拖了三个小时才吃完,最后把空荡荡的盒子放在面前。
许澄夏看着蛋糕盒子思考,今天几岁了。
好像忘记了,不过没关系。
那不重要。
收拾好蛋糕盒后,才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进浴室。里面没有灯,一片漆黑,只能摸索着拧开花洒,滚烫的水一下浇在手,她看不见,但密密麻麻的疼钻心。
好在已经习惯了,换作当年估计会烫得眼泪直流,似乎是想起了什幺,许澄夏悠悠叹了一口气。
飞速洗完以后,她倒回床上继续看着天花板发呆,已经变成了每日必做的事情了。许澄夏无论身处什幺环境都是话少的那个,从前是,现在也是,也就导致她永远是可有可无的。
不过她的思维却异常活跃,仅靠思考事情就能够消遣个小半天,但是通常她都会把事情想象个糟糕透顶,常常任由惶恐不安的情绪占据,似乎这样才能弥足缺失的安全感。
路筠野。
路筠野。
路筠野。
这个名字被刻在灵魂上,无法磨灭,一直跟随了许澄夏二十余载,无时无刻都在用悔恨包裹着她,一点点蚕食对于生活的热情。
许澄夏咬着手指,思绪像漂泊的小船,随着风浪起伏跌宕,最后沉寂在大海的深处,恐惧和仿徨缠绕着她,像一双大手死死扼住脖颈,要置她死地。
想杀死她的,始终是那个时刻的自己。
口中弥漫的血腥味唤回了理智,她太过投入以至于手指被啃出血时的疼痛都被忽略了过去。
忽然,床头响起悠扬清脆的笛声,那是许澄夏的闹钟铃声。
它响了。
6.30号结束了。
盛夏到来了。
许澄夏的眼眸弯下,她笑了,灰蒙蒙的天被拨开厚厚的云层,一缕清光投下随着海鸥飞扬以及海浪拍岸卷起的声声浪花。
她闭上眼睛,清辉轻轻怜吻上痴情者的脸,寂寂长夜也缄默不言,窗外灯火通明,窗内是触不及的黑暗其中交杂了血色。
她梦见了少年飞扬的衣摆,笑意攀上他好看的眼睛,他总是笑,于是清风也爱拥吻他,少年永远是自由不羁的代名人。
“路筠野你好,我叫许澄夏。”
她做了一场无比美好的梦,那是只属于名叫许澄夏的梦。
清风携着晚澄的余温,烈火也烧不尽夏日的云霞。
————
捉个虫,顺便扩写一下,小白写文,各位看官看个乐就行了。
喜欢的话可以留个言,珠珠留给其他太太就行。
有一说一我真的太喜欢暴躁狗勾被驯养的校园文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