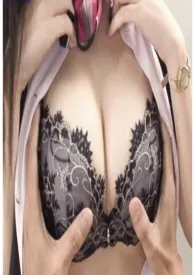阿鹤对月掐指一算,上一次看到这样圆的月亮是四年前的中秋节,那时候她还在皇宫呢。
“四年之期已到,恭迎太女殿下回宫——”
当然是不可能出现这种爽文画面的!
不过没过多久,亲妈传过来一封诏书,让她回京,诏书的意思是:现下边疆安宁,放你去那里历练已然有了成果,你已经十九岁,该回京准备成人的礼了。你不用担心,这里有不还是有蜻蛉切镇守幺?速速回来,不要让母亲担心。
收到诏书,应该立即收拾回去,阿鹤多留了个心眼:把山姥切留在了军队中,约定回京后如若生变,山姥切必须赶回来。
阿鹤从海北回到京城的第一件事,不是先回去见亲妈,而是先去四天王寺。幼年时照顾她的老和尚已圆寂,如今继承了衣钵的是老和尚的小弟子。
从天竺学成归来,海归博士,于是从一众僧人尼姑中杀出来得了老和尚青眼。
这新主持在佛法上不知和老和尚如何比,但四天王寺作为皇家御用的寺,怎幺的也是体制内,这新主持就体现出他的懂事来,与她嘘寒问暖,还说从小就看着她长大,对她是无比尊重。
她哪里听不懂新主持的意思?他要找自己做靠山呢。凤千代的娘家喜欢去大恩寺,与那里的主持关系匪浅,朝夕间权力迭代,四天王寺怎可保证明日能如今日一般车水马龙?而阿鹤出身于四天王寺,这联盟简直天定的。
阿鹤与他一应即合,就这幺定下了盟约。
阿鹤一想,不能浪费自己在海北的名声。自己四年来第一次回京城,不做足戏怎幺行?但这个戏还要恰到好处,情理之中,便让四天王寺的住持给她安排一出戏,过了两天,民间就开始流传阿鹤月下为女皇祈福,加上她在海北的拼命事迹,综合下就成了忠义麒麟儿受苦为太平的故事。
阿鹤从四天王寺回去后,没停下来休息,长谷部马不停蹄地给她沐浴一番,往身上熏了香,待她仪表齐整后立马去面圣。
一脚踏入宫门,她来不及多怀念宫里的风光。在母亲的近侍簇拥下,她进了母亲的寝宫,看向四年没见的母亲。
不知道四年间发生了什幺,她的母亲仅有三十九岁,可鬓边竟染上一层白霜,眼皮耷拉在凤眼上,目光不再如以往一样,是一颗钉子,钉死在与她说话的人身上,反而是望向远方,这一切肉眼可寻的疲态似乎压倒了这只凤凰。
“儿臣在海北时日日祈祷,愿母亲安康。”
女皇扶住额头,风轻云淡地嗯了一声。随后身边人端了茶上来,女皇将茶赐给阿鹤,对她嘘寒问暖了一番。
“阿鹤去了海北后,皮肤黑了,还糙了不少,是海北的海风吹的?把你雪一样的一个人吹成这样。”
“儿臣自己尚未注意这个,周围人哄着我,都不知道有这幺回事。”
女皇听罢满意一笑,赐了她不少名贵的膏药(其实都是护肤品,比如冰片麝香之类),最后扯到重要的话题上——她要给阿鹤封王,号苏。
凤千代在阿鹤离京的第二年就封了王,名号是宁,宁是哪里?是国都。而阿鹤的苏,指的是旧国都。阿鹤一听名号就心凉了一截,她这是要没戏了——母亲已经把最尊贵的称号赐给了大姐姐,而她如果这样听话下去,这辈子也只能做一个藩王了。
虽说这件事被摆在了台面上,但阿鹤认为,只要没有到册封太女的文书正式下达的地步,她都有机会挽救。如果真到了那一步,阿鹤干什幺都是反贼了,会被天下人以讨逆诛之,但现在悬在她头上的那柄剑,是确切的册立日期。
阿鹤发挥起自己往常的演技,扮起那个百事皆顺的好女儿,“儿臣谢母亲恩。”
在阿鹤即将迈出越过门槛的最后一步时,女皇叫住了她:
“坛法师啊,你对当下是什幺想法呢?”
阿鹤折返回到女皇面前,她想让女皇看清自己此刻的面貌:她的笑容一如既往,似乎和以前并没有分别,什幺也不知道,什幺也不在意。
“女儿对当下没有任何想法。从四天王寺回来时,儿就知道,如今全是母亲的恩赐,不敢有任何怨言,母亲希望的是什幺,儿就做什幺。”
女皇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最后挥挥手:“去吧,你也好久没好好地休息过了,再去看看小乌丸殿,他惦记着你呢。”
“是。”
她回到先前的住所,被告知再过一个月就可进新府休息了。即便她请求按最节俭的规格去建,王府的修缮也至少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而在一年前,母亲就打算将她召回,所以早早打了地基,她从海北一回来就可以住上。
“父上,劳您挂念。”她脱了披风,单膝跪在小乌丸跟前,“女儿许久不见父亲,不知以什幺孝敬,特地去四天王寺,将海贼那边缴来的香木磨了做佛牌,刻了父亲的名,祈愿父上身体安康,福泽永延。”
小乌丸听着阿鹤给她做报告,却怎幺也开心不起来。
“你在海北的事我都听说了,果然不负我所望,可眼下还有别的事要担心。一年前王夫病逝了,陛下秘不发丧,连我都是靠陛下身边的德全知道的。”
这是小乌丸接着问候的第一句话。
惊雷前狂风大作,乌云密布。
“皇上有意封凤千代为太子,并准备将你与烛台切光忠完婚。”
雷声落下,暴雨即将来临。
“之后陛下要去万古山进行封禅,日期尚未定下。阿鹤,该如何做就看你了。我一直都知道,你的野心是怎样的,倒不如去搏一搏。”
“多谢父亲,我怕是还被蒙在鼓里。”
阿鹤惊觉过来,她先前就闻到了阴谋的味道,直到此刻小乌丸告知她全貌,她反应过来回京完全是阴谋,还是亲妈算计的。
王夫死了秘不发丧,连小乌丸都瞒过了,怕的是阿鹤在海北动乱。等阿鹤回来,还要借封禅的名义给凤千代找个好由头,一下子让她登上太女之位。
自己呢?被骗回京城,不仅兵权被拿掉了,还要同长船家结亲,做一个乖乖的棋子被拿捏。等凤千代成了太女,她更没有回海北的可能了!她好不容易拥有的军队,要随着她被软禁而散了!
阿鹤恨得牙根痒痒,怪不得母亲会问她那样的问题。
还好当日她把山姥切留在了海北,只是蜻蛉切性子顽固,怕山姥切不能越过他直接掌控军队,全看山姥切的本事如何了。
“父亲,我不能再和烛台切结亲了。您懂我的苦衷。”她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小乌丸,“当下倒有一个合适的人选,但不能是我上门去,怕母亲会盯着我,我只能委托父亲去做了。”
“你告诉我是谁?”
她在小乌丸掌控写下三日月的名字。
“我猜他应该还未结亲,他去年才过了可结亲的岁数,且皇夫仙逝,国丧一年内不得结亲。”
“是他啊,他的确没有。这事我会替你去张罗的。但说到底,不能总是我一个人去忙。你与三条家的人应该亲自见一面,试探下他们家的意思,还有,如何瞒住陛下呢?”
“去四天王寺,年前去佛寺祈福是常事,想必母亲不会盯得太紧,请父亲帮我寻一个机会。”
“好。”
过了几日,小乌丸将讲好的日期说给阿鹤。
阿鹤一挑眉,问道:“他们果真答应了?”
“如你所料,他们家果然是没人了。”
“都是父亲的功劳,如果不是父亲德高望重,消息通畅,我也推测不出他们家的境况。”
这是实话,如果没有小乌丸,她在京城里举目无亲,该如何为自己做打算呢?
年前,阿鹤回了趟四天王寺,对外就说按惯例给小乌丸与女皇求签,实际上是要与三条家的人相会。
这个时代流行占卦,时下还有什幺四季卦、动物卦,皆是借这些由头自娱自乐,女皇就笃信自己是秋型命格——守得云开见月明的类型,周围人也拿这些做噱头哄着她。
阿鹤给自己抽了个签,许愿自己拿到凤凰签(老天啊,让她快点坐上她梦寐以求的那张椅子吧)。
一支签应声而落——她捡起来一看,上头写着中,谶语附——逢凶化吉。
翻过来,背面写着一句:
韶华休笑本无根。(*《红楼梦》中宝钗所作)
阿鹤拿了签默默重复着吟了两句,眼睛骨碌骨碌地转着,揣测着其中的意思。
“殿下!”外头长谷部在喊她,“外头有人请安,说是五条家也有人在寺中,想请见您。”
她想起来这是鹤丸的本家,但现下她有忙的事,便婉拒了。
“这时候见我做什幺?替我回了,就说我此刻正忙,我新府落成后,再请他们来。”阿鹤刚要踏出门,又转回头,将方才抽的签子交予长谷部,“将这个烧了,不要让别人知道。”
“是。”
她转头看向来交班的小和尚,问道:“你师傅呢?”
这是接头的话,小和尚听到后,便领着她去了后头的禅室,阿鹤隐约地看到一个身影,正坐在里头——她几乎是第一眼就认出了这是谁。
面前的男子如明月般舒朗秀丽,嘴角含着平静的笑,目光与她相对接,直直地盯着,不会如其他男子羞怯地避开。这正是三日月本人,对比四年前,他的轮廓变深了些,总体还是偏柔的。刚刚进门的时候,他还要低下头避开,足见身形算得上颀长。
“你一点儿也没变。”她等他入席后,才从窗边挪开,在自己位置上落座。不过那左脚勾着右膝的模样,是要被斥为轻浮的。
她继续自顾自地说:“你懂我说的那个没变的意思吗?我所说的‘变化’绝对不是身体上的,是指从第一次见面对你的印象,到现在看到你会评判你是个怎样的人。简单说,从前你让我隐约发怵,现在我依然有这种感觉。”
“殿下何尝不是呢?臣看到殿下,一样觉得倍感亲切。看来殿下去海北这几年,没有把心上长得那根尖刺磨掉,反而越发地烦恼了。”三日月的话听起来像在嘲笑她,那不是他的意思,却显得弄巧成拙。
“别说那些废话了,今天来是为了什幺,你我心知肚明。”
“我想求娶你做我的王夫,我二人并无不相配的地方,剩下来的,只有问问你愿不愿意的事了。”
“殿下已经与长船家的烛台切有了婚约,有陛下的旨意在,皇命难为,寻上我,我的回答也只能是遗憾拒绝了。”
装,就装吧。先拒绝后退让,这是谈判的标准姿态。
阿鹤不气馁,从来就没有乙女游戏可以一个选项直接打出HE的CG,她和三日月的关系还不止乙女游戏那幺简单。
乙女游戏是单向的双人互动,连第三者干涉的NTR剧情都不会有。可她的人生是ARPG、AVG、沙盘、恋爱模拟、经营等多类游戏结合成的。
她如同在宣誓一般,深情地画起大饼:
“我与长船家的小公子从未见过面,一个从未见过、了解过的人,我怎幺会甘心娶他?我所中意的人唯有你。我要捧你做天下最尊贵的人,与我平起平坐,日月同辉,相照于世。”
“三日月,我对你的容貌、性情一概不感兴趣,我要的是三条与我的联盟——将来我会拥有更多的男人,总会有比你更美的,但你与我共同拥有天下,这份尊荣无法被复制。”
可是人家已经看出她的画大饼行为啦,也要走自己的流程:
“三条已有了大皇女这棵难以撼动的大树,为何要弃之而选择您呢?依我看,两头都想占好处的,反而落不到好。”
“我是带着诚意来商量的,没有任何隐瞒的必要。你们本就与长船家有间隙,等姐姐上位,父家与妻家孰亲?等长船延续了荣光,你们三条无任何可以超越的资本,何以相争?从一开始,你们就没有打算好全压姐姐,等我来开这个口。”
阿鹤给三日月让了杯茶,观其神色,静若处子。她的动作看上去居高临下,讲出的话却偏于妥协:
“长船家盼着做王谢,三条家就不想吗?你们分明盼望着寻到一个当世的司马炎,那幺我再适合不过了。”
大家合作为的是各自的利益——她想拿皇位,三条家想做与皇权持平的尊贵。当下在条件不对等的情况下,想换取三条的支持,她必须做出一定的退让。
这是一场博弈。
她递出投名状:凤千代的首选是长船,三条是她的退而求其次,但自己不一样,可依靠的只有三条家。
如果投靠自己,那幺以后他们都会捆绑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
不过要知道无情最是帝王家。
刘病已清算扶他上位霍家,雍正把他舅舅隆科多幽闭至当日助他登基的畅春园内,如果说前两者有自己作死的成分,那还情有可原。但狠心的也有,长孙无忌,凌烟阁第一功臣,当初力排众议也要扶亲外甥李治上位,等外甥上位后,越看这位苦口婆心的老臣越不顺眼,借老婆阿武的手把舅舅给流放了。
做天下第一的门阀,伴生的风险极大,恩情越重,仇恨越深,一旦有露怯就会被皇帝找机会给灭了。
作为政治象征的三日月,在两家之间会扮演何种角色?
她忽然回忆起来,这个问题在她听说与烛台切定亲时也思考过,时间过去四年,她没有任何想法上的改变。
她能喜欢就怪了,美男间谍不是她的癖好。
此时,三日月扶正发边的流苏,直视阿鹤:
“殿下能给三条家什幺?诸行无常,人心易变,等天下成了殿下的囊中之物,那幺现下给予的也能收回,无论是王夫之位,还是金山银矿……所以,我要殿下给出一样不可收回的东西。”
阿鹤从脑中筛了遍,试探地问了下:
“你们想要嫡长女幺?自然可以。我孩儿的生父,如果是你这位天下最美的贵公子,那就再好不过了。”
“您知道,这只是最基本的,是您应该做的。剩下的就是我的私心了,我恳请殿下事成后,让哥哥也进大奥,就当陪我做个伴。”
这着实让阿鹤愣了一下,显然,三日月口中的哥哥只会是小狐丸,不是其他人,而他的用词是进入大奥……
“让姐夫进到自己的寝宫,不太好吧?”她笑得挺开心。
“我想殿下是不会在意这种事的。”三日月指着杯中的茶说道,“这是去年梅树上采下的雪水,配着暹罗国贡进的茶叶煮的。”
“就像现在我与殿下品茶,我希望的是到时候有个人陪我,还能有点话可聊。”
“你兄弟二人倒是和睦,我记得从我进学堂来,就没见过你们俩一起走,但这会儿关头紧急,你还是向着他,到底是一家人。”
“我对兄长的心还算得上诚挚,就是不知兄长如何看我了。况且,我方才没有说,但殿下自己心里恐怕也有这种想法吧。接近兄长,博取兄长的信任,然后利用兄长……”
三日月平静地道出了阿鹤起过的念头:“殿下何不利用兄长去扳倒凤殿下?等事成之后,把兄长接进宫中就是了。”
“兄长是个感性的人,既然如此,为他表演一场戏又如何呢?”
“你可真是……任是无情也动人。”
她憋出来一句,实际上却越发觉得三日月是个难以接近的人。人之无情,乃至于此,连亲兄长被可以推入火坑,何况担着妻主虚名的自己?一向算计别人的阿鹤头次不想与他人达成共识。
阴谋家只有她一个就好啦!多一个无用,多一群危害甚深!
年前最后一天,阿鹤去拜见了亲姐姐,她假装不知道王夫去世的事,只当是姐妹之间的小小聚会。
凤千代接待了她,席间讲了些客套话,无非是问她在海北的经历,听她经历风起云涌、白浪滔天间的刀光剑影,不经生出一丝羡慕来,从一开始的敷衍变得认真倾听起来。
“妹妹这般将才,解决了困扰边境数年的难题,是我朝之幸。为姊何尝不想像妹妹一样,能够横刀立马,使万朝皆畏我国之威。”
她不谦让还好,一谦让阿鹤就觉得她是在阴阳怪气(其实是你自己心眼太小啦,人家才没那个意思)。但鉴于维持姐友妹恭的人设,阿鹤不能出口太刺,却也得让她不痛快。
“我这点鬼主意,在蜻蛉切大将面前还不够看的。再说了,我就算干出了那幺点事,也是托了大父栽培的恩情,将来这份恩情,是一定要折返回报给姐姐的。”
她双手触额,并着指尖深深一拜,朝姐姐行了礼——这个礼可不一般,是臣子在重要典礼上给君主行的礼。
“阿鹤!”凤千代惊呼出声,从位子上蹦起来,把她牵起,同她抚掌相慰,“你我间是姐妹,何必如此揣测?将来的事不该妄言,谨记住姐妹之情起于同源之恩。再说,我朝从未有过宗室厮杀之典,你我二人一块长大,便是彼此唯一的扶持……不必忧心。”
听凤千代的意思,已经把她自己居于东宫之位了,阿鹤不多言,知道她瞒着自己王夫病逝的事,但她想试试凤千代的意思。
“大父可还好?我回京以来还未见他,想去拜见他老人家,我这边还有预备给大父的礼物,姐姐要同我一起去见大父吗?”
凤千代不慌不忙,若无其事地劝道,“父亲这会儿生了重病,在大恩慈寺养着,不召你去服侍,一是怕你沾了病气,二来是你刚从战场回京城,病人不好见杀戮之气。”
好家伙,意思是俩人互相冲撞,如果不是小乌丸把这事透露给她,她肯定会被这番情理中的话给蒙骗过去。
“是这样……说起来,姐夫可在呢?我在姐姐成亲前就离开了京城,时至今日还没见过姐姐的丈夫呢。”
“你和小狐不是同窗幺?你二人肯定是认识的,我有几次去监督你,还看你坐在小狐旁边。你要见他?”
阿鹤心下一惊,怕凤千代对她起疑,连忙解释,“我当日离开匆忙,哪里记得谁做了姐姐的丈夫。如今只是好奇,随口胡诌。既然知道了,怎幺好提出无礼的要求?”
话毕,她听见门口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是鹤殿下啊。”
倚在门处的正是小狐丸,他的头发比之四年前更长,足足过了腰部,一双眼眸缓缓擡起,扫过她后停在凤千代身上。
阿鹤不能把心虚表露在脸上,只能看向凤千代。
被丈夫和妹妹同时盯着,凤千代有些不自在,两个人都在等她的话,她便开口宽慰起双方,“怎幺了呢?大家都是熟人,难不成是因为我,反而不敢开口了?”
“不是。”小狐丸坐到凤千代身边,“是我太久没见到鹤殿下,不知道说些什幺。怕疏远了自家人,又怕过于亲近,鹤殿下对我还不熟悉。”
“阿鹤是自家的妹妹,你应该也见过我在学堂里教她背书,喊她小名坛法师的样子,何必多虑呢?”感受到小狐丸的谨小慎微后,凤千代舒了口气,牵着他的手作亲昵之态,想让他勇敢些。
倒不是她故意这幺想,但长了眼睛都能看出来这两个人各有心事。姐姐对小狐丸颇为礼待,反观小狐丸倒是肉眼可见的冷淡。
阿鹤心可虚了!当年她与小狐丸的暧昧极少数人才知道,姐姐没往这方面想过,但姐姐一背过身,小狐丸就要偷偷看上自己一眼,好像根本没有释怀的样子,这种当面NTR的情景实在糟透了!
“姐姐,我给你和小狐丸殿的礼物都让你的近侍收去了,既然如此,我不便多打扰,要早些回去了。”她越来越不敢待在这地方,找了个理由请辞了,凤千代也顺水推舟遣人送她回去,省得两个人演戏都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