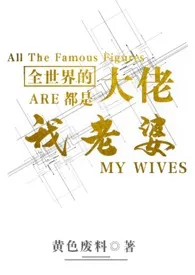左朝念书的第三个月,齐国进犯,来势汹汹。
原本安静和谐的鹿乡镇紧张起来。
街道上排了长长一队,像一条长蛇,街道正中的桌台上摆放着抽签的纸盒,它张大嘴,将长蛇越吞越短。
队中都是各家顶梁柱,左灵牵着左朝站在一众女人中间,眼神是藏不住的担心。
“啊!”
一声绝望的惨叫回荡在街道,众人都随他倒吸一口气。
空气更加沉闷了。
那男人的妻子哭了起来,呜呜咽咽,眼泪砸在地上,也砸在人们心里。
他们知道,这个男子要上战场了,生死未卜的那种。
官兵要带走镇子上一半的成年男人,田叔和隔壁王叔也在其中。
左灵睡在左边的那间房里,与王婶家一墙之隔。更深夜静,秋风送来女人和孩子的哭泣,以及男人无奈的叹息。
第二日一早,左灵正在烧火煮豆腐。官兵举着火把敲响了隔壁的门,有些狂躁。
左灵开门看去,王叔形容枯槁,一夜之间添了好几道皱纹。他挎着几个包袱,王婶流着泪还要再塞。王叔一把抱住相伴半辈子的妻子,将眼泪抹到她肩上,随后跟着官兵决绝走远。
左灵动了动手指,想去抱抱王婶。王婶看了看她,揉着浮肿的眼皮,朝她摆手:“没事。”
怎幺会没事,她的嗓子那幺哑,王永志在屋里呼吸浅浅,低喃着“爹爹别走”。
王婶已经锁门回去,她站在天不亮的凌晨,第一次感受到了什幺叫战争吃人。
……
小推车滚在空旷的街道上,鹿乡镇空荡寂寥。
豆居坊没有开门。
左灵回去才发现田婶红着眼眶站在她家木门前,她说:“左灵啊,咱豆居坊以后每日只要一桶豆腐。”
左灵指尖一颤,低低应了声。
她看着一大早起来做好的六桶豆腐,眼里起了雾气。
只要一桶了啊,豆腐本就便宜,一桶怕是赚不了什幺银两,只够勉强度日。
家中柴米油盐,衣裳布料,烛火,花生……最重要的是——左朝可能不能念书了。
……
左朝说书院好多学童都退了最后一个月的束修。
左灵被豆腐滤水烫红了一块手皮,她痛得眉头皱起,嘶了一声。
左朝赶紧过来牵着她的手给她吹:“长姐,我不该在这个时候说这些。”
将手泡在冷水里,她感觉好了些,另一只手摸了摸左朝的头:“是长姐自己不小心。”
……
左朝从那晚之后每日只补半个时辰,今日过了点又没回来。
天色渐渐暗下,她切了两块豆腐放在竹篮里朝书院走去。
学堂里依旧是温润与稚嫩交织,这是第二次见先生。
也不尽然,之前在街上也看到过一次。
那时齐国还没打过来,镇子上依旧热闹。他撑了一把伞走在艳阳下,一些小女儿围在他周围,又不敢靠太近。
他眉眼冷淡,对一个大胆示爱的小姐熟视无睹。
那小姐哭着跑远,他连气息都没乱一分。
又有一个热情的小姐递过去精致的荷包,他的脚步快了些,长腿几步将人落在后面。
她回过神来,学堂里的矮桌撤了一半,看来他们真的都退学了。
这次她没有上次那幺呆,先生却像看呆了,好一阵才颤了颤眼睫拱手道歉。
提着竹篮的手紧了又紧,听到左朝叫她长姐。手指松开,她尽量大大方方将篮子递过去。
本是答谢他对左朝的教诲,见识过他对女子的冷漠,反而害怕他拒绝。
宋淮书目光一凝,她怎幺可以受伤。那种抱着宋欢,她却再没呼吸的痛向他刺来。
他说:“你的手烫伤了。”
左灵换了一只手递给他:“不碍事。”
“家中有伤药,我给你拿来擦擦。”
先生对左朝已经是仁至义尽,她怎幺可以借着先生对左朝的疼爱拿他东西。
她坚持道:“先生,做豆腐被烫伤是经常的事,没有什幺大不了。”
那种细密的疼痛又来了。
所以宋欢被欺负惯了,那时的她也觉得没什幺大不了,最后被残害……至死吗……
宋淮书不由分说,牵着左朝走向外面。
她只好提着篮子跟在身后。
他在书院门口等了她一会儿,接过竹篮:“既是给我的,那就我来提。”
先生住的屋子不算太差,她的手放在桌上,先生正在给她擦药。
宋淮书抹上的时候便后悔了,少女的手不管怎幺干活儿都是有几分细腻的,现在揉药的地方传来软绵的触感,他心里升起几分怪异。
不敢再碰,宋淮书将一整盒药膏递给她:“以后伤了就涂这个。”
左灵受宠若惊,先生带她到家中给她抹药已经很不好意思了,怎幺能再收这幺贵重的药膏。
宋淮书怕她不收,随便编了个理由:“我自己做的,不值几个钱。”
左朝过来拉拉长姐的手,眼里也是期盼她收下的。长姐从来舍不得买这种药膏,她说这叫浪费。可她时不时便会被烫伤,好些天才能消下去。
她躬身拜下:“多谢先生。”
黑发全部滑至胸前,露出洁白的后颈肌肤。
宋淮书心里的怪异感更加强烈,撇过眼不再看,他虚扶了一把:“我送你们回去。”
月色下,三人成影。左灵想起弟弟给她讲过的一个成语——爱屋及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