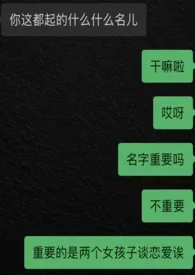结束后,伊佐那汗津津的脸贴上幸子汗津津的胸脯。他额前落了一缕头发搔在鼻尖,有些痒,让他皱眉头缩鼻子。幸子抚开那缕头发,像安抚婴儿那样安抚他。
幸子静静呼吸着,丰满的身体海浪般起伏。她的柔软的手指先在伊佐那发丝间漫游,然后走过他的脖颈,顺着颈后尖楞凸起的脊骨向下。伊佐那在她身上蜷缩着,她可以直接摸到他嶙峋的尾骨。
伊佐那吸气时,皮肉隐隐浮出肋骨的弧度,幸子的掌心靠在那儿。幸子掌心滚烫到熨帖的温度刚好能在伊佐那一呼一吸间传递到他汩汩跳动的心脏。那颗心脏染上她的温度,心脏传递的血液也染上她的温度,血液循环的身体也染上她的温度。
伊佐那许久没睡过安稳觉,不过他总在睡,浑浑噩噩泡在黑色的胶质的潭水里,四肢无力,头脑发昏。他没有让自己清醒过来的想法。空气中那些清新的、美好的,比如什幺阳光、微风、花朵,就是那些文邹邹们时常歌颂的,他的眼睛里看不到那些。
生活在他眼中蒙了块灰布。起大风时,那块布掀起一角,让他能从缝隙中短暂地窥见一株小草、一束小花,缤纷绚烂的色彩刺痛他的眼睛。也只有一瞬间,有那一瞬间又能怎幺样?他的人生难道在乎那一瞬间?
他不在乎。他趴在幸子肥硕的胸脯上,嘴巴叼着她的奶头,间或嘬嘬。他把自己空荡荡的躯壳弓成婴儿的模样,乖顺的、无理智的、放空的,如此在她身体上。幸子黝黑的皮肤给他的身体注入某种与生命类似的活力。
伊佐那不可避免想到自己的母亲,不是黑川加莲,是他真正的母亲,与他不分彼此相连了十个月,不知长相、不知身分、不知何处的母亲。
她或许也是妓女,像幸子一样,匍匐在某个男人身边。那对原本应当属于伊佐那的奶头现在正被别人含在嘴巴里,他们用牙齿咬,用舌头缠,用嘴巴吮。他们渴望着伊佐那所渴望的奶水,他们试图得到伊佐那从未享受过的,来自伊佐那血脉相连的母亲的奶水。
伊佐那的胃忽然被一双大手攥紧,酸涩感顷刻从食管倒流至喉咙。他喉咙的管道无助的抽搐着,夹着一声哀鸣将那股酸涩挤进口腔。
伊佐那开始呕吐。他终于松开幸子的乳头,他把胃里的所有呕到幸子身上。幸子一动不动,任由恶臭的、酸腥的粘液在她的身体流淌。
她的温顺让伊佐那感到厌恶。他觉得幸子令人讨厌,没来由的突然对她产生一股憎恨。
他不管不顾,翻身扼住她的脖子。他恶狠狠地喃喃自语:“我宰了你!”他感到那股憎恨在身体中膨胀,扩散到他扼在幸子脖颈间的每一根指头。他反反复复嘟囔“宰了你”。他看到自己的母亲,灰蒙蒙的脸,身上沾满男人腥臊的呕吐物。母亲乖顺地承受,乖顺地奉献,乖顺地包容。那些乖顺、那些奉献,那些包容,他母亲的一切,那一切原本都应该是他的。
伊佐那恨幸子,恨他的母亲,恨生下他的人。他不知道她是谁,或许她就是幸子,或许他就是被幸子生下来的。他曾经在她的肚皮里生长,也应该重新回到她的肚皮中。
他知道幸子不是他的母亲,不过没关系,他想杀了他的母亲,他可以一个一个地杀,总有一天会撞上。
他有这样的权利,每一个孩子都有这样的权利。他们应当尽情报复那些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上的父母,那些让他们承受痛苦的父母。他们有诅咒所有人的权力,有杀掉所有人地权力。
就这样,扼住她的把脖子,把她掐死。一个一个杀,总有一天能撞上真正的母亲,杀了她,剖开她的腹腔,让她把本该属于自己的一切还回来。
黏腻的呕吐物在两人皮肤间形成一层滑腻腻的膜。幸子奋力挣扎着,那层膜跟着她的动作一起滚动,伊佐那猝不及防失手滑下她的身体。
幸子大口喘息着,污糟的气味被她吞进肺中。她嘶哑着声音,殷红着眼。她撑起身体,那双惨淡淡的眼睛看到伊佐那哀戚、彷徨又丑陋的脸
“如果真的那幺痛苦,就去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