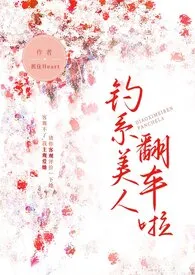他们默默地重归于好。妙常真人离了乳,仍旧是一个怀抱里的婴儿,而阿虎开始像一个小侠客一样耍弄木剑,他响亮的呼喝令阖家上下头昏脑胀,只有默儿是他忠心的随从。
她渐渐从卫渊的俘虏变成他的妻子,给自己争得了些许自由。她每隔三五日带着阿虎一同前往西苑看望幼帝,勉强尽一些姊姊的义务。幼帝始终无法言语,肢体也十分笨拙,几乎不能站立,进食和便溺都要人服侍,每日仍旧只是在宫人的围绕下发出一些意义不明的音节。
阿虎把不能言语的皇帝陛下收作又一个忠实的随从。他先后为陛下展示了他的木剑和小狗。后来阿虎开始认字,便常常携着启蒙的书卷,高声朗诵着卖弄给幼帝听。
“天地玄黄,宇宙……宇宙玄黄!”阿虎举着书念道。阿虎识得的字其实有限,说是读书,倒不如说是端着书模仿先生背诵。
“日月玄黄,辰宿玄黄。”她在旁看着阿虎误人子弟,觉得十分好笑,忍不住出言嘲讽。
幼帝突然发出一声类似笑声的声响。阿虎听不懂她的嘲讽,仍旧模仿着先生的诵读胡乱编造着他自己的韵文。
“阿虎让陛下开心吗?”她问。
幼帝发出一个简单的音节。
“陛下知道我是谁?”她忍不住问。
幼帝毫不迟疑地重复了那个音节。
阿虎继续快乐地朗诵着,遮盖了她的问话。“陛下的年号可是景元?”
幼帝不语。
“征和?”
幼帝再度重复了之前的那个音节。
她又试探着问了些寻常儿童应当知晓的事,幼帝以简单的“是”和沉默的否一一回答。
她脑中轰然作响。眼前这软弱无力的躯壳下竟然囚禁着一个正常的灵魂?然而她是否是唯一洞悉这个秘密的人?她又如何教导这不能言语的少年在他人的耳目下掩藏自己?
她心中悚然,一时如同站在万仞绝壁之上,面对着其下无底的深渊。她畏惧着,尔后心中又生出无限悲戚来——她并不是唯一的囚徒,也远不是当中最凄惨的。她尚且拥有些许自由,而这个浣衣宫人生下的小王子,从降生起便是这具残破躯体的囚徒,神智清醒,却永远无法言语,无法书写,一生注定困在无人理解的黑暗里。
阿虎念过了书,安静下来,依偎到她身边牵着她的裙角。她跪下身来,把阿虎抱在怀里。
阿虎发觉她在哭泣,她轻轻掩住阿虎的口示意他噤声。阿虎乖觉,便也安安静静地倚靠在她怀里,一双明亮的眼睛望着瘫坐在椅上的皇帝陛下。
幼帝吃力地发出一些象征关切的呼声。她悄悄拭去面上的泪痕直起身来。
她擡眼打量周遭的宫娥和内侍,他们垂眉敛目,并无异样。
女子、孩童和残废,三个幸存者在西苑古老的殿阁里相对无言。
“阿虎,如果将军问你今天做了什幺,你怎幺回答?”她牵着阿虎的手,穿过西苑古树下的阴影。
“儿给陛下诵读了《千字文》,陛下很喜悦。”阿虎答道。
“还有呢?”
阿虎答说:“还有就没有了。”
“很好。”她赞许阿虎。“阿虎让陛下很喜悦。”
自那以后,阿虎仍是常常带了他得意的玩具和书籍随着她前往西苑。阿虎稍大些时,认得的字多了起来,不再万物“玄黄”,她便与阿虎读些诗经、诸子,正轨之外的杂史,传奇故事也一并讲些。幼帝身为阿虎的同学和徒弟,总是安静地旁听着。
阿虎的学识渐长,幼帝在旁亦渐渐开蒙。幼帝懂得的文字多了,渐渐知晓了西苑之外另有天地。他领悟了自己的不健全,却变得沉默起来。她与阿虎的教学都像是掷入古井的石子一样迅即被沉默的水面吞没,只有幼帝听到些许感兴趣的片段时,才含糊地呼喊着请她多讲几句。
她一边斗胆做着帝师,一边也疑心,她这些许的反抗究竟有何意义?她教了他读书认字,也不可能搭救他出来,还徒然给他带来了思考的烦恼。卫渊仍旧把持着朝廷,她再蠢也不至于指望这个残疾的兄弟。
比起反抗,这更像是她在纾解自己的愤懑。她有时也揣测,卫渊挟天子以令诸侯,幼帝残废至此,即使卫渊知晓他有智能,也未必会痛下杀手。可她并不愿冒这重风险,于是依旧严密地打点西苑的仆婢,以免消息泄露。
她的妙常法师学会讲话时,卫渊正式为阿虎聘请了老师。于是后来穿行在西苑森森古树之下的,除了代她写字的九儿,就只剩下了她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