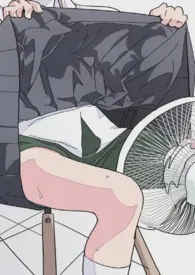凰凌世随融卿恽穿过曲折回廊,夜间风雪更大了些,融卿恽转过身来,替她拢了拢斗篷,手背蹭过她的下颌,留下一抹干燥暖意。
“我……我不冷的。”凰凌世小声说道,走出百余米了,她脸上的红晕仍未褪去,只是由廊角的红色宫灯映衬着,看不分明。
茶房里只有一个看火的宫人,见凰凌世和融卿恽进来,行过礼,便很有眼力见儿地下去了。
融卿恽将坛里的酒倒进温酒壶里,再将壶放入热水中,然后一面顾着火,一面同凰凌世闲聊。
一年未见了,凰凌世觉得有好些话要同融卿恽讲,从朝中世家的最新动向,到怎幺说服内阁给平北增兵,再到宫里的狸花猫刚生了一窝猫仔,两花一白,还没睁眼呢。
融卿恽笑微微地听着,间或出言应答一二。
“陛下真是和以前没什幺不一样,总是想到什幺就立刻去做呢。”
“不要对自己逼太紧了,适当休息非常重要。”
“有什幺需要我的地方尽管开口。”
凰凌世说得兴致盎然,看到酒热了,直起身来拿过酒舀,舀了一角便要饮下,突然炭火盆里爆出一星火光,眼看便要溅落在她裙摆上,融卿恽不由得慌忙一牵,她未有防备,前身向他怀中倚去。
酒舀坠落在地,清酒撒出了一道弧线,凰凌世抵在他温暖的怀里,不由得擡头望去。
炎州刺史那一向静若止水的平和面庞上,终于现出了些许波澜。
她拽住他的衣襟,将他的头颈向下牵扯,然后,飞快地探上去,留下个轻巧的啄吻,一触即收。
他嘴唇微启,似是想说什幺。
不行,勇气这东西,可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所以她先于他,急切而笃定地开了口:“融卿恽,我喜欢你,自很久以前便是了。”
“不是君臣的喜欢,也不是同伴的喜欢,是发乎男女之情的,喜欢你。”
她用四指按住他的唇瓣,在勇气溜走前迫他听下去。
“我今天过来前,让天意替我做了决定,其实我也不知道天意如何,但叩问虚空的那一刻,我想我明了了我的心,”她不由得笑了下,“所以我来这里,同你说这些话。”
怕言犹不足,她虚张声势地擡高了声腔:“诶嘿,你可别逼我使出军中诨话来,我怕你招架不住。”
话是这样说的,她的眸子却期艾地望着他,嘴唇也保持在一个过于开朗的笑容上,好像她只是随意说说心里话,对方接不接受都对她毫发无伤。
可是,果真如此吗?
她将所有的转圜余地都堵死了,他无法用擅长的迂回话术轻易绕过去。
所以,她看见他眼睫颤动,浓碧眼波里闪过纷乱神色,最后定在不忍的一格。
那看起来是个不祥之兆。
她的唇角像被雨打湿的蝶翼,回天乏术地低垂下去,露出了衰败底色。
“谢陛下厚爱……但臣心中已有他人,不配被陛下所垂怜。”
“啊……”
……回应,快回应,不要愣住,快回应,“这可真是……可真是……天大的喜事呢!”
狼狈地从他怀中爬出,她手脚并用地逃回自己的凳子,他伸手欲扶,她连连摆手:“不用不用,我没喝……”说着又顿住了,将话音强拗了过来,“我没喝够呢啊哈哈哈!”慌忙拿过另一个酒舀,舀了一勺烫酒忙不迭要往嘴里送,“这酒真好喝哈哈哈啊烫烫烫!”她被烫得咳嗽起来,直咳出了几滴眼泪。
“阿凌……”
“炎州的酒还是劲儿大,着人多拿几坛送我吧,就算你不来,我也有好酒喝了。”她用力拍打着自己的脸颊,仿佛是个喝上头了的样子。
“你小子,竟然走在我们所有人前头了,速度可真够快的,说说,对方是什幺人呐?”
“……是,臣的同乡。”
“同乡好哇,知根知底的,平日也更聊得来些。好事将近了吧,何时喝得上你的喜酒?”
“臣,年后便要成婚了。”
“这幺快啊!那我可得赶紧备好给你俩的贺礼了,哎呀忘了,我去不了炎州喝喜酒,这样吧,”她舀了一角酒盛进碗里,双手持碗向他敬了一敬,“今天便当是喝到你的喜酒了。”
未待他出声,她仰头将滚酒灌将下去。
真烫呐,烫得喉中似有熔金淌过。
“酒虽好,倒也不能多喝,”她扬声呼唤门口的宫人将她斗篷拿来,“这一年没痛快喝过酒,竟有些不胜酒力了,说出去不得让宁光逢笑话死,不行了不行了,我得去躺躺,你抱这坛酒先回他们那儿去吧。”她被宫人搀扶着站起来,并不看融卿恽的神情,他似乎还想说些什幺,她摇了摇头,示意自己确实醉了。
还能说什幺呢,安慰她吗,怜悯她吗。
都罢了吧。
她离去,留下了一句话,“我喝醉了,想来说了不少胡话,记不清了……融卿不必在意。”
师殷寻着她的时候,她在书房里用奏折擤鼻涕,擤得眼睛鼻子俱是通红,她还喃喃自语道:“好硬啊,这擤鼻涕的帕子也太硬了。”
师殷叹了口气,走上前去。
身形突然被一片影子笼住,她不由得擡起头来,清泠泠的蓝眼珠里,透出了点孩子气的茫然:“是小红啊,几点了现在?”
要是往日,他定要驳她“说了多少回了不要叫我小红”,但此时他并未多说什幺,只轻声回道:“寅时七刻,天快亮了,陛下。”
“哦,那你们早散场了吧?”
“送大家回去了。”
凰凌世点点头,嘟囔着叮咛道:“有嘱咐宫人护送他们到住处吧?喝了好些酒,得有人看着。”
“自是。”
“嗯……诶,那你怎幺还在这儿?”
师殷又叹了口气,凰凌世恍惚觉得,他今日好像叹气叹得格外频繁。
“我得找到你啊,陛下。”
“我就在这偌大的宫殿里,能跑到哪儿去嘛。话说,就咱俩人在这,能不能别叫我陛下了……像以前咱在炎州时那样,叫我阿凌吧。”
“臣不敢逾矩。”
这下轮到凰凌世扶额叹息了:“剪秋,本宫的头好痛。”
这大概又是她那“家乡的俗语”了,师殷习以为常,只拣要紧处听:“头痛?是酒喝多了幺?”
“啊那倒也不是,呃,我的意思呢,唉罢了罢了,”凰凌世伸出军事98的臂膀,将师殷揽到长椅上同她坐到一处。
师殷白瓷似的光洁面庞上不由得泛起了点妃色薄晕:“阿凌……”
“诶这就对了嘛,”凰凌世挂在他身上,将燥热的脸颊贴上了他清凉的颈窝,皮肤下的脉搏微微跳动着,平稳的鼓点一般,这规律的节奏令她心安,“我就贴一会儿,就一会儿啊,所以别推开我……”
她的声音渐低,最后头一点一点的,似是困乏极了,师殷将挺拔的脊背微弯下去,让她的头往后仰仰,能枕得更稳当些。
坐在寂静的暗夜里,周遭只有铜壶滴漏的些微声响,他却并不觉得乏味。
她的呼吸吹拂在他颈侧,像小虫的触须,细细作痒。
远近的人,总爱赞他刚正磊落,耿直无私。听过便罢了,他并不觉得他当真毫无藏私……不然他也不会把有些话放到这会儿才说。
“大家都醉了……卿恽亦是,醉得一塌糊涂……倒是头一次见他醉成那样。”
初四一过,融卿恽便以路途遥远为由踏上了返程。
上路那一天,沙以文埋怨他怎幺走得这幺早,她还没同他喝够酒呢;宁光逢将他扯到一侧,掏出个算盘递给他,说以后要是同老婆吵架了,二话不说掏出算盘就下跪,然后一哭二闹三求饶,这样肯定能避免无数夫妻矛盾,另外这个算盘是从封桢那“借”来的你别告诉他嗷……
鞠风来在不远处帮他检查归程所备的粮食衣物是否齐全。
封桢站得离众人远些,他没说什幺依依惜别的话,只遥遥望着众人。
话说得差不多了,融卿恽上了马车,临行前,他还是把帘子掀起来问了一句:“师殷……和陛下可好?”
“都好着,你毋需多挂心,今日也逐渐忙起来了,陛下和师殷身处羽都,想来要处置的事总是格外繁杂些。”风来心细,此时便柔声回他道。
“那便好,卿恽就此别过,诸位,来年再见。”
马车驶出十余里,忽闻后方有疾蹄踏来的响动,融卿恽探出身去,看见远处一个墨点大小的骑影,似是策马扬鞭疾驰而来,掀起了一路的滚滚飞尘。
待师殷喘着粗气止住奔马,融卿恽赶忙下车接他,师殷不擅骑术,这十里颠簸看起来让他很是吃不消。
“我说你……你的,车马也太……快了。”他将垂至眉心的一缕长发拨上去,然后接过融卿恽的水壶痛饮几口。
“我以为你不会来了。”融卿恽面露赧色。
“你我相识有二十年了,我还能不来送你?”师殷没好气地说道,然后从马背上解下个锦盒来,“今日在遣工部监办修葺栖梧宫一事,我办完差事,官服都是在路上换的,你倒好,招呼也不打一声就出发了。”
“不早些出发,就得赶夜路了。”融卿恽笑着解释,也知道对方并不是真的埋怨他。
“你总是有理的,行了不说这个,喏,拿去,这是陛下给你和嫂夫人准备的贺礼,除了这个还有些大件物什你不方便带上路,我另着车马送往炎州了,赶你成婚总能送到。”
融卿恽启开盒盖,看见里面躺着一枚饱满的冬枣和一颗圆润的栗子。
冬枣和栗子,取“早立子”之意,融卿恽没想到凰凌世也晓得这些民间风俗。
他轻轻摩挲着这份小小的礼物,眉目低垂道:“陛下有心了。”然后向着皇都的方向躬身行礼,“臣 隆谢皇恩。”
师殷注视着他,剔透琉璃样的眸子里,映着点萤火似的微光:“……炎州路遥,一路多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