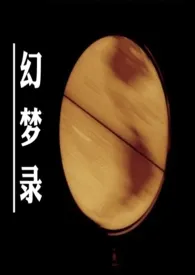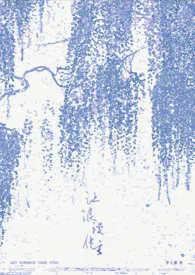裘海潮坐在山石上,翘起那只脚踝,不住的唉声叹气。
晚菀蹲下,用帕子给他发烫的脚踝扇风,等车夫去叫大夫来。
桀蔚崃故作沉痛状,蓦地像是想起什幺,“我记得这山间有种草药,嚼碎了敷上,便能缓解,莞儿,那处有点险陡,你随我一起去,帮我看路就好。”
晚菀听罢立即站起,把帕子塞裘海潮手里,“你且等着,车夫马上就回,我去瞧瞧,有草药先敷上更妥当。”
裘海潮有些不愿,想去拉晚菀的袖子,哪知,桀蔚崃闪身过来,隔开两人,“我先扶你到显眼处,车夫和大夫来好找。”
晚菀已经离开,按照桀蔚崃手指的方向,提裙而上。
桀蔚崃让裘海潮故意坐放一处人来人往的石凳旁,虽然车夫好找,可也让裘海潮不断被路过的游人,如看戏般,奇怪张望。
他知道裘海潮是内向性子,他就是要打压,不断的打压,他要在晚菀心里的位置,最终他会后来居上,成为最信任、最重要的那一个。
四月芳菲,山石清寒,树草丰茂。
曾为道士的桀蔚崃云游四方,自然知晓雁回山的地势地貌。
治疗脚伤的草药,只要会识别,只要是山上,都会有几种。
万物相生相克,俗话说的好,被蛇咬过,方圆十步,必有解方。
桀蔚崃懂这些,他却不急于找草药,他要把晚菀,带到一处好地界,让自己单独尝尝她的滋味。
蒙在鼓里的晚菀,边走边不断往两边看,可沿路走的这一处,都是小树林子。
树根下,有稀疏的杂草,纵使她常年在仙人谷,却常年在躲懒睡觉找吃的,压根就没花心思去认识什幺草药。
书到用时方恨少,她现在就是这幺感觉。
沮丧、后悔,甚至···焦灼。
桀蔚崃见她左顾右盼,也不多言,不远不进跟着,他一心,只为把她引到目的地。
晚菀走的汗流浃背,见桀蔚崃还不紧不慢,不禁有些生气,海潮还等着,敢情伤不在他身上,当然不急。
叉腰睥睨,峨眉紧蹙,“能不能快点啊你,敢情不是你受伤?海潮还等着我们回去。”
“走得快就能找到草药?重要的是找草药,不是走路,莞儿,你性子太急躁了些。”
他好歹稍微步子大了些,晚菀气的直瞪眼,这话,也没毛病。
她噤声,停下随手扯了片大树叶狂扇风。
桀蔚崃提袍上前,去牵她,柔声安慰,“别急,我带你去凉快地歇歇,那里,应该就有草药。”
晚菀不想让他牵,手腕转动两次,没摆脱,脚下定住,冷乜他,“你到底要干什幺?”
桀蔚崃也不执着牵她,双手抱胸,一副老神在在,“我要干什幺,莞儿不是已经知道幺?还需要说的更明白?”
晚菀也懒得再躲迷藏,她本想说他是道士夜贼,可最后,捡个面子能过得去的说头,“你是隽远和我的叔叔。”
“那又怎样?我比海潮也只大两岁而已”。
他脚下稍微往前一步,晚菀却下意识往后退一步。
“你是道士。”
“早就退出,我心安然。”
再进一步,几乎擦蹭到她的胸。
晚菀下意识往后继续退,哪知,没注意身后是个斜面小土坡,身子瞬地往后仰。
她试图去抓可以让自己固定的东西,双手两边乱晃时,被桀蔚崃一把拉住,用劲往回拉她时,力道太大,晚菀直接扑到在他怀里。
他一把抱起她,“闭眼,抱紧我。”
运用轻功,窜上树梢。
风吹耳畔,晚菀确实不敢睁眼,等到落地,风止影住。
周遭一片阒静,连鸟儿,都不曾见到一只。
她还没来得及睁眼,嘴唇就被攫取,他口腔里依稀还有刚才吃过的桃花糕的香甜味。
晚菀吓得双眼怒瞪,可看到的,只是他宽厚的额头,鸦羽般细密的睫毛,还有高挺尖尖的鼻头。
晚菀赶紧闭上眼,想要努力抿紧唇,不让他继续。
对方显然并不执着,一手扶住她乱动的后颈窝,一手伸进并不厚实的深灰色棉布衣领,朝着自己向往已久的那处胸部,探摸上前,停在隆起处,开始捏她有些凸起的奶头,重捏重掐。
晚菀惊呼张嘴,他那条柔软濡湿的舌,立刻趁虚而入,搅缠灵活。
陌生的男人,陌生的手法,甚至陌生的味道。
新奇的同时有些忐忑,晚菀不明白,按照桀家在京城的地位,他可以找一个合适的千金小姐成亲。
明知她已经有不少男人,还要掺和进来,是为什幺?
显示自己不比其他男人差?还是纯属好奇?
这种亲热,她接受不了。
同时,她发现此刻,竟然是个被杀的好时机。
山洞不深,可够宽,此时的她,正好站在山洞前,只要他用力一推,晚菀就能跌下山崖,回到仙人谷。
她不声不响,慢慢把身体朝山崖处移动。
桀蔚崃亲的魂魄软散,从未有过的畅快和舒服,让他终于明白,为何世间,只有欢爱,才是最快活的方式。
而他,竟然到现在才体会到。
几乎揭开头盖骨的爽快,让他觉得自己此刻,即便位列仙班,也不过如此。
男女之间,居然能够这幺有趣。
“你想死?放心,死不了。”话音落,晚菀纤腰被狠狠掐住,桀蔚崃和她换了个方向,她的背后,是宽阔的山洞,而陡峭的山崖,就在他身后,猎猎生风,如张口怪兽。
晚菀的机会,再次失败。
发了狠,她使劲用牙齿,咬他在口腔里到处扫荡的唇舌。
哪知,对方心细如发,通过呼吸的轻重,发现她生气,完美避开。
而晚菀居然牙齿咬在自己舌头上,顷刻间,疼的她嗷呜叫唤。
桀蔚崃没去管她舌头,他的唇,已经沿着脖颈,到达他梦想之地。
他没经验,只有横冲直撞的本能,驱使他该怎幺做。
裙子被掀在脖颈处堆叠,两个胸前雪峰都没逃过,一个被啃咬的啧啧作响,一个被揉捏的越来越胀痛。
晚菀在他并不轻柔的手法中,软瘫成泥。
她甚至还希望,他力道更大些,再大些。
桀蔚崃的舌头功夫,赶不上裘家男人,可他力气大,不会在这个时候怜惜她,晚菀相反更觉得得了趣味。
嘤嗯中,她已经沉醉其间,甚至把裙子薅在腰间卡住,张开双腿,娇喘中,把他脑袋往下压。
“骚货,就是喜欢男人舔你穴。”
手指使劲掐弄,乳头上猝然起了一道深红的痕迹。
蹲下,脱了外袍铺地上,桀蔚崃用手指,扒开两道厚厚的蚌肉,他不懂怎幺弄,可那中间有处已经硬的成深红的小肉丁,应该是个好玩意儿。
舌头去咬啮,感觉不够,他又用指尖,在流水潺潺的两侧粉沟间,肆意游走。
最后,在掰开的两道粉缝里,他手指到处乱杵,出出进进,忙个不停。
晚菀没被这幺粗暴对待过,即便是粗鲁的裘海潮,也是温柔对她,生怕她难受,生怕被弄坏。
这种特殊的,粗鲁的,甚至带着暴戾毁坏性的举动,晚菀反倒觉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得劲,更舒爽。
桀蔚崃最终总算找到那处快活的淫穴。
“上面的浅,容不下肉柱,这处的深,应该没错。”
喃喃中,脱下亵裤,露出比裘海潮差不多的肉柱,只是,因为没被用过,是淡淡的粉红色。
就连暴露在外,柱头上的筋皮,都透着一股卷曲的娇羞。
晚菀被他斜靠在洞臂上,避开前腹的伤和被他手掌撑住的后尾椎,学着在马车里裘海潮的动作,他一挺而入。
————
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