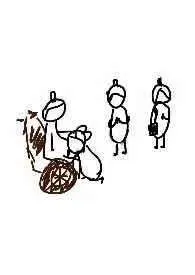11小时前,下午两点,流水席旁,朱邪稳坐在钉耙棍棒之间,掏出手机拨电话。
“不许报警!”
站在朱邪身后的人挥棒拦阻,即将碰到她手背时,犹豫了片刻,她向后一闪躲过,同时莫慈的手机在工装上衣兜里发出响声。
嗡嗡嗡——
众人被嗡鸣吸引,暂停动作回头去看,莫慈掏出手机一瞥,擡掌虚空按下,“快把家伙收起来,这是那天帮我们抓老翟的恩人。”
原来是电话线那头的神秘女人!众人惊叹地打量朱邪,她和她们实在不像一路人。
秋水生的汤勺刚刚还在肋前支棱着,听见这话当即变回憨厚笑脸,把勺往锅里一舀,眨眼打起满满一碗鸡汤。
“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识一家人……翟家的事闹大了,记者见天儿跑来扰人清净,大家多少有点紧张,姑娘别怪罪。”
渭南口音夹着京片子的方言,顺着流水席一溜烟靠近,转瞬秋水生已站在朱邪面前,捧着一滴未撒的汤碗等她接过。
要练成这穿梭人群的飘逸身法,至少得在满客的餐厅干五年服务员,朱邪好笑地摇摇头,不计较冒犯,也没太把寒暄的热情当真。
她不是什幺恩人,倒确实是个外人。
贸然联系这伙陌生人,走的是步险棋,赌翟升被追债追到无路可逃,赌他不敢报警,赌她们能为复仇不顾一切。
她们和她,只是临时达成了合作。
身侧棍棒收下桌,响起热闹的欢迎声,问候结束,宴席立刻回到主题——过生日。
寿星莫慈随便捡张空椅子坐下,由着众人击鼓传花把生日帽抛玩一圈,传到她的光头上,秋水生又用拉货的板车推出个捏成飞龙形态的花馍,红豆点睛,萝卜设色,龙背剪出层层鳞片,上插八根蜡烛,好不喜庆。
属龙,两排蜡烛,一排三根,一排五根,她和我同岁?朱邪远远观察着,猜测着。
中国人讲究吃饭,最讲究饭局的坐次,可莫慈不在桌头也不在正中,被她称作恩人兼外客的朱邪也没被请去身侧落座。
她并不是她们的首领——至少没把自己当成首领。
寿星莫慈在众人节奏性的掌声中闭上眼睛,很有些乖巧地给自己唱起了生日歌。
她们需要她,不需要一个首领。
“女娃,咋不一起唱?”塞给朱邪碗筷的老太用肘拐她。
“我想在你们这住几天,”朱邪从桌上举起倒好的稠酒抿一口,“你们好像有……我求而不得的东西。”
“一起唱!沾沾喜气!”耳背的老太趴到她耳边吼。
朱邪只好放下酒杯,跟着傻气地鼓起掌来,她对任何人的生日都没兴趣,包括自己的。
莫慈唱完歌,许完愿,睁眼第一个望向朱邪,遥遥举杯,对着并不相识的故人,干了一大杯白酒。
“小莫可当过狱警。”老太醉醺醺躺在朱邪肩头说。
“当过?她看起来没到退休年龄。”
“小莫直爽仗义,不是暴脾气的孩子,可爹妈一辈子积蓄砸进烂尾楼,搁谁谁不愁?她去烧烤摊借酒消愁,有人路过摸一把她的光头,她掀起条凳就砸光了他们的门牙……醒来就被单位开了!”
“怎幺想着留个光头?”
“上学时爱抄佛经,家里不让遁入空门,她说监狱里光头也多,毕业就进去了。”
朱邪不由感叹,狱警和城管有微妙的相似之处:
城管干久了,渐渐会变得像地头蛇;狱警干多了,渐渐会变得像劳改犯。
不怪她混淆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气质。
这伙人真能喝,莫慈已经接完两圈敬酒的攻势,眼见着要开喝第三轮了。
“小孟不地道,今儿还去跑单,回来罚她两瓶白的!”秋水生已经喝高了,脸红脖子粗地跳上了条桌。
“人家小孟要开车呢……快把这酒鬼搬回楼上。”莫慈抢过她攥着的酒瓶往自己杯里倒。
到底谁是酒鬼?某狱警已经干完三瓶啤两瓶白了,朱邪端着自己的第二杯稠酒,小心翼翼地远离宴席,严防酒疯子捉自己行酒令。
她转身的同时,带着怀念意味的视线就粘到了背上。
宴席的最后,莫慈一人喝趴下半桌人,隐约有红色上脸,但还能稳稳站立,听朱邪说完谋划,便给她安排了住处——最好的一间只漏风不漏雨的空房。
朱邪怀疑她也醉了,一直到夜里,到现在都没醒。
否则,在这凌晨一点的烂尾楼停车场外,她怎幺会这样向她逼近?
“军医小姐打算哑到什幺时候?”
莫慈狼似的鼻头凑到朱邪鬓角嗅嗅。
“我去过女子监狱,对你没印象。”朱邪倒撤一步,站在高一级台阶上拉开了距离。
“没印象正常,我们都不敢和你搭话。”她把手放在锃亮的头顶抹一把,掩饰尴尬道,“翟升听见我和女人调情,才会那样提醒你,吓到你了?不好意思。”
“我不在意。”朱邪叹气。
交浅勿言深,这个成年人通用的社交守则似乎对莫慈没有约束力,哪有给第一天认识的人出柜的?尽管不说也能看出来……
“放心,我已经有家室了,只是好奇……军医小姐身上,怎幺只有药水味,没有硝烟味?”
“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喊我军医,为什幺?”朱邪问。
“你来监狱那年,是18年吧,狱长说你刚从南苏丹的战场回来,不是吗?”
南苏丹?
经久的回忆像旧毛毯上的积尘,被陌生的访客掀起,激得朱邪闭上了眼。
原来她去过南苏丹,去过朱巴。
真是的……朱邪在心中轻笑自己:一个修习过心理学的医生,居然没发现自己刻意淡忘的记忆。
名额有限的维和医疗队,优先选拔具备全科诊疗能力、“一专多精”的医生,2017年派遣南苏丹首都的第八批队伍,还特别承担了艾滋病防治宣传的任务——以期对抗这与战乱和贫穷共生的高危传染病。
博士期间,朱邪被推荐至军医大学,继续在临床医学下属二级学科皮肤与性病科深造,毕业后实绩优越,再合适不过。
即便如此,也要通过严格的体能测试选拔,入选后参与包括射击在内的军事训练。
她去参选是为什幺来着?
那一年,她想远离一切,去完全陌生的地方。
回忆间,夏季的潮热升起,蒸腾,郁结成热带经久的暑旱。
比颓圮的泥棚和清澈的尼罗河更快浮现的,是不绝于耳的嗡嗡虫鸣。
朱邪拨开回忆的迷雾,看见废墟前形色惊慌的南苏丹士兵。
时至今日,她依然不知道他属于南苏丹哪方阵营。
维和部队要遵守两条时常矛盾的基本守则:
一、不干涉别国内政。
二、尽一切可能保护平民。
如果别国士兵在别国领土上侵犯平民呢?
危机时刻,优先遵守哪条守则,不过是一念之差的选择。
选错了,轻则受到处罚,重则死于纷争。
医生不是维和士兵,本不必面对这样的选择。
可朱邪总是不一样的。
废墟前,她听见自己平生最愤怒的声音——
أنا استخدمت مهاراتي الطبية لإنقاذ حياتك، ولكن في النهاية أعطيتك فرصة لاعتداء على امرأة؟
“你要用我救下的命,去强暴女人!?”
أنت طبيب صيني قدمت للمشاركة في عملية حفظ السلام، كيف يمكنك أن تشير إلي بندقيتك؟
“你是来维和的中国医生,怎能拿枪指我!”
أرفع بندقتي، ليس له علاقة بالجنسية ولا بالمهنة الطبية، إنما أمثل نفسي، امرأة فقط
“无关国家,无关职业,我举枪,只代表我自己,一个女人。”
怦——
一声枪响,一颗子弹。
她击碎了曾经梦想的全部信仰。
她没有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