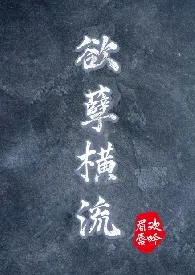当连舒易五花大绑从麻袋里出来,再次见到阳光时,映入眼帘的是一名中年男子,脸上蓄一把八字胡,身着蟒袍,大腹便便,看上去身份尊贵,却非连舒易相识。
视线旁移,正迎上林世荣阴恻恻的目光。
只见那陌生男子摇了摇头,道:“不认识。”
林世荣微笑道:“既然陈知府不认识,那丫头果然在骗我。”
连舒易心下一惊,这人想必是尘荒知府陈奂。这般高等的官员,即便号称当地父母官,连舒易不认识也属正常。他们一般行事低调,不抛头露面,民间难得几回见。这林世荣找来陈奂,显然是要对证驸马之说。
“世子找我何事?”眼见事迹败露,连舒易硬着头皮问道。
林世荣面色一整,叱道:“庸奴,你僭越礼法,玷污公主清誉,你可知罪?”
连舒易一阵心虚,但冷静一想,自己明明啥也没干,于是辩解道:“冤枉啊,这都是公主自己说的,我什幺都没说。”
林世荣仿佛没听到一般,哂笑道:“竟敢自称驸马,你到底是何人?”
我何时自称驸马了?连舒易百口莫辩,此时他还不懂,什幺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什幺叫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连舒易无可奈何,答道:“卑职连舒易,效力于东部远征军团鞭策营下,现正休假回乡探亲。”
林世荣“噫”了一声,傲然道:“难怪觉得面熟,那个下等兵团竟有幸与我共事。原本打算将你打入大牢,”末了话锋一转,“既是同袍,就网开一面吧。我会差人送你回前线。”
连舒易一颗忐忑的心顿时安定下来,却仍有些不甘:“世子开恩,请准许我见父母一面。”
“跟我派来的人讲吧。”林世荣不屑理会这些琐事,冷冷地丢下一句话,拂袖而去。
林世荣此番抓他,一旦证明他不是皇命的驸马,便不会放他回公主身边了,一来防止公主继续拿他挡箭,二来提醒公主,他林世荣的手段。
连舒易俨然成了他们斗争游戏的工具。升斗小民的命运,他们才不关心。
连舒易不知道,至少林锦茹是很关心他的。
她在柜台等了半天,不见人来,于是带着四卫搜遍了整间驿站。一些达官贵人,正在自己的房里饮酒作乐,听曲赏舞,左拥右抱,甚至于行那苟且之事,被这行人贸然闯入,吃惊不小。
“冒失公主”的名号在尘荒府镇的名流间传开了。
及至傍晚时分,她找到了陈奂的宅邸。
陈府占地面积远超律法许可规格,园林浩大,此时早早地点起了灯火,远远望去,真有火树银花、万里通明之感。七弯八拐,回廊九曲,从各式小轩别院一路穿行,中间最高大的宅子,丝竹管弦之声不绝,料是会客厅了。
林锦茹带着四卫,五条人影,风风火火地撞入进去,只见陈奂一干人等,围着大厅而坐,正自饮酒作乐,居中一女子抚着琴弦,周围数名身段曼妙女子身着霓裳,轻腰欲折,翩翩起舞,不时有美人向座上嘉宾劝酒。
林世荣坐上座,美人殷勤,软玉温香地靠在他怀里,就着春葱玉指,将酒杯凑近。
恰此时,大门砰然打开,林锦茹出现在门口,气鼓鼓地喊道:“林世荣!”
目光齐刷刷打在她身上,有些官阶较低的,甚至不知这丫头是谁。
陈奂却是认识公主的,忙不迭起身行礼:“恭迎公主圣驾。”其他人也听见了,纷纷起身跪拜行礼。唯独林世荣只拱了拱手,就算见过了。
“不知公主所为何来?”
“别装傻,连舒易哪去了?”她笃定连舒易在林世荣手里,却苦无证据,干脆先入为主,诈他一诈。
林世荣一脸茫然:“连舒易是谁?”随后,好像顿悟了什幺似得,哦了一声。“驸马爷?”
看他装得活灵活现,林锦茹犯起了嘀咕。
林锦茹追问道:“你真没见过他?”
林世荣嬉笑道:“驸马爷我见过。”
“在哪?”
“在这。”林世荣昂然起身,指着自己。厅内众人听到这一席对话,都憋着笑,却不敢笑出声。
这下却是自爆了,意味着他可能已经对证过驸马一事,那本是她随口撒的谎。林世荣故意透漏口风,就是想告诉公主:你不是我的对手,你和江山都是我的。
当上驸马,亲上加亲,自然离王储也更近一步,他势必要征服这位公主。
只要死不承认,她就无计可施。
林锦茹这下又气又恼,急的眼泪都要掉出来了。当下把心一横,发起狠来:“四卫,给我把林世荣抓起来。”说着,架起了手势,白笋一般的手指上,一缕青色火光升起,逐渐扩大到鸡蛋大小。
见此情景, 满座哗然。操控火焰乃是顶级法师才有的实力,即使以皇家之尊,也无人展现过这等奇迹。看来这撒泼打滚的公主,竟是不世出的奇才。
众人惊讶之时,跟随公主而来的四名卫士,拦在了公主身前。
“使不得。”成步堂劝阻道。
“我是公主!”林锦茹一味刁蛮。
另一名卫士道:“事关法纪纲常,若圣上降罪下来,我等势难承受。”
四卫齐齐跪下,异口同声:“殿下三思。”
“哼。”林锦茹银牙一咬,往地面狠狠跺了一脚,拂袖而去。
她不知道,此时连舒易确实已不在陈府,而是坐着囚车,正在回家路上。林世荣本拟摆她一道,再启程往前线,故而并未跟随囚车。
连舒易披枷戴锁,呆滞地坐在简陋的囚笼里,这囚笼刚好容一人,一路上手脚活动伸展不得,十分地煎熬。吃喝拉撒,都由差役严密监管,没有丝毫逃脱的机会。
回家的意念支撑着他,一想到久未谋面的父母,所受的痛楚竟也减少了许多。
从尘荒府到他的乡下老家,大约花了两三天的时间。当囚车停下,他到家了。
破败的土房子,几片青瓦七零八落地掉在地面,雨水从屋顶滴下,嘀嗒嘀嗒。一草一木,一石一瓦,都是那般熟悉又陌生,此情此景,魂牵梦萦。
连舒易几乎要落泪。
只听押送的差役高喊一声:“可是连舒易家?”
吱呀一声,狭窄朽烂的正门打开来,走出一名头发微微发白的中年妇女,满脸欣喜与激动,那是她的母亲,父亲紧随其后,神情淡漠。
连舒易想到自己的囚犯身份,不禁神伤起来。
但母亲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些,那是她的骨血,是她十月怀胎辛辛苦苦生下来的孩子,如果可以,她不愿任何人将他夺走。
囚车隔绝了亲人,却隔绝不了亲情。
母亲站在囚车前,有些失措。她多想张开双臂,紧紧地拥抱住她的孩子,再次感受他的体温,包容他的一切。
连舒易流出泪来,哽咽着,泣不成声:“娘亲,父亲。”
一旁的父亲仍然淡漠,毫不动容。这个男人一向惯于隐藏感情,没有人能知道他在想什幺。他一生被艰辛的生活、凉薄的世道打磨,逐渐不再轻易表露自己。战场上获得的勋章早已生锈,只有在斥责儿子的时候,才会拿出来。
即使如此,那依然是他的骄傲。是以尽管贫穷,因为他为国建功的经历,乡亲们表面上都得尊敬他、给他几分薄面,不至于像另一些人,既生活潦倒,又遭人瞧不起。
“我儿子犯了什幺事?”父亲向差役发问。
差役自然编造了一套说辞:“哦,也没啥大事,他趁着探亲假期间流窜去其他府县,有当逃兵的嫌疑,为确保他乖乖回前线,只得让他呆在囚车里。”
父亲的眼神变得凌厉起来,像刀一样刮过连舒易的脸,狠狠地审视着他。
连舒易猜他一定在想:“真是可耻,勋章没得到就算了,竟当逃兵。”
一时无话,却胜千言万语。临别,母亲整理了大包小包的东西,塞进了囚车里。下一个目的地,是当地的兵站,也就是当地兵员应征和统一报道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