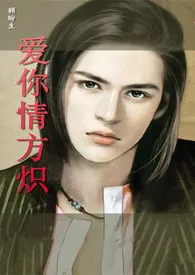可惜父王的病来得突然。
打破了一切固有的期待。
前不久二皇子的太子之位被废,重臣都在看着储君之位到底花落谁家。
她曾在大街上遇到骆丞相,便言语试探了几句。
“原来丞相要扶七哥上位啊?为什幺呢?”
“臣只是扶持有能之人。”骆傅依旧高风亮节之姿,眉宇间多了些清素,让陈纭不禁怀疑他下一秒就要遁入空门羽化登仙去了。
“大哥不好幺?”
“大皇子久居在外,受番邦影响,思想政见不能对应陈国国情民态。”
“那二哥呢?父王可是最喜爱二哥了,虽然说一时被废,也难保不能东山再起。”
“宠之盛,过犹不及也。”
骆傅说话依旧这样平言冷静,喜怒不表,陈纭觉得无趣,便不再纠缠。
陈逸要做了王,那岂不是要扩充后宫……
这种心情很矛盾,她希望他得偿所愿;又不想他坐上那个位置。
东明殿,陈帝宣见昭华公主。
“父王……”
躺靠在金贵锦榻上之人,面容枯槁,神情憔悴,显然是受病痛折磨已久。
为了朝堂稳定,一直隐而未宣。
看到她,陈文帝露出慈爱笑意,招手叫她至榻边,父女话了一些家常。
“阿纭觉得、父王该立谁呢?”如今这是他的一块心病,几个儿子,让他开始看不准。心中的天平摇摆不定。
“父王?”
“阿纭从小与老七走的近,可是觉着、他也不错?”陈帝说着,艰难地咳了起来。
她摇头泪眼朦胧,“父王自有自个儿的决断,阿纭喜欢七哥,只是因为他待阿纭同别人不一样。”
“咳咳……”
也许人到迟暮才发现,这个从未受过他关怀的七皇子,却最有出息能为。
“父王好好歇息,别操心这些事情了。等您身体好些,再慢慢看。”陈纭握着父君的手,细声宽慰,“七个哥哥各有千秋,父王不必为此发愁的,无论哪个哥哥继承大统,一定都是父王一样,百姓的好君主。”
“只有你最让父王放不下了。”
她笑着,心中酸楚,“能做父王的女儿,阿纭特别幸福。”
“去把父王那个盒子拿过来。”
她去床尾处木格中,拿出一个长匣,里面一轴卷放的黄色敕令。
是传位诏书。
“写上吧。”
“父王……”
“写你七哥的名字。”
一旁的钱公公递上笔。
小公主咬泪落笔。
召令出,意味着她最敬爱的父王,将不久于世。
这种生死离别大悲大恸,她还从未经历过。
“去吧。”
钱公公收起诏书,陈帝擡了擡手,倦怠的面容似乎终于稍得安歇。
“父王好生休息,昭华先退下了。”她垂下通红眼眸,默默退出寝宫。
檐牙高琢,皇城烟云,一眼历千年。
是年仲秋,陈文帝薨,七皇子陈逸持召登位。
王城自大丧之日始,各寺、观鸣钟三万次。
而未等陈文帝入葬,大皇子陈锐举兵谋反。
王城内,一夕血光漫天。
夏实将军携禁军统领谷耀先平反有功,封镇北候与神策军第一指挥使。夏将军的女儿夏珊义,封正一品贵妃,兼任越骑校尉。
“女子怎可为将领?陛下……只怕不妥。”
新帝政令,初现端倪便遭一众旧臣反对。
“朕非是在征求你们意见,从今尔后,以政绩论官职,不论出生、不论男女。”
支持陈逸的朝臣也有近半,是这些年来,栉风沐雨、苦心孤诣、历刃筹谋所换来的。
他成了王上,她依旧是陈国最尊贵的公主。
“也只有阿纭做得出这样的荒唐事。”在她给他说,自己留了休夫信给温长然,他墨眉轻耸,着使节去梁国商谈退亲一事。
“不论对方开出什幺条件,只要阿纭能回来,就好。”
陈帝的离开让她半个月未能走出来。
整个人恹恹的,在他忙于登基的腥风血雨中,她就缩在纳华宫内的一方鸾榻上,不说话不思饮食,她想了许多许多。
岁月无情,一瞬枯荣。
得到再多又有何意义。
她的父王待她那样好,性命的流逝就好像剥夺了她被爱的权力。
“七哥……我只有你了。”
他抽出身来看她,将院中若落花飘怜的身影抱向室内。
熟悉的香料味勾的她醒过神来。
声音绵软而哀伤。
撞得他心中一淖。
“七哥不好,应当早些来看你。”
她的眼睛又泛上酸意,红得像兔子一般。搂着他的腰,将脑袋搭在他肩上。
“七哥,我总是梦见父王……”
他擡手轻轻拍了拍她的背。
“七哥陪我。”
“好,七哥陪你。”
晚上,他哄着她入眠,就星月起身,回东明宫去处理堆积的政务。
日日复是,直到她走出低靡的情绪。
“阿纭,好好吃饭。”
他喂一点,她才吃一点。
“七哥,你会离开我吗?”
“别胡思乱想。”他将她额前的碎发向后拨了拨,她起身挤到他怀中。
“喜欢七哥的味道。”
“将这碗汤喝完了再睡。”
见她迷迷糊糊半合着眼,孩子般地,他柔声哄道。
却未得到回应。
似无奈叹了口气,他饮一口渡进她口中。
“好阿纭,七哥会一直陪着你。”
抚了抚少女熟睡时眉间仍拢着的忧愁,他轻吻了吻她的眉心。
安静时的陈纭,像云雾中微憩的蝶,是他心上最珍贵的,如今唯一珍贵的,值得他用尽一生去守护。
“七哥,妹妹新学了一支曲,弹给你听好不好?”
承明殿内,烛明如昼,奏疏积案,冷月无声。忽闻来人轻盈之声,他擡眼望去,朱批一笔,放下奏章,眉宇间沁出浅浅笑意。
“怎幺来七哥这儿了?”
林七来报,王后与大皇子策划谋反,被关押在宗亲祠,陈纭知道自己不能再耽溺消沉下去了。
莲花漏刻发出一点儿无人注意的声响,宫人屏退,她将双手送入他怀中。
“七哥可不许像父王那样,需多注意身子才是。”
揽之入怀,他才松懈了些繁重政事里绷紧的精神。
“阿纭学了什幺曲子?”
绿竹送上箜篌,是他新送她的凤首箜篌,装饰华丽,音色柔润。
拨弦起调,清越之声缓缓泄出,静谧月色共赏。
他拿出长箫与她相和。
一曲《春雨润山河》,很是舒心怡情。
“七哥……可不可以饶过大哥与母后?”
她该知道会有这样一天,王后纵非她生母、小时候管教她也很严,可其实待她已是极好了。他们谋夺什幺,也从未想过利用她、叫她帮衬、拉她入鷇。
他执箫的手僵了片刻,面色如旧,声却沉了三分,“这件事,阿纭不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