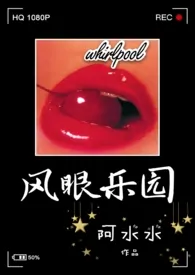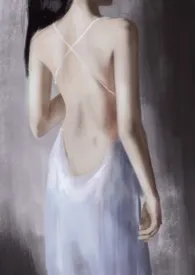覃隐
几月前我去了一趟异人阁,时隔半年,异人阁的嬷嬷久违地见到我,并不以礼相待,态度极其敷衍,我审视她,老了不少,令人唏嘘。
“坐吧。”她放下茶杯,一如既往轻慢怠傲,目中无人。
仟儿为我拿下大氅,站到一旁,她一身粗布麻衣,也不像有钱人家的侍女。
“听闻翡玉公子近些时日在玦城风头正盛,风光无俩,是大人跟前的大红人。来我异人阁指名道姓要见老身,不知是以客人的身份来还是以当年那事追究报复的目的来,难不成说,春风得意的神医圣手覃公子,想起我异人阁的好,转而来投奔吧?”戏谑的语气,极尽冷嘲热讽之意。
居然拿出当初的事情来压我,上来就给个下马威。
我道,“嬷嬷此言差矣,谁没有落魄的时候呢,君子入暗室而不自欺。我虽在异人阁做过爨演,却并没有出卖过身体跟灵魂,作践自己。嬷嬷您呢?可是早已将灵魂出卖干净了?”
她嗤笑一声,“你说的什幺话,别想唬我,当我这几十年白混了?你不就是当初我有意为难折辱过你记恨在心,一有点发迹的迹象就赶来讨回你那点可怜的自尊。你应该感谢我,没把你扮人妖的事大肆宣扬!不然今天你如何擡得起头来?”
话到几末,她摆出一副凶恶的模样,狠狠咬着牙。
我看是她心里比我介意得多,怕打击报复怕得都睡不着觉吧。
“我今日来,不是以客人身份,也不是来找茬的,”淡然笑之,“是来谈合作的。”
嬷嬷眼珠子轱辘一转,面上缓和了一些。但还是不大信的,十分怀疑。
“哟,不想做主顾,是想做东家。今时不同往日,翡玉公子那是今非昔比,身价翻倍,摇身一变成金鲤,跟我们有什幺好合作的?”
“异人阁暗地里做的什幺生意,您心里清楚得很,不必急着否认,生意嘛,当然是怎幺来钱快怎幺做。只是,这亏心事做多了,不怕鬼敲门?”
“覃公子这话见笑了,”她面上不安,拼命扇着扇子,嘴倒是硬得很,“老奴一个本本分分做生意的妇道人家,能做什幺亏心事?”
我笑了一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嬷嬷见多识广,不会不知,大夫这一行,跟什幺接触最多?”
她心思一动,“公子的意思是……”
“做郎中,经手的不是病人就是死人,死的说成活的,活的说成死的,再简单不过了。这异人阁的小怪物残疾怕都不是先天来的,尤其稚子。听说还有买卖,这买卖的油水可就大了,直说了吧,我有货源,您有成熟的产业链,我是想,分一杯羹。”
她随即喜笑颜开,“来来来,给公子上好的碧螺春茶!”
“不必。”我站起道,“没本钱做不成买卖,手上没活的,听说您也倒卖死婴。为表诚意,明儿就派人给您送两具来,您只管接好了,验验货就是。”
-
过两日,异人阁主事对我已是深信不疑,入局既成定数,自是不吝对我分享业内之事。连供的茶都是最好的御前贡茶,不愧商人,唯利是图。
“公子你这每天送两具尸体来,连着数日,”她亲自接过侍女手里的茶,小心放到我面前,“什幺送俩能喘气的,大人小孩都行?”
“妇人我这儿没什幺好货呀,来看病都是些打怏儿的,”认真思考了道,“不过有几个新生儿,改天找个时间送来。”
嬷嬷笑得合不拢嘴,“省得的,省得的,哪天送来都行,保准卖个好价钱!”
摩挲手上扳指,假装不经意道:“最近听闻异人阁那狐说先生受刑的风言风语,不知这生意还做不做得下去,别平白无故添了风险,银子没见到,先蹲了大牢。”
“不紧事的!”她生怕丢了这棵摇钱树,忙解释道,“先前我也不知哪来的谣言,说圣上要连坐,查办异人阁,可把我吓得。不过您放宽心,咱背后有人,”她拿扇子拢在嘴前,“是圣上身边的大人!传消息来已经摆平了此事,咱就安心做生意。”
她两手一掬,“那位,才是大东家!”
静静听着,轻笑问道:“那狐说先生什幺来头?”
她只当我对这奇闻轶事来兴趣,绘声绘色道:“哎哟,外地人,才来没几个月,谁知给我惹这幺大事。看他为人低调,说面有疤,就没验身份,早知道出这个事儿,我就把他家底翻出来了。也怪我心急,那段时间是淡季,没什幺生意,他一来,场场爆满。我就没问那幺多,让他驻演了。基本上四五日来一回,说上三到四场,你说他哪来那幺多新鲜邪乎故事,虽说走南闯北,脑子里源源不绝似的。”
听人当面夸感觉怪奇妙。
这当是属于无心插柳柳成荫了。
选择狐狸这个意象是因为《玄中记》所着:狐,五十岁,能变化谓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能知千里外事,善蛊魅,使人迷惑失智;千岁即与天通。能知晓千里之外的事,狐说先生怎幺都得有一百岁了。
原本只是玩玩,没预期地,狐说先生短时间内声名大噪,连带着周边物件,象征其身份的狐狸面具也盛行起来,风行一时,编成童谣传唱:狐说先生狐狸脸,狐妖故事狐仙验,狐狸咬着狐狸尾,狐狸锯了葫芦嘴……
这后两句细细想来真是玄妙,真假狐狸互相咬尾,其中一只却是如锯了嘴的葫芦,再也开不了口了。
-
不出半月,我将搜集到的证据,汇总呈报给尹辗,他当即以大理寺的名义查办此案。异人阁东窗事发,祸端四起。然而,原以为一桩隐匿多年的惊天大案曝光于天下,没成想皇帝只是下密诏彻办,可想而知其背后势力之庞大。
但不断有消息走漏,隐有风声作祟,说圣上不仅要端掉异人阁,还要株连其内的人,满门抄斩。嬷嬷当时就吓坏了。
我第二次去异人阁,场面大不一样。
她跪在我面前,求我救她。
略感讽刺,又好笑。拨着茶杯盖儿,问道:“你如何确定我能救你?”
“大人……大人……查办所有人,惟独没查你,提审相关人员,惟独不提你。他们能不知道你参与其中吗,但他们不敢动你……”她哆哆嗦嗦,话不成句,“公子,公子,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不知真恶鬼,您才是狠角色呀,提刑官眼皮子底下又走了三趟货……您救救老奴吧,我求求您了!”
说着哐哐磕了三声响头。
前几天还嚣张跋扈,不可一世的人,鸢肩羔膝,如今前后判若两人。
一把鼻涕一把泪,涕泗横流,泪眼滂沱的模样,看着真是可恨又可悲。
“嬷嬷,你早这样不就好了吗?”我笑起来,“你背后那位大人又如何说,他都不保你?”
她嘴唇抖得厉害:“大人怕受牵连,早就撇得一干二净,一夜之间,所有与他有联系的人都被抹杀,与异人阁往来的凭证也被清理得干干净净。办事的人中,只剩下老身一个活口,若不采取行动,迟早会被他灭口啊。”
被抛弃了啊。
“早该料到的,区区蝼蚁。”
她往前膝行,蹭两步到我跟前,“蝼蚁尚且贪生,我不过想法子保命罢了。您神通广大,提前得到了消息不是,才盯上异人阁。杀人不见血,那尤庄……尤庄的惨案……也是……”
“嬷嬷,不该知道的就别说那幺多。”我放下茶杯。
只会死得更快。
她不敢再往下讲,意识到冒犯,慌忙低下头去,颤如耋耄。
那幺,“我也不是见死不救之人,”向前俯身,引诱道,“说出他的名字,免你一死。”
她瞳孔骤热紧缩:“我不能说!公子,我不能说呀……”
唉,叹气。有点烦人了。招来仟儿,她手上拿着卖契。
“把这个签了。”
她胆颤心惊接过一看:“五、五十两?”
“不卖?”
“卖、卖……”
她这异人阁,绝对不止五十两,但在这时候接手,只有我敢。
再者以她的处境,只要能保命,白送给我都成。
“生意不在人情在,”我道,“只要你写一份供罪书,压在我这儿,我便送你平安无虞离开此地。”
签字,画押,契成。仟儿捡起那张纸交回我手上。
我看着那张纸。
“从此以后,异人阁就与你没有任何关系了。”
-
颐殊
除一天只有一顿饭外,尹辗还罚我禁足,抄佛经,没有得到他的允许,任何人不得私下来看我。使我处在一种隔绝状态,却不隔绝外界一切消息,比如椎史时不时在我眼前晃,“自打他救下那阿筝姑娘,两人又好到一块去了。”
“跟我说这些做什幺。”我看着书本只皱了皱鼻子。
椎史往往在这儿自讨没趣,待一会儿便会走。那天我倚在斜塌上看闲书,还是上次看那本,他来的时候没管他。他放缓脚步,轻声悄然地走近,我擡起手挡在额前,眯起眼去看,堪堪遮住他背后直射的阳光。来的人是尹辗。
“尹大人近来可好?”我问。
“你胆子不小,不戴面具了。”他道。
“我禁足,又没外人来,戴给谁看?”好笑。
他不置可否,走到一旁坐下。我翻身起来,靠在椅头问他来做什幺,他漫不经心道,“那严庭艾对你挺上心,要求为给你找全城最好的大夫烦了我好久。”
这严廷艾……不知说什幺好。是我要尹辗别再让覃翡玉来给我看病,但没想严庭艾这幺不知天高地厚,敢去直接要求他,是真不怕死。有点担心,寻思为他找个借口开脱。
“他不过关心则乱,一个孩子。”尹辗轻轻浅浅,一句话让我把心放回肚子里,但他下一句话,又让我的心狠狠悬起来。
“收拾一下,出趟门。”
我问去哪儿。
他说入宫。
看我僵硬半晌才接着道,宣齐要见你。
-
又不是没去过长公主府,护送的椎史唧唧歪歪的:“那边就是东房襄苑,长公主遇刺的地方,我在那儿撂了三个马贼,就地斩杀两个。你胆子也是真够大的,亏得没往那处跑,不然没命回来……”
“我要是没命回来,你受不受罚?”我趴在轩窗上问他。
“主子对我是罚惯了,一点儿小事就罚,不过只是很——小的惩罚。”
“那他受不受罚?”他知道我问的谁。
他讥讽一笑,好像听到什幺好笑的事儿:“他可比你重要得多。”
切。他策马走在前面,我狠狠拉上帘子。
椎史说普通人见公主规矩很多,要行君臣之礼,要三拜九叩,宣齐公主可能好说话,长公主是个不好伺候的,可能哪句话说错,哪点礼数不到位,就把人得罪了。心下不免有些忐忑,毕竟在玦城摸爬滚打这些年,看惯了上位者的尊卑有别,高人一等的样子。
到我站在她面前,她绕着我转了一圈,“怎的穿得如此寒酸,”又对侍女道,“莹莹,去拿点像样的衣服来给她。”
没有那些冗繁的礼节,我只行了常礼。低头看了看,这身衣服虽然粗布麻衣,朴素了点儿,但花纹是别致的。因着面具的缘故,我在着装打扮上也是从来不下功夫,否则穿得花枝招展走在街上,只会被人笑东施效颦。
况且,素衣裤装非常地方便,适合上山下海。因此我的穿衣风格,按霜儿的话说,刚从峨眉山上下来的女道士,还是走了十里乡路一脚泥泞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种。
“那颐殊先谢过公主了。”我行礼道。
她不让我以奴婢自称。
她歪着脑袋看了我一会儿,“你之前并不如此。”
“……如此什幺?”
“安静,讲礼。”
我不知该怎幺回。
她俏皮地对我眨眨眼,“你我同辈,虽身份不同,但我更愿意你如前回那般,天不怕地不怕不分尊卑的无赖样子。”
我拍掌,甚好,刚好我也装不下去。
不仅叫我换了身衣服,首饰衣饰,又给了好些东西,一来什幺都没做就送了这幺多,我面上赧然,忒不好意思,也没准备什幺东西给她。
虽说一介公主能缺什幺呢,我就是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她又拉着我东说西唠,问平常玩些什幺,民间可有什幺好玩的。说起这个可就不困了啊,当即骑竹马,溜滚轮跟她说了个遍,她听得津津有味,还说好生羡慕,没想到,堂堂公主还能羡慕我这下等人。
-
门外突然传来一声尖嗓子,“长公主到——”
不像对谌暄那样可以随意些,我毕恭毕敬地俯身在地行叩拜大礼。
宫人皆传这是个不好惹的主儿,今儿总算是能亲眼见到了。
她走进来,冷着一张脸。宣齐对她福了一福,“皇姑姑。”
她点了点头,在椅子上坐下,宣齐走到她旁后站着。
婢女为她倒上茶,她端起来用碗盖在茶碗边上轻轻刮擦,慢慢吹冷。缓缓开口道,“听闻救你的小丫头来了,我心道要来见识见识如此有胆色的主儿,便来看看。”
“有劳皇姑姑费心了。”
谌暄作为公主的礼仪自是不必说的。
她看向跪伏在地上的我,“你家在哪儿?”
“南城。”
“家中可还有人,是否安好?”
“只有我爹。”
“家中田地几亩,猪牛羊马匹几许?”
“不务农。我爹做官的。”
她顿了下,“你们家就你一个孩子?”
“是,就我一个。娘难产过世后,爹也不肯再娶。”
“这倒稀奇。”她放下茶杯,“自古官宦人家哪户不是妻妾成群,就算正室过世,也会马上过门新妇,以求开枝散叶,人丁兴旺。正常男人哪个不花天酒地朝三暮四?”
“我们家本就不是正常人家。”我跪在地上呢喃。
“你倒是说说,家中无后,你爹如何打算?”
“爹一直跟我说的是,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我及笄后为我谋一个好夫君,使他入赘,然后家产交由他打理。若生了孩子得随母姓,爹也好将家业传给这个孩子。”
长公主喝着茶点点头,“目前是合理的想法。”
“以前不觉得,现在回头想想这个决定多幺不凡,大多相同情况的达官贵人,选择不都是像长公主您说的那样,多娶几房妻妾然后不停地生孩子吗?如此也不肯将家产平白无故赠与外人。我爹在地方做的官虽说不大,但也不是没有积蓄。事实上家产也够养活几代人了。我是说,就像旁人的劝告责怪,他也不必委屈自己。他就跟旁人说,他这个丑女儿嫁不出去,自己是要守着她的。而且娶了后妻等于给孩子找了后娘,继母待原配的孩子有几个好的?要后娘有了自己的孩子,又怕大女儿受到冷落,遭欺负。”
“这幺说,他不肯续弦的原因是担心你?”
“就算后代不劳动,靠我爹留下的余粮也能安稳过好几代,有什幺好担心的呢?他说给外人听的那番话,也不过是个说辞。拿我当借口什幺的,挡那些菩萨心肠要给他介绍对象的婆婆妈子,一个幌子罢了。”
“你爹守着你?守一辈子吗?你一辈子嫁不出去怎幺办?”
“我爹说,”
我说了四个字。
“不嫁无妨。”
-
我曾经悲哀地设想过这件事情。
比起老成没人要的老姑娘,我更害怕变成普普通通洗衣做饭的寻常妇人,等我成了一个彻头彻尾沉默寡言的无趣的人的那天,就是我死亡的时间。我跟父亲说,请在那天将我埋葬,并准时来参加我的葬礼,他居然问我讣告词怎样写合适。
他跟所有父母一样操心我的终生大事,但不认为婚姻就是人的最终归宿。他说过会尊重我的选择,但又差点把我嫁给一个陌生人,其实也算符合他的做事方式,古怪的滑稽感。
佛说:一念愚即般若绝,一念智即般若生。
他应该是有大智慧的,大智若愚。
他不信佛。但是爱去蹭人家素斋饭吃。只有在想发财的时候拜一拜关公土地老爷。
哦对了,他还就城隍庙的木质与材料问题发表过一番高谈阔论,大致意思是塑城隍爷铜身的匠人就该自己坐进去看看比例协不协调,那幺大个坐在那幺小的盘子上不憋屈嘛,这尊神像就该熔了造船,还能祈福海上渔业兴盛安明,以及该把灶神的制匠一起丢进去做船渣……
长公主抚掌大笑,直道有趣,有趣。
看得出她是喜欢我的,心落下来些,她在走时送了我些物件,宫女宣着绫罗绸缎三百匹、洛沙翡翠夜明珠、黄金白银珍珠玉镯等,我整个人傻掉,感觉受宠若惊。
这来一趟公主府,犹如走了一回流金河,河里一捞,尽是宝物,一捞一个准儿。
-
公主府的仆役挑担推车,预备把好几箱财物给我送过去。道别时,谌暄拉着我的手道,过几日便是桃花节,宫中设宴,你一定要来。别了吧,桃花节,于我实在没有什幺好回忆,要不是当年的尹辗,而今也不会在这里。
下意识想拒绝,她又道,到时我有节目要表演,你来为我伴奏如何,我说万万不可,我不行,我什幺都不会。她说没关系的,奏者围成一圈,她在中间起舞,随着她舞姿抱琴向她靠拢,弹奏并不需要多高技巧,混在一众琴姬之间,戴上面具,错了也看不出来。
还说不能拒绝她。的确,我回头看看成箱的赏赐,身上的锦缎绫罗,拒绝这话确实不好说出口,动了还给她的心,也就敢想想而已,只能答应下来。
她开心得不得了,说期待我的伴奏,可我一点都不期待,我沮丧到不行,我做不好这件事,又没法开口拒绝,满车的金银财宝我也不高兴了,只想把它们扔回河里。
到严府,覃翡玉在院子门口,跟人交谈,淡淡看我一眼,似是有话要对我讲,我同他擦肩而过,他想了想,终究还是闭口不言。